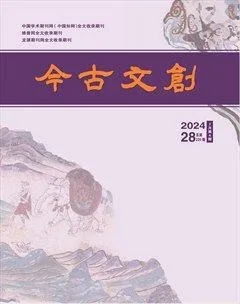庄学对阮籍咏怀诗创作的影响
【摘要】阮籍作为魏晋玄学名士的代表,在《咏怀》八十二首的创作中,无论从诗歌的思想、意象选取、批判性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追求自由超脱、安时处顺的庄学思想。昏暗时局下,诗人内心的恐惧与挣扎,只得通过庄子逍遥天地的生命观寻求解脱。《咏怀》八十二首言辞微妙,立意隐晦,意境玄远,得见阮籍受庄学影响下,诗歌创作中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和精神世界。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庄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3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10
阮籍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现存诗歌共八十二首,皆为《咏怀》。正始年间,曹氏与司马氏争名夺利,互相倾轧。司马氏夺取政权之后,“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阮籍等士子的处境更加艰难。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咏怀》八十二首在情志寄托上皆有所保留,刘勰评价:“阮旨遥深。”[2]钟嵘亦说《咏怀》“厥旨渊放,归趣难求”[3]。可见阮籍的咏怀诗的总特点是内涵深远,抒情隐晦。这固然与身处乱世需谨言慎行的社会环境相关,但身处魏晋玄学高潮期,儒学渐失统治地位,庄学发展达到新高度,处于士族领袖地位的阮籍更是“博览群籍,尤好《老》《庄》”[1]。八十二首诗中反映出阮籍痛苦、矛盾的精神状态、清高超然的理想追求,皆以庄学书写性情、思辨明志,故《咏怀》是阮籍深受庄学影响后的创作产物。
一、追求自然与超脱的庄学思想
庄子曾以无名人之口吻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也。”[4]可见,“自然无为”是庄学思想的核心。阮籍同样在《达庄论》中表述了“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5]的想法,认为万物顺应天道才得以生生不息,在《咏怀》中也有多处表达了对庄子自然观的认同。
(一)唯物的自然观
阮籍对自然的认识受庄子影响颇深,他认为自然就是客观世界中真实存在着的自然,这与当时广为流传的贵无论有本质区别。阮籍认识到,天地之中人和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运行方式。诗曰:“混元生两仪,四象运衡玑。曒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辉”[5](其六十九)。阮籍意识到自然是一个宏大、深奥的存在,运行之法应“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5](其二十二),不以外力相迫。待到诗中真正出现“自然”二字的则是在《咏怀》四十八“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缤纷”[5]和五十三“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5]二句,意在强调万物运行自有其规律,不可人为加以干预。这也表明他体察到“四时更代谢,日月递代谢”(其七)[5]的自然流变后开始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最初没有受到外物的染指时本质是非常纯净的,性“灵”情“真”,才能与“自然”之法相契合,达到“穷达自有常,得失又何求”[5](其二十八)的豁达境界。但人事随自然代谢,面对自然界的更迭,阮籍联想到当世君子之消逝,悲伤与苦闷齐上心头,在这样的情绪笼罩下,他发出“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5](其七十)的玄学之叹便不足为奇了。
(二)对生命的珍视
咏怀诗中也多次体现出庄子“保全性命”思想。咏怀诗中不难见阮籍对“延年”的追求,如“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5](其十)“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5](其五十五)。可见对庄学养生论的认同,更可见阮籍对生命可贵的认识。司马氏昏暗的政治统治让阮籍对长生充满探求。“一为黄雀叹,泪下谁能禁”[5](其十一)的感叹,忧心自己身陷世俗罗网,更因为生命随时会被剥夺而常怀恐惧。“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5](其三十三),黄侃评:“知谋有限,变化难虞。虽须臾之间尤难自保。履冰之喻,心焦之谈,诚非过虑也。”[5]庄学的本质是生命之学,对自然和性命都有深刻的阐释。探求宇宙之道的首要条件便是《养生主》中一再强调的“保身”与“全生”,珍视生命才是获得一切思考和行为的前提。“纶深鱼潜渊,矰设鸟高翔”[5](其七十六)便是引用《大宗师》中的典故,以抒发自身对姓名难以保全之忧虑和身处黑暗中仍不愿同流合污之意愿。阮籍对自然生命的珍视也是作为其玄学精神的领袖,在认识到庄学本质后的实践。
(三)追求逍遥的心灵世界
阮籍对庄学的关注也使得八十二首中出现许多以游仙为主题的诗作,如《咏怀》二十三,“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六龙服气舆,云盖切天纲。仙者四五人,逍遥晏兰房。寝息一纯和,呼噏成露霜。沐浴丹渊中,照耀日月光。岂安通灵台,游瀁去高翔。”[5]这首诗以清丽的笔触描写了姑射仙人悠然自得的一天,诗中充满了对神仙不拘世俗,舒放自如的景仰之情,洋溢一派“羡仙”之情。道家的经典人物赤松子和王子乔也是他赞美的对象,“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5](其八十一)“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5](其八十)。阮籍在咏怀诗越传达出自己渴望无拘无束悠然自得的精神世界,越可见其现实中肉体的被束缚。晋书记载阮籍“至慎”,处在混乱高压的时局中,庄子逍遥物外,追求精神独立的宇宙观成为阮籍最理想的精神家园。阮籍将庄子笔下的“至人”“神人”“圣人”视作心中最圣洁的形象,是阮籍以庄学为基础所构建出来的对于其最完美人格的化身。咏怀八十二首中常见归隐诗,但司马氏是绝不会允许阮籍归隐。阮籍在认清现实的黑暗和残酷后,不屈的灵魂始终寻求解脱,将内心苦痛以游仙诗为掩盖,具有极致的飘渺和梦幻。以求如庄子一般泯灭物我,虚静超脱,不使心灵受到任何约束的境界,真正实现“遥顾望天津,骀荡乐我心”[5](其六十八)。
二、注重自由的意象选取与重神轻形的意象刻画
能够以一个真正自由的身份参与自然和社会中也是阮籍所渴望的,这份情志寄托在诗句之中则表现在他格外注重意象的选取。与前代作家相比,阮籍的《咏怀诗》创造了一个更高层次、更新境界的意象群,黄侃便感慨咏怀“独振奇文,兼包前体”[6]。
(一)自由翱翔的飞鸟意象
《逍遥游》中击水三千里,抟扶摇而高飞的大鹏,一直是人们无拘无束、冲破俗世的化身。阮籍《咏怀诗》中也数次利用“飞鸟”意象来抒发对自由的渴望。“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5](其四十三), “鷽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5](其四十六)诗中,阮籍化身飞鸟,不仅身体上得以自由,心灵上也得以解放。且《庄子·外篇·天运》有言“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4]。意在说明天性的东西不可改变,阮籍写鸿鹄海鸟,更有自托之意,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之心迹。飞鸟高飞振翅、远离尘俗,自由来去的特点,正为阮籍提供了释放心灵的具体渠道。道家的“鹏鸟”本不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正是因为其虚拟性却使之成为超脱自由意象代表,具有符号性。
(二)高洁不染的青云意象
另一个能体现阮籍对追求自由的意象便是“云”了。远离俗世,自由来去的青云纤尘不染,淡然悠远。阮籍诗中常用“云”以示逃离俗世之向往,如“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5](《咏怀》四十三);以及“鸣鸠嬉庭树,焦明游浮云。”[5](其四十八)都可见到《庄子·天地》中“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道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4]以青云载神思、修仙以超脱的无限遐想。
同时,阮籍还将“云”意象成为心中理想人格的修饰,如《咏怀》五十八,“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5]阮籍在此诗中刻画了一个高洁的人物,不仅顾谢西王母,更能与蓬户士弹琴相伴。通过描写人物冠帽入云衬托得气质俊朗不凡,多么疏狂潇洒。利用外貌与云结合来表现人物形象并非只有此诗,在《咏怀》六十二中,“裳衣佩云气,言语究灵神”[5]中将人物的衣衫与云气相互结合缭绕,给人飘渺梦幻之感。诗中人物遗世独立,再次将阮籍心中的理想人格展现在大众面前,而尾句“何时见斯人”更是阮籍对何时能够摆脱桎梏以求得真正超脱境界的呼唤和向往。这一切的祈盼和体悟,都围绕“青云”得以展现。
云和飞鸟本都是自然界常见景物,但通过阮籍的艺术加工,成为寄托诗人情感和志向的载体,反映了诗人的情趣和追求,不仅成为具有了象征力的景物,更为后世开创了“飞鸟”和“青云”意象运用新方式。
(三)重神轻形的意象刻画
咏怀诗意象的营造也可以见到庄学对阮籍的影响。《庄子·秋水》中提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4]可见在对待外物的态度上,庄子不主张“形”的逼真,而是强调“神”的丰富。外物只是人内心的反射,不应被过分重视。庄子“听之以新”“听之以气”的主张,就是强调人在认识事物时要重视挖掘自己内心想法,而所谓“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更是说明真正的物我融合是不具备明确的方式和界限,这种物我两忘不是诗人主观选择可以达成的。而正是这种不具备任何准备、构思、人为性的情感体验,才最符合庄子的美学理想。阮籍在他的诗中意象选择上也颇具“言不尽意”之特点。咏怀诗中他运用了大量比兴的手法。但与前代诗人选取比兴物象不同,阮籍在诗歌单句中往往选取指向性十分鲜明的物象,可将其全部诗歌整合后,他的感情表达却有了一种不确定性。如阮籍诗中“凤凰”这一意象,在《咏怀》二十二中是“明我心”的高洁之鸟,但在《咏怀》七十九中却指郁郁不得志的落魄名士。这样选取同一意象表达不同心情、不同内涵的例子在《咏怀》八十二首中屡见不鲜。这更体现出其受庄学影响后所表现出的飘渺玄妙,旨趣深远。
既然言和象只是表意的工具,在欣赏美的时候自然也要抛却外在的形式,这促使新的审美风格产生。这一点在阮籍诗歌中以女性形象的选取最为明显。如《咏怀》十九中,“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佩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闲,挥袖凌虚翔。飘摇恍惚中,流盼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5]
阮籍在诗中以及其飘渺的笔触,几笔便勾勒出一位圣洁的神女轮廓。但对于诗中出现的“佳人”意象分析各异,东方树就曾直白地表示不懂此诗所指。的确,历代文人对于女性形象地运用,或是臣子自喻以求君王垂怜,或写女性贤德用以规范伦理,或侧重刻画女性的容貌、服饰、体态动作等以表对美的追求爱慕。可阮籍笔下的“佳人”却十分神秘,美女的容貌连同诗人的情感都无定论。但正是这样朦胧的描写,恰恰符合了庄子笔下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4]的言不尽意思想。阮籍借风姿迷离的神女,表达自己在险恶政局下屈心抑志的忧愁。得到了“意”便忘记了“言”,自然也不会费心勾勒神女体态了。正与他在《清思赋》中所传达出的“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5]的审美观相一致。
三、《咏怀诗》中的批判性
《庄子》一书在阐述顺应自然、言不尽意等思想的同时,还有很强的批判性质,对社会要求的伦理规矩、道德规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道德不废,安取仁义。”[4]可见庄子对儒家礼乐教化是持批判否定态度的,儒家传统的礼乐制度若演变为统治者笼络人心的手段,就失去了其人性天然的一部分。使人们“经营利禄,争归而不知止”[4]。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便是循庄学而对“名教”完全的否定和批判。司马氏治下的“名教”,失去了仁义礼乐之初衷,残存其形而不能警醒人们遵守是非道德规范,与庄子提出“退仁义,宾礼乐”[4]的初衷相同。庄子也并非全然否定礼乐制度,正如阮籍并非排斥“名教”本身,他们提出的批判意在唤醒人们看清“名教”的副作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阮籍在《咏怀诗》中的批判是十分具有艺术性的,诗中常常出现利用自然景物烘托世俗险恶的句子,如“荆棘被原野,群鸟飞翩翩”[5](其二十六),李善注:“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猜测。”[7]可见阮籍虽用词斟酌严谨,但“刺讥”之意是不难看出的。阮籍轻视那些趋炎附势,攀附权贵的人,并将这些人称作“虱子”,如《咏怀》七十二:“修涂驰轩车,长川载轻舟。性命岂自然,势路有所由。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雠。更希毁珠玉,可用登遨游。”[5]
诗中提到名禄使人志向不坚,金钱使人心神不宁,这是违背自然天性的,为阮籍所不齿。尾句表达了阮籍渴望超越礼法的束缚,达到“不以物所累”的自然境界。
又如《咏怀》六十七中说:“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5]诗中对“洪生”这类徒有其表,虚伪奸诈的儒生批判。阮籍也曾在诗中多次抒发对功名利禄的漠视,“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5](其四十一);“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5](其六)若一味求外物而伤身害性,是不符合庄学明辨万物,善待自身的生命观的。咏怀诗中传达出的是阮籍在意识到“外物不可必”[4]后,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的心路历程。
阮籍也以自己现实种种行为表现对名教的批判,他身体力行的用一种纵情纵欲、完全不拘于世俗的生活方式宣泄他的不满。《养生主》中秦失不愿如社会既定的模式在葬礼上流露出逝者离去的哀悼,模式化的礼仪与表演性的悲痛与庄学死生无常的超脱相悖。只有被禁锢在名教框架下的“悦生恶死”之辈才会在丧仪上哭天抢地,惺惺作态。阮籍在母亲葬礼上酩酊大醉的行为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社会的礼仪规范的,但却是庄学的批判性实践。他用独树一帜的行为,切身传达出对当时统治者借“名教”束缚人性的不满,是对沦为了司马氏统治工具的“礼”的无声抵抗。
四、结语
综上,庄学对于阮籍的影响不止在《咏怀》八十二首中,也体现在魏晋时期文学、玄学、审美观等各方面。因此《咏怀》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气质、精神、审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咏诗》八十二首中无一不洋溢着对自由的渴望、对世俗的悲愤、和对更高层次精神世界源源不断地探索与向往。阮籍对庄学思想的重视也促进了玄学普及,成为当时文人群体的精神载体之一。清人刘熙载也曾评价:“阮步兵出于庄。”[8]庄学、阮籍给后世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一直绵延到今天,使人“陶性灵,发幽思”[3],焕发出极高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59.
[2]杨明照.订增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0:64.
[3]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23.
[4]王先谦.庄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162.
[5]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107-405.
[6]黄侃等.钟嵘诗品讲义四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2.
[7]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085.
[8]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7.
作者简介:
丛蓉,女,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至唐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