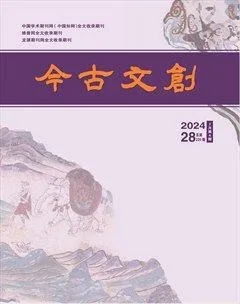梦呓与妄言
【摘要】荒诞性叙事,早在古希腊悲剧中便可窥见一斑,表现为对人类命运、生存条件残酷性与荒诞性的关注。经20世纪卡夫卡和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文学家之手,逐渐传入小说创作领域。《黄泥街》作为中国先锋派女作家残雪的处女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荒诞派的叙事风格,并加以作家自身独特的理解和创新,以超现实的笔法展现现实社会的精神危机。本文将着眼于《黄泥街》的荒诞叙事,分析小说荒诞色彩的具体表现和荒诞主题的建构过程,希望看到残雪对西方荒诞叙事风格的运用与创新,进而理解残雪小说独特的象征性和隐喻性。
【关键词】残雪;《黄泥街》;荒诞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2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09
残雪的小说向来被冠以“晦涩难解”的帽子。作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残雪在总体上继承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运用荒诞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象征直觉的手法写作。评论家称其为“唯一一个似乎不必参照着中国、亦不必以阅读中国为目的而获得西方的接受和理解的中国作家”[1]。残雪的处女作《黄泥街》以反现代的笔触,描绘出一种“破烂现实”的图景。小说中超现实的人物形象、光怪陆离的意象、虚浮难觅的叙事主线,都呈现出一种感官上的梦幻,透露出不折不扣的荒诞色彩。如何理解残雪小说的荒诞叙述,并通过相对可感的“荒诞性”解读抽象化的“现代性”,是我们读懂残雪小说的关键。
一、梦呓——现实与虚幻的交织
梦呓,在生理学上指睡眠中无意识的讲话。《黄泥街》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存在着对现实社会意义认知的缺失,因而常常将人生寄托于梦境之中。在《黄泥街》的序文中,作者在开头便写道:“那边上有一条黄泥街,我记得非常真切。但是他们都说没有这么一条街。”[2]这看似平淡的一笔却引人深思:“我”究竟是谁?为什么没有人知道黄泥街的存在?作为外来者的“我”又是如何了解到黄泥街的?作者对这些疑点全然没有交代,只是在最后点出:“有一个梦,那梦是一条青蛇,温柔而冰凉的从我肩头挂下来。”当现实与虚幻的界限逐渐模糊,甚至相互交织,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架构在便会在荒诞的背景色下自觉进行“蒙太奇”式的解构与重组,最终以非理性的状态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人的变形
《黄泥街》中的人物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甚至是“变异”。比如胡三老头整日坐在马桶上拉个不停;齐婆每天夜间去翻垃圾堆……黄泥街市民怪异的日常就在彼此间的注视下有序的运行,而对于他人的“变形”,他们或是鄙视嘲讽,或是接受模仿。久而久之,怪异变成了常态,常态却被视为怪异,一种荒诞的道德伦理体系在黄泥街得以构建和存续。
与外界的伦常体系相悖,赋予了黄泥街社会以很强的孤立性和排外性。在小说中,“我”和王子光是两个主要的外来人物。当“我”出现在黄泥街,并向市民问路,所有人都“向我瞪着死鱼的眼珠,没人回答我的问题”。而当王子光出现在黄泥街,立刻被视为“恶”的源头,成为瘟疫、水患、暴徒等一切灾难的令使。小说中,“王子光”变成了“王四麻”,寻找“王子光”变成了证明“王四麻”是否存在。黄泥街人擅长将自己无法理解的外来人、事转化为自己所能触碰或是感知到的存在,并对异己者展开“自恋式”的同化,从而缓解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在《黄泥街》中,“我”是一个概念化的隐性个体。在正文内容中,“我”只以“过客”形象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序文中,另一次是在全书末尾,且两次都是以“迷途者”的身份向他人“问路”。这里的“我”究竟是谁,作者并没有向大家揭示。但不难推断出:“我”并非作家残雪本人。纵观全书,“我”虽然没有以文字实体的形式出现,但却是黄泥街整个荒诞世界的见证者和叙说者。残雪创造了一个上帝视角的叙述者“我”,代替自己来“窥视”黄泥街的一切。“我”是故事的直接观察者,而作者则以“编辑者”和“剪切者”的身份出现[3]。在这一环节中,作者是占有绝对主导权的,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受叙述者的所见所闻所感,使自身的意志得以“投射”到作品上。因此,“我”虽然不能算是残雪的化身,却是残雪的代言,是帮助残雪将心灵视窗投向黄泥街的媒介。
(二)叙事的拼接
在常规的小说叙事中,作者会依据时间或是空间线索展开对小说世界的建构,这种“有线可循”的小说叙述模式自然、清晰,且遵循省力原则,无疑是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的。而作家也会慎重选用插叙、倒叙、补叙等方法,不会轻易让读者回读前页[4]。然而,这种适配于常规现实叙事的规程却在《黄泥街》的梦幻叙事中被打破和重造。小说中,残雪刻意回避“一叙到底”的常规叙述结构,转而将事件打碎混合,督促读者进行寻找、撷取和重组。譬如,叙述黄泥街拆迁流言一事,小说这样安排:
1.胡三老头在梦话中咕噜出“拆迁”二字;
2.齐婆和齐二狗讨论“机密文件”中提到的“拆迁”一事;
3.齐二狗因拆迁恐慌,在黄泥街散布流言;
4.区长前来调查黄泥街拆迁流言案件;
5.区长被齐婆吓走,流言调查不了了之。
首先,在这五个相关情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叙述鸿沟,在各情节之间,作者插入了大量的无关叙述来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读者往往读到后边便忘了前边,顾此失彼;再者,对于这些关键性内容的叙述,作者往往以一小段甚至是一句话的笔墨带过,过于平淡的书写难以回应读者追求刺激和精彩的阅读心理,因而常常将这些关键内容一扫而过,给读者后续对事件主线的把握造成更大的困难。在残雪的文学时间中,只有现在不允许过去的存在,这又像一场荒诞的梦境。梦,只有现在,没有过去[5]。
这种断续性叙事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要叙事线索的隐匿。在《黄泥街》中,我们隐约能够感受到贯穿叙述的重大事件——对王子光其人的寻找。但如果通读全书,就会发现,黄泥街上肮脏凌乱的景观、各色人物的怪异行为、大大小小的日常琐事等等,各种无意义的“虚笔”都在无形中稀释着读者有限的注意力,让读者无法将全数精力集中于对主线问题—— “对王子光去向的探索”。黄泥街上的人认为“王子光”就是“王四麻”,而“王四麻”就是“区长”,最后齐婆点出“王四麻”就是昨夜跳楼死了的那个人。对主线的荒诞化解读更增添了小说的虚无感和幻灭感。
二、妄言——灵魂与肉体的对话
接着来讨论《黄泥街》的叙述语言,笔者将小说的语言特点概括为“妄言”,并不是指残雪在《黄泥街》中的叙述皆是胡言的诳语,“妄”更多地体现在其荒诞性与自在性上。不同于传统小说,《黄泥街》的叙述语言并不急于向读者传递某种观点或信息,人物间的对话似乎也难以或者根本不打算起到信息交流和正常沟通的作用。事实上,不论是作者、叙述者、还是黄泥街的市民,他们都在“对自己说话”。他们将语言视为自在自为之物,但语言又从来不是自在自为之物,当灵魂发出的呐喊被一句“认清自己”所粗暴打回,灵魂与肉体就会发生冲突,叙述语言的荒诞性和怪异性也在内外矛盾的冲突下得以构建。
(一)审丑的秽语
与神经质的人格心态意象相对应,残雪的小说构筑了一幅丑恶、肮脏的人间景象。《黄泥街》中,残雪毫不避讳使用“秽语”来书写“秽景”。在《黄泥街》的世界观中,墙上可以生疮流脓,人身上可以长出蛆虫。宋婆可以不停地吃蝇子,胡三老头可以不分昼夜坐在屋檐下的马桶上。可以说,黄泥街的市民虽然在灵魂上保留了人的生存本能和情感活动;但在肉体上却逐渐被周围的环境所同化,堕落为污秽的信徒。基督教讲求灵肉两分,黄泥街的人便处于精神崇高和肉体凡俗的漩涡之中。但与基督徒肉体受难灵魂得救不同,没有人会充当他们的救世主,他们亦缺乏自救的能力。渐渐的,他们会将苍蝇蝙蝠当作美味佳肴,将随地屙屎屙尿当作生活日常。
一直以来,残雪小说的“秽语”都被学界视为“审丑”研究的重要材料,但大都将“审美”和“审丑”相互对立,认为审丑是审美的反面[6],其实不然。审丑是异化的审美,是波德莱尔式的“从恶中抽出美”。这种美感,不同于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优美”或是让我们心生敬畏的“崇高”[7],而是一种淡淡的同情与哀伤。龚曙光说:“残雪的小说绝非一味溢恶,如果我们坚持着终于没有被小说中的肮脏和恶臭窒息,那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一派朦胧温暖的夏日阳光。”[8]残雪在审丑道路上的探索、其荒诞的叙述风格,都在揭示着人性的弱点,引导我们以人为镜,关照自身,透露出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
(二)“无意义话语”的重复书写
在《黄泥街》驳杂的不明意义的叙述语言中,能够发现对人物话语的重复性书写。这些语言一部分对小说的叙事推进毫无作用,纯粹为了营造内容的无序性而设置;或是原本有作用,但在重复的叙述中便显得冗杂和多余。譬如,王厂长抱怨自己脖子上肿瘤逐渐恶化的病情,他的老婆说:“他这病很深了。”这句话在文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向医生陈述病情,而后两次并没有交代叙述的目的,可以纯粹视作厂长老婆的自言自语。到最后,她说了一句:“他这病不是很深了吗?”陈述句转换为问句。在间断的重复叙述中,黄泥街人仿佛是急于去确认什么,但最终却陷入对事象、对人生真实性的怀疑。他们对实体世界的构成和意义存在认知上的缺失,因而只能将自己的观点和判断由向外输出转为自我消化。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区长为调查王子光案件向胡三老头打听王四麻的身份。这里问话人的语言和被问者的反应都很值得玩味,区长问的是:“王四麻是不是一个真人?”相同意思的话在小说中重复了四次。值得关注的是,在胡三老头一次次转移话题、插科打诨式地打断和回复中,区长问话的自信心越来越弱,语气也越发得不坚定。最后,已经从最初的“王四麻是不是一个真人”变成了“你能不能证明王四麻不是一个真人”,黄泥街社会是容易让人“失心”的,外界人会被黄泥街所感染、所同化,直至对自身存在意义产生怀疑。
残雪在《黄泥街》中以女性特有的心灵视角,结合存在主义的视域,对人物的主体性情感进行挖掘。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曾在他的作品中写道:“如果有个声音向我说话,它是否是天使的声音还得由我自己来决定。谁能够证明这些声音确是对我说的呢?”[9]黄泥街上的人不仅不相信别人的话语,对自己的口吐之言尚存有疑心和戒备。他们机械地重复着无谓的话,却不知自己为何重复。在黄泥街这个相对独立的天地中,人变成了机器,人生变成了一串串冰冷的数据。残雪想要暴露的,正是黄泥街市民这样一种“存在即虚无”的价值思考。
三、回归荒诞——前进与彷徨的和解
《黄泥街》的难读,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小说情节呈现出有意的“反波折”倾向,导致我们难以从情节建构方面对文本进行深入的体察;另一方面,《黄泥街》并非传统的人物发展型小说,小说着力塑造黄泥街的人物群像而并不着力于刻画某一位主人翁。同时,小说各人物的性格、社会风貌在总体上并没有随着小说故事发展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整个黄泥街社会并不会因任何人的介入而发生转型。王子光、“我”、作者、哪怕是读者的参与,就像在名为“黄泥街”的水塘里投下一块理性的石,确能荡起阵阵涟漪,但不多时便回归平静,回归死寂与荒诞。
残雪的《黄泥街》,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学与现实的良性互动。残雪在《黄泥街》中展现出生命的虚无和精神的危机,投射到当时那个转型的年代,又有多少人将灵魂封存,给心灵上锁,愿意沉溺在虚无的梦境中一睡不醒,只靠时不时发出的“梦呓”向外界传递活着的信号。残雪也是从那段日子走来,叛逆的个性督促她用文字争辩,用文学进行表达,《黄泥街》的荒诞叙述就是这种夸张的现实展现和委婉的艺术讽喻的产物。
但荒诞并不代表绝望,《黄泥街》的创作动机也并非纯粹地揭露荒诞、书写绝望。生活可能会陷入彷徨和无意义的泥沼,但黄泥街的人却在荒诞的社会中积极创造生命的价值。S机械厂的运行、垃圾站的修建等等,虽然我们看到,这些“创造”仍充满了荒诞性,甚至可以说仅仅是人类瞬时热情的造物,但却是不可忽视的进步和改变。“当人生没有了意义,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前进?”这是存在主义哲学所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每个人应当去思考的人生之问。黄泥街的人们向我们展示了一条独特的救赎之路,即便多数是无用功。然而,只要肯迈出步伐,踏上行路,就不能说没有进步的可能。
四、结语
近藤直子评价,残雪是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开启了对‘黑夜’的讲述,将小说化作了黑暗灵魂的舞蹈。”[11]《黄泥街》以荒诞的笔法书写荒诞的人、事,揭示荒诞的主题,映射荒诞的精神社会,体现了残雪对于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存在主义式反思和深切关照。同时,残雪以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深入人物和读者心灵的沃壤,又给《黄泥街》佶屈聱牙的叙述和荒诞怪异的呈现增添了一分温润暖心的“人文关怀”,使人们能够与之共情。
要之,残雪的《黄泥街》以荒诞叙述写精神的虚无,叙人文关怀和价值反思。通过分析《黄泥街》的荒诞叙述的呈现方式,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体会残雪后现代主义式的写作风格,增强对残雪小说意旨的把控能力。同时,《黄泥街》也成为人们窥视先锋写作时期大众精神状态的重要窗口,深入挖掘,大家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残雪小说的女性主义和存在主义特征,体会残雪淡淡的、母性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戴锦华.残雪:梦魇萦绕的小屋[J].南方文坛,2000,
(05):9-17.
[2]残雪.黄泥街[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
[3]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4]邱怡.黑暗灵魂的舞蹈——评残雪《黄泥街7llVNnuFFusvYRHuAIGX9skjxf2RSX0J4vgsrUp3GPw=》的荒诞叙事[J].大众文艺,2023,(09):7-9.
[5]近藤直子.陌生的叙述者——残雪的叙述法和时空结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66-74.
[6]邱怡.黑暗灵魂的舞蹈——评残雪《黄泥街》的荒诞叙事[J].大众文艺,2023,(09):7-9.
[7]康德著.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龚曙光.对话残雪——暗影与光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9]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10]罗璠.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张学军.当代小说中的荒诞意识[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