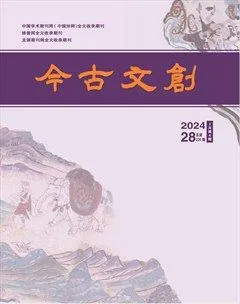《紫木槿》中家庭空间下的暴力与救赎
【摘要】《紫木槿》是非洲新生代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首作,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一个笼罩在殖民阴影下的尼日利亚家庭的崩溃过程。在作品中阿迪契建构了一组对照空间,其一是上述提到的充满暴力的规训空间,在作者的笔下,家庭不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欲望释放和暴力实施的行刑场,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成了施暴者的同谋,致使暴力主/客体出现了认知错位;而作者建构的另一个异质空间却具有文化包容和平等民主的特质,具有能够唤醒暴力客体的反抗意识,帮助暴力客体完成主体建构的功能。通过作品中的暴力演绎,作者揭示了宗主国的文化霸权,通过具有排他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使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知识被置于边缘地位,并在殖民地人民的身体和心理上留下了双重阴影这一事实。
【关键词】《紫木槿》;家庭空间;暴力;认知错位;创伤
【中图分类号】I4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06
《紫木槿》的作者是尼日利亚新生代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从伊博族女孩的视角讲述了后殖民时期一个表面平静和谐的尼日利亚资产阶级家庭空间内的“暴力”事件。在阿迪契的描述下,本应和谐的家庭空间成了权力场域,而尤金,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实则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殖民产品,选择通过暴力手段维持其权力和规训正常运行。在这个压抑、冷漠和撕裂的空间内,作为文化殖民手段之一的西方宗教成了尤金的同谋,致使暴力的主客体都体现了认知错位和身份焦虑现象。在整部作品中,作者主要建构了两类家庭空间,通过两个不同家庭空间的构建,反映了殖民历史和殖民经历对一个国家及生活在此的人民的深刻影响,而民族性文化能唤醒处于文化分裂状态的前殖民地人民。
一、家庭空间下暴力表现形式
暴力指“违背客体的意愿对身体进行伤害的行为”,其中不仅是实际的身体伤害,还包括了“引起歇斯底里等的举动”[1]。可见暴力对于受害者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紫木槿》中,阿迪契将目光聚焦于尼日利亚资产阶级家庭内部,重点描述了家庭中的暴力事件。在这个家庭中,父亲尤金是一位具有双面性格的人物,在外表现为慷慨大方的资本家和宗教信徒,但在恩努古家庭空间中,却对家人施以暴力以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阿迪契对于这个家庭空间的描述体现了家庭空间的政治功能,尤金便是利用家庭空间的政治特性对家人进行规训。能容纳上百人的空旷院子,二楼看不到外面街道的高墙,墙上缠着电线圈[2]8,外面的一切目光均被阻挡在高墙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空间断然地同社会空间隔离开来。在家庭空间生活的人们,摘下对外的社交面具,变得放肆而真实。
家庭空间是社会空间特质的一种投射,也是父权的容纳场所[3]164。作为家庭中的掌权者,尤金为了维护天主教的地位和避免权力的失落,选择残忍地对他的家人使用暴力,殴打妻子至其多次流产;在妻子比阿斯特丽斯因为怀孕身体不适表明不想陪同尤金去拜访白人神父本尼迪克特之后,在卧室对其实施暴力;因为儿子扎扎未在初次圣餐礼中考到第一名便打断了他的小拇指,以至于那关节扭曲的指头,像一支干棍子一样变了形[2]16,在未告知他的情况下,一双儿女与他们的祖父(被尤金看作异教徒)在姑姑家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尤金便用滚烫的热水烫伤他们的脚作为惩罚;在发现康比丽私自收藏祖父的画像时,对其实施残酷的暴力惩罚,导致她的内脏出血,肋骨断裂。借助身体惩罚手段,尤金确立了家庭空间中的地位和权威性的话语权。在尤金的暴力统治下,一家人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
尤金的这一系列身体暴力背后的推手是西方殖民者的文化暴力。曾经殖民者为了使殖民地人民归属而使用的宗教手段,成了尤金的同谋,为其暴力行为提供了合法说辞。殖民和霸权对后殖民时期尼日利亚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尤金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上。他是一个被白人文化改造的黑人,也正是法侬所描述的戴着白色面具的黑人。尤金强迫康比丽等人信奉天主教的过程,就是西方殖民者向非洲传播宗教的隐喻[4]。尤金对“白人性”的追逐可以从他对英语和天主教义的狂热追求,以及他对信奉不同宗教的父亲和岳父相反的态度中得以显现。无论是在私人还是公共场所,尤金几乎不说伊博族语言,他也不允许他的儿子和女儿在宗教仪式和公共场合讲伊博语。因为接受了殖民者白人和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宣扬,殖民地人民受到“自卑情结”的影响,以至于黑人失去了对自身种族身份的理解和感知。黑人把自己想象成白人,并且无意识地拒绝和憎恨任何有关黑人的东西,甚至否定整个黑人身份,这就是黑人认知异化的过程[5]。在天主教宗教戒律下,家人的正常生活受到压制,尤金狂热地信奉基督教,坚持一种“清教徒式”的极端僵化的宗教教规,整个家庭都处于他和天主教教规的极端控制和规训之下,尤其是他的孩子,他们的房间不允许上锁,所有房间的钥匙由尤金管理,为的是便于监管家人,并约束其行为。孩子们每天的生活被尤金规定的时间表所分割,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康比丽被禁止穿裤子,家庭空间内不进行任何娱乐活动,卫星电视、立体声响和那些黑胶唱片永远没有使用的时候,整个家庭空间处于一种压抑的沉默中。当尤金对妻子家暴至其流产后,要孩子们念诵十六种不同的九日敬礼祷告,以求得上帝对母亲的宽恕[2]29。尤金以宗教之名为他的暴力行为正名,使具有伤害性质的身体暴力行为合法化。他的暴力行为以西方宗教暴力为依靠,在精神和身体上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了不可消磨的创伤。
二、暴力主/客体创伤体验和认知错位
阿迪契描述了家庭暴力对尤金家人的伤害,然而在这段暴力关系中,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作为暴力客体的尤金的家人,尤金作为家庭空间的暴力实施者,在对家人进行身体伤害时,同时也体现了内心的冲突与煎熬,遭受着一种“同构性压迫”。阿希兹·南迪将“同构式压迫”描述为压制关系中主/奴、殖民/被殖民、施暴者/受害者等共同体验着的异化和心理损伤[6]。过去的创伤经历导致尤金在对家人施行暴力的过程中,表现出歇斯底里的复杂情绪,并在惩罚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和痛苦。在他每次对妻儿进行身体惩罚后,他的眼睛又红又肿,泪流满面,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恩努古的家庭空间掩盖了殖民主义在场,将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立掩饰为家庭伦理。在经过殖民暴力后,尤金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与殖民施暴者产生了共情心理。当一双儿女在与被视为异教徒的祖父一起生活的事情被尤金发现了之后,他采取了与白人牧师相同的暴力行径,用滚烫的热水将儿女的双脚烫伤。曾经被白人殖民者用来惩罚黑奴的手段,在后殖民时期被黑人用来对自己的后代施行惩罚,体现出殖民经历对被殖民地人民的影响之长远、之深刻。在家庭空间中,过去的殖民创伤和对孩子的父爱相互碰撞冲击,导致了尤金歇斯底里的情绪,处于西方文化与血缘亲情的冲突之下,尤金必然的结果便是精神认知上的扭曲和实施暴力时内心的煎熬与挣扎。
尤金的暴力行为,导致了殖民创伤在家庭代际间的传递。康比丽作为尤金身体专制的对象和西方宗教暴力的客体,失去了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能力,在冷酷的宗教规则之下,她成了被动的接受者,面对家人及自己被伤害的事实,她没有去深入思考的能力和辨别能力。在家庭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康比丽处于暴力和亲情的双重张力之下,对于父亲的暴力行为出现了认知错位现象。“It landed on Jaja first, across his shoulder...I put the bowl down just as the belt landed on my back.He swung his belt at Mama,Jaja,and me.We did not move more than two steps away from the leather belt...”这个情景描写了尤金对一家人实施身体暴力的场景。在这一段文字当中,作者将关注点聚焦于尤金实施暴力行为所使用的武器——皮带,在这一段落中,具体描述尤金的暴力动作的小句共有五句,其中物体为主语的句式共有四句,均以无生命之物充当主语的句式现象体现了作者认知模式的偏离,在这一段落中只有一个小句的施事者是父亲,而对于主要暴力过程的主语却是第三人称物体主语it和belt,从句法上来讲,康比丽作为叙述者隐藏了真正行动主体,将无生命之物作为主语,表明了叙述者当时的认知心理,故意忽视了爸爸作为真正施暴者的事实,作为一个13岁的孩子,康比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父亲暴力行为背后的深刻内涵,由此显示了在一个撕裂的家庭空间下青少年的认知异化现象。
在恩努古家庭空间中,她同时遭受着父权制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生活在这种压力下,她几乎失去了正常表达自己的能力。她从不主动和其他人进行社交活动,也无法以正常的方式与他们交谈。加布丽埃·施瓦布(Gabriele Schwab)曾提到,无名的恐惧可能使受到创伤的受害者沉默,甚至使他们陷入失语的状态[7]。在回答同学和家人所提的问题时,她最常见的回答只是“是”和“哦”。一旦她说长句,她就会结结巴巴,甚至不能以正常的音调表达,说话像是低语,这些行为都让她周围的人觉得她很难相处。由此可见,康比丽的话不作用于任何人和物,也无法产生语言应该产生的效力,作为暴力行为的见证者和受害者,康比丽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创伤症候,严重地影响了她的社会生活,使她沦为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人物。在恩苏卡,当姑姑一家人在讲述伊博族的传统故事时,她不能像他们一样表达自己对故事的看法,因为这一行为是她父亲和这个家庭所信仰的一元论基督文化所不允许的,面对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她失去了欣赏和表达的能力,处于文化“失语”状态。斯皮瓦克认为,自身话语系统的破坏使人们“不能说话”这一现象不意味着他们在生理意义上失去了发音的能力,而是指他们不能进行思考和文化表达,进而无法用自身的话语体系建构主体性、文化身份和观念形态[8]。“而沉默和说话困难是遭受创伤者的共同特征”,当被姑姑问到对于父亲不允许孩子们来看祖父行为的看法,首先出现在康比丽头脑中的是祖父的异教徒身份,在尤金的影响下,康比丽以一种二元对立和主体性思维看待对于祖父的身份,异教徒是祖父唯一的身份,除此之外的一切身份,包括血缘亲情,都被此所掩盖。
受到殖民文化侵蚀的尤金,通过对家人实施暴力的手段,将殖民创伤传递给家庭的下一代。而帝国文化霸权为尤金的暴力行为提供了话语场,使其暴力行为合法化,在这个话语场中,西方天主教处于主体地位且具有排他性,本土宗教文化皆处于附属地位。康比丽被置于英国帝国主义和非洲本土间的尴尬地位,她看不惯来自宗主国牧师的做派,但她也不能适应与本土同伴的和谐关系之中。她的思想受到西方宗教文化的统摄,而又不能与传统文化完全断离,从而在造成一种思想上的既不属于“此”也不属于“彼”的本土流散状态[9]。
三、对照异质家庭空间的创伤修复功能
作家将恩努古家庭空间建构为暴力的空间,除此家庭空间之外,作者还建立了另外一个与之对照的家庭空间。并且赋予这个空间以重要的修复功能,“也许我们去过恩苏卡之后都变了,事情注定要发生变化,秩序注定要被打破”[2]165,恩努古家庭空间所体现的静止僵化状态在恩苏卡之旅后开始改变。作者通过主人尤金扭曲的性格强调了殖民主义所倡导的“白人至上”对被殖民地人民的影响。而叙述者康比丽在恩苏卡家庭空间的转型过程,则凸显了本土民族性文化对创伤群体的治愈力量。恩苏卡是霍米·巴巴所提出的“混合空间”,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处于动态的互动融合状态[10],伊菲欧玛的家庭就是这个混合空间的具体缩影。在物质空间中,姑姑家的空间陈设打破了空间的政治性,同一个空间承担多种功能,从内部瓦解了家庭空间的秩序和规训功能。客厅不再是父母对儿女进行规训的场所,反而承担了吃饭、做弥撒和家族代际间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
而在文化空间中,姑姑一家也是基督徒,但他们选择将基督教本土化。伊菲欧玛姑姑的家庭呈现出一种包容和杂糅的文化氛围,这一点可以从家庭内部的家具摆放看出,桌上画着身着和服女子的东方花瓶、播放着本土音乐家的音乐、画着深色皮肤的圣母和圣子的水彩画和穿插着伊博族歌曲的玫瑰经。康比丽的姑姑倡导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和谐共存,平等民主的家庭氛围令康比丽开始反思父亲的控制,并试图冲破父亲锻造的家庭牢笼。在混合空间里,康比丽接触到了非洲文学、非洲的当地音乐、传统的节日仪式,在黑人传统文化的力量下,康比丽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摆脱了文化“失语”的状态,在姑姑家,她开始大声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开始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重新将自身与本民族的文化纽带相连。在这个混合空间里,康比丽通过接触之前从未被允许接触的非洲传统文化,重新获得了建构自己文化身份的机会,通过对于本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回顾,康比丽开始了身份建构之旅。伊菲欧玛姑姑是恩苏卡大学的非洲学研究教授,身为非洲学研究学者的伊菲欧玛看到并接受了混合多元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终因政治迫害,伊菲欧玛带着孩子移民到美国。通过伊菲欧玛这个人物经历,作者表明了即使国家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殖民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前殖民地人民仍然因为某些原因被迫踏上异国流散之路。
四、结语
通过将目光聚焦于尼日利亚家庭内部,阿迪契向世界揭示了在后殖民时期,即使殖民已经结束,但是,殖民主义仍然以另一种形式在场影响着前殖民地的人民的真实境况。尤金的暴力行为将殖民创伤转化为家族代际创伤,通过暴力的呈现,作者揭示了宗主国的文化霸权,通过这排斥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使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知识被置于边缘地位,并在殖民地人民的身体和心理两个层面,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在漫长的殖民历史中,以语言和宗教为代表的帝国霸权文化,对殖民地的本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康比丽从恩努古到恩苏卡的旅程,可以看作是身份建构之旅,亦是从西方宗教一元论跨向多元文化融合的一段旅程。除了宗主国的殖民侵略,非洲社会长期存在许多民生问题,战争、饥荒等肆虐这片大陆,使得本土作家在关注殖民遗留问题时,也注意到了底层叙事的重要性[11]。通过家庭空间的暴力演绎,阿迪契重建了社会中受压迫角色的主体性,并且帮助其重新发声。
参考文献:
[1](英)保罗·洛克利.走出婚姻暴力的阴影[M].刘稚颖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2](尼)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紫木槿[M].文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4]袁俊卿.“新非洲流散”:奇玛曼达·阿迪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J].非洲语言文化研究,2022,(02):1-24.
[5]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M].New York:Grove Press,1967.
[6]陈李萍,陶家俊.后殖民视野中主/奴范式的文学表征——论《黑暗之心》与《蝇王》的双层结构及其裂变[J].外语教学,2010,31(03):68-72+76.
[7](德)加布丽埃·施瓦布.文学、权力与主体[M].陶家俊译.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11:149.
[8]李应志.认知暴力[J].国外理论动态,2006,(09):60-61.
[9]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07):
135-158+207.
[10]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4.
[11]朱振武.马克思主义与尼日利亚本土流散作家[J].外国文学,2023,(03):4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