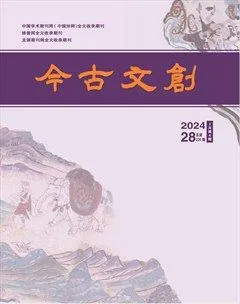神话原型视域下《等待戈多》的精神隐喻
【摘要】《等待戈多》里有着众多意义悬置的信息碎片,笔者经过对《等待戈多》文本的反复细读,联系诺斯洛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分析其六位主要人物的圣经原型,并进一步通过原型分析《等待戈多》对当下人类精神世界整体图景的隐喻式书写。在《等待戈多》更深层的隐喻图景中,戈戈/耶稣隐喻着人类的自由精神,狄狄/先知隐喻着人类的理性智慧,幸运儿/人类隐喻着人类的物质存在,波卓/假上帝隐喻着人类创造的精神偶像,戈多/真上帝隐喻了人类实现超越性的可能性,孩子/天使则是沟通超验与现世的纽带和联系,戈多的不在场是对超越性精神的解构,暗示着期望得救的不可能,而以开放又循环的戏剧结尾表明未来的不确定性,宿命感的悲观与未确定的希望交织,将根植于人本能深处的依赖冲动与超越性的自由欲望间的强烈张力诠释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等待戈多》;贝克特;诺斯洛普·弗莱;圣经原型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03
一、原型、神话与《圣经》
作为神话原型理论的集大成者,弗莱的“原型”的概念不同于创始人卡尔·荣格所认为的“集体无意识”,而是摒除人类学的影响,试图把原型完全置于文学的视野下。弗莱的“原型”是一种固定的文学程式,它包括同类主题、结构和意象的所有要素。而所有文学的脉络的起点一定就是“神话”。神话是无可取代的,是构成一切思维的框架和语境,神话是无法被完全驱逐的。
从文学一体的宏观视野来看,神话就是文学最初和最根本的原型。但要注意的是,弗莱的神话原型是形式性的,包括它的语言模式、意象结构、叙事结构等。在神话中,弗莱最为推崇《圣经》,认为《圣经》在文学的视野中就是西方文学的最本原的神话原型。对于弗莱而言,正如《圣经》无法脱离整个西方文明而单独存在一样,其理论最主要的两个核心概念—— “神话”与“原型”,都无法独立存在于《圣经》以外。在弗莱的著作中,《圣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他认为,《圣经》是一个浩瀚的神话集,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含着语言结构、意象结构、叙事结构的所有原型,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等待戈多》属于文学模式循环的反讽一环,反讽意味着超感官根基的缺失,认识和感受形成了断裂,个体与自我、他人和世界都形成了难以弥合的隔离感。反讽文学采用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指东说西”,它往往利用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意象叠加的方式,使两者之间的联系产生悬挂,进而形成一个流动的隐喻结构。借此外层的隐喻框架得以跨越理性思维及传统说教语言所无法涉及的层面,并与深刻的内在精神进行对话。借由人与神之间的矛盾对抗,反思现代人内心所存在之神灵缺失以及物质需求突增的精神状态,以及隐藏在理性生存假面下,人类实则一直生活在神话中的生存本质。
二、《等待戈多》人物的圣经原型
(一)弗拉第米尔和爱斯特拉贡:先知与弥赛亚
弗拉第米尔(狄狄)和爱斯特拉贡(戈戈)是《等待戈多》的中心人物,整部剧本中充斥着两人大量的看似无意义的行为和对话,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大量意识流的线索随意穿插在文本中。在已有的神话原型批评分析中,两人是人类的代表,然而笔者认为,弗拉第米尔以其审视的思想和忠诚的姿态,隐喻身份是圣经中的先知/信仰者,而爱斯特拉贡以其既低下又高贵的双重地位和独有的悲悯态度,隐喻身份是圣经中的耶稣/精神拯救者。
戈戈和狄狄的舞台身份是两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世俗王权中,权威者不可能既是国王又是乞丐;但在宗教领域,许多宗教的宗师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流浪汉,不管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譬如佛教的释迦牟尼、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孔子,也包括圣经中记载的犹太教的弥赛亚或是基督教的基督。弗莱认为:“一方面,大多数宗教的根本目的在于重新塑造社会群体,使它们建立在一些个体影响上,如:耶稣、佛、老子、穆罕默德,或者至多一个小群体。这些传道者以自身来表明他们代表着一个群体,而不是群体代表他们。”流浪汉的身份正是为着人可以从社会中脱离而出,真正彰显个人的存在。
戈戈在入眠时常常重复做一种相似的梦境,但每当他企图向狄狄述说时,却每每遭到极度恐惧的拒绝。按照以往学者分析,二人的象征身份是人类,这显示了人类主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通壁垒,由此推断,人类间往往拒绝真正、有意义交流的态度。这诚然是一个合理的解读,但若进一步思索,普通的梦有什么“受不了”的呢?戈戈每每梦到便惊醒正表明戈戈的梦是不同寻常的,终于,在最后一次做梦惊醒时,戈戈控制不住地呼喊出了这个噩梦——坠落。对现实的所感所思化为一个具体而强烈的符号在梦中出现,这一令狄狄恐惧至不敢倾听的梦境终于得以传达给读者,戈戈的坠落意味着耶稣的坠落。在圣经中“记载”耶稣曾从天堂坠入人间,又坠入地狱,完成拯救后升回天堂,从而完成了圆形的闭合运动。但当前此坠落,实质上体现了信仰的沦丧,象征信仰失去其神圣性而沉沦入淤泥。狄狄的恐惧正表达了对心灵信仰的不堪跌落之惧。
在一次争吵中,戈戈说:“要么就干脆把我给杀了,像别人一样。”
狄狄:“哪一个别人?(略顿)哪一个别人?”
戈戈:“像千千万万别的人那样。”[5]101
被“千千万万别的人”杀死的戈戈正隐喻着耶稣之死。耶稣是被犹太祭司处死的,但在弗莱看来,耶稣是被所有人包括基督教信徒们一同杀死的,基督教是建立在一个被当作渎神者和社会危险分子而处死的先知(耶稣)之上的。他对抗社会,预见未来,并经受痛苦,被社会杀死。他的行动与结局表明,人必须靠自我奋斗摆脱历史而不只是从历史中醒来,而到目前为止的任何社会都无法接纳一个完整的个体。
(二)波卓和幸运儿:上帝和人类
波卓不止一次地被戈戈指认为戈多,但每次都被狄狄反驳,语气确凿肯定,从而也给读者传达了同一信念:波卓不是戈多、波卓不是上帝。但排除狄狄武断的否认,种种蛛丝马迹都在暗示着波卓和幸运儿的真实身份:上帝和人类。
波卓和幸运儿的主仆关系怪异而离奇,波卓无情地奴役着幸运儿,却又极度依赖和害怕幸运儿。幸运儿看似事事服从波卓却不再服务慰藉波卓的心灵,因为幸运儿的不作为,波卓只能请求戈戈请求他坐下。波卓是个被宠坏了的暴君,就像上帝一样。世事变迁,幸运儿则从主动的供养变为被动的服从,就像人类一样。
幸运儿之姓名与境遇截然相反,名为幸运却受着奴役,但他却浑然不觉,反而乐在其中。简单一个设置已是辛辣的讽刺,人类虽然追求自由和平等,自以为受到上天眷顾,但对自己和别人受到的剥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沉溺在幸福的幻象海洋,不愿挣脱。
幸运儿因年岁极高而显得衰老,有着长长的白发。相比波卓、戈戈、狄狄,他是如此衰老,这正象征着人类存在时间之久远,远超他所崇拜或信仰的偶像和领袖。但如今,人类的生命力也从春天走向了冬天,曾经生命可以自由地起舞,“以前,他跳过法兰多拉舞、埃及舞、法国摇晃舞,快步舞、凡丹戈舞,甚至跳过水手舞。”[5]64现在却变得衰弱苍老,丧失活力,僵硬麻木。
幸运儿应波卓要求,办了两件事情。第一,跳舞。“幸运儿跳舞。他停下来。”他的舞蹈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一个“词语”。对于幸运儿舞蹈的阐释命名,共有四种视角:戈戈、狄狄、幸运儿自己和读者。戈戈的猜想是:“《点灯人之死》”。“点灯人”从广义的含义来看,其奉献性和独一性都与耶稣有相似之处。“点灯人之死”更像是一种牺牲。牺牲本质上属于替罪仪式,在原始部落便已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耶稣被基督教所赋予的就是“替罪羊”的价值,因此他的猜想属于合理地以己推人,这是其隐喻身份的另一例证。狄狄的猜想是“《老年人之癌》”,狄狄下意识地认为他是因为衰老、动作迟缓,才无法起舞。它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生存现状的认知和领悟,人类没落的根本原因不在外在的束缚,而在生命力的衰竭,感性力量的丧失,在“不再起舞”。他们两人都猜错了,幸运儿舞蹈的正确答案是“《网之舞》”。“他以为自己陷入了罗网。”[5]49幸运儿以为自己“陷入罗网”,隐喻的是文明的罗网。许多反思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们都像幸运儿一样,认为问题的根源在文明的制度中,渴望挣脱文明的束缚而重返自由。
第二,思想。幸运儿的长篇演说没有标点,词汇使用混乱,毫无逻辑。有学者认为这象征了现代人因接受了爆炸式的信息而导致了思想的破碎和思考能力的萎缩。笔者则试图从另一角度出发,不着重“破碎”,而着重“统一”所呈现的信息。这段文本的书写以上帝开始,以上帝结束。尽管其逻辑结构存在混乱,但从整体的叙述角度来看,它实质上具有一篇布道文的表现特征,诸如“耶和华在那高高的山上”。然而,预期传统的赞美上帝之爱的颂歌相比,这段演讲却是一段充满着残酷无情预言的呼喊。我们在混乱的文本中抓住关键词,会发现“但时间将会揭示”一共出现了4次,“不知什么原因”出现了10次,“衰弱萎缩”出现了4次,并且出现了许多物品名。如同翻译预言的乱码,经过分析重组,依笔者分析,此一句子所概括之含义为:时间流逝的过程中,人类在物质领域所追求的进步均无法承受时间的考验,最终所有人事均将进入入衰败及减毁的状态。人类既无法了解此一现象的成因,更无力改变这残酷的命运。这一最终归宿使人联想到《圣经》的末日以及时间的终结。
第二幕再上场时,波卓已失明,幸运儿已失语。波卓的失明隐喻了主仆关系的颠倒。最开始波卓掌控着绝对的权力,但他失明后,不仅难以准确鞭打惩罚幸运儿,而且难以决策行进的方向道路,实权转移到了幸运儿手中。幸运儿的失语隐喻了行动和真正的思考将要取代浮于表面的言语。行动与言说在常识认知中是二元对立的,一方的增长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消减。最开始,幸运儿不能跳舞,却能长篇大论地演讲。而现在,他不再能说话,但或许正预示着其思考能力的回归和对自己生命的重新掌控。
(三)戈多和孩子:上帝与天使
戈多的圣经原型是上帝这一观点已被学界进行了充分阐释,并得到了普遍接受。需要补充的是,戈多在剧本中处于不在场状态,其上帝形象在文本中的明显线索,如胡子是白色的,两个孩子为他放羊(牧羊人)等,都是由孩子传递的。孩子充当了戈多的传声筒,而圣经中的天使意象往往象征了语言交流,天使是为上帝传赐圣经的使者,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孩子的圣经原型就是天使。
三、《等待戈多》的精神隐喻图景
神话阐释的真正价值在现象学维度方得以展现,《等待戈多》是基于圣经原型的现代人类精神现状的缩影。贝克特将人类这一难以言说的复杂对象进行拆解,剥离出不同的元素,并将其化为具体的分身角色,上演了这一出隐喻性极强的戏剧,在《等待戈多》更深层的隐喻图景中,戈戈/耶稣隐喻着人类的自由精神,狄狄/先知隐喻着人类的理性智慧,幸运儿/人类隐喻着人类的物质存在,波卓/假上帝隐喻着人类创造的精神偶像,戈多/真上帝隐喻了人类实现超越性的可能性,孩子/天使则是沟通超验与现世的纽带和联系。
戈戈和狄狄是一对个性迥异的朋友,戈戈喜欢自说自话、行事随心所欲且性情阴晴不定,狄狄则相对显得更加沉稳理智、喜欢思考讲道理,二人分别是人类的追求释放自由与追求克制理性的两种精神追求的拟人化形象。二人徘徊在荒野之中,四面寂静,空无一人,他们是被驱赶来的,被抛弃来的,他们也曾有过好日子,也曾有过被尊崇的时候,但现在世界变了,是人类自己抛弃了人类的自由精神和理性智慧。
幸运儿是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现实存在的拟人化形象,幸运儿曾经也是威风凛凛、机巧可爱的,担得起他的名字,但他现在却虚弱衰老、僵硬麻木、破破烂烂像个乞丐,这正是对经历了一战、二战的人类物质存在的形象书写。幸运儿的演讲初看只觉恐怖,而另一方面,意象引发的火花构成了一种不同于流俗时间的本真时间,双双塌陷于现在的过去与未来已经终结,现在构成了一种统摄性的同时性观念,存在着时间的原型,过去未来统统消减,当下也就实现了永恒。
波卓和戈多的圣经原型都是上帝,但二者不可等同而语。波卓不是真正的“上帝”,只是被人创造的一个“偶像上帝”,代表着人类文明创造出的各种偶像。《圣经》谴责偶像崇拜,其谴责的正是它所使用的意象在外部世界的反映。摩西诫命曾言:“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出埃及记》20:4-5)创造并侍奉诸如波卓这样的虚假偶像不过是人聊以自慰的谎言,是人对责任的惧怕与躲避,它们凭借着人类的崇奉和供养丰满健硕,奴役着自愿被奴役的人们。
剧中从未现身却存在感最强的戈多才是真正的“上帝”,或者说是人类实现超越性的可能性。《旧约》明确表明:上帝永不现身,凡见过他的人必遭受死亡。而《新约》中耶稣则表示上帝是他自己能量的看不见的源泉。上帝显现是一个伪命题,“等待戈多”也是个伪命题,因为“上帝”非实非虚,戈多也没有实体形象,而只有“名”。问题的重点从不是见到上帝或是戈多,而是要“打通人的个性和象征着人的个性无限延伸的神的个性之间的界限”,要使人的可能性由此得到无限的延展。幸运儿凭借崇拜想要获取无限与超越的精神力量是痴人说梦,而只能把自己锁死在波卓这种宗教偶像的手里。戈戈和狄狄一再等待戈多,但他永远不会来,也不可能来,因为戈多并非独立存在,而只是代表一种可能性。唯有戈戈狄狄重与幸运儿联手相助,人类开始重拾理性精神,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不再试图有任何依靠或推脱,勇敢地面对自由,那么真正的解救才将到来。
弗莱将《圣经》中的“原罪”看成是“人类对自由的惧怕,对自由所带来的原则和责任的惧怕”。赎罪、解救则相对的,隐喻着人类的自由、理性精神的真正实现,人对生命自身的真正负责。在戏剧的最后,波卓依然失明,戈多却仍被等待,何时人类能不再等待戈多,使幸运儿和戈戈、狄狄相认合一呢?狄狄最终戴上了幸运儿的帽子,也许这是个好的开始。
参考文献:
[1](加)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Northrop Frye,Fables of Identity:Studies in Poetic Mythology[M].New York,Hareout Brace and World,1963.
[3](加)诺斯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英)詹姆斯·诺尔森.塞缪尔·贝克特:盛名之累[M].王雅华,刘丽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5](英)萨缪尔·贝克特.贝克特全集16:等待戈多[M].余中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6]饶静.中心与迷宫:诺斯洛普·弗莱的神话阐释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法)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姜宇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