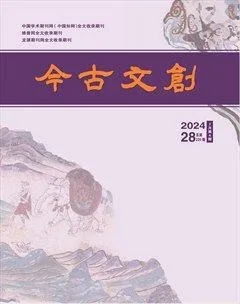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与上海文化的距离
【摘要】《长恨歌》作为描写上海转型期的小说,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能够集中反映上海地域文化的经典作品。王安忆在写作中,明显带有书写宏大历史的冲动,其主要人物王琦瑶作为上海命运的同构体被赋予深刻的历史意义。然而,自身经验的匮乏,使得作为代言人的“王琦瑶”与真实的上海文化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割裂感。
【关键词】《长恨歌》;王安忆;上海文化;王琦瑶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8-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01
《长恨歌》作为一部长期以来被当作描写上海城市文化的读本,其城市主题成了历来人们研究和关注的对象。王安忆在采访中谈及《长恨歌》,称其为一个城市的故事,“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1]。归根结底,为上海这座城市画像、剖析上海的文化精神是王安忆致力之所在,但是王安忆想象中的“上海”与现实的上海是否严丝合缝、不差分毫?她对上海文化的展示是否又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偏离?本文从探寻上海文化出发,与王琦瑶的形象进行比较,旨在揭示王琦瑶与上海文化之间存在的距离,进而思考《长恨歌》在对上海文化表现上存在的偏差。
一、上海文化的界定
长久以来,《长恨歌》被认为是展示上海文化的权威读本,那么上海文化究竟是什么呢?陈思和在答《上海文化》问时,指出上海主要有三种文化构成:“一是海派文化(新市民文化);另一则是石库门文化(上海市民文化);另外一种则是上海本土文化,此则与江南文化相关。”[2]
陈伯海先生曾经提出:上海文化的底子是古代吴越和明清江南文化。人杰地灵的江南孕育了上海文化中务实理性、开放包容、精致柔美的一面。南宋以后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反映在文化中便形成了讲求实利、重商业的一面。它不像北方社会偏于保守,又鲜有南方沿海一带的排外心理。这些都为上海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五口通商,上海一骑绝尘,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外,与其良好的文化根基也是分不开的。
海派文化的形成,与上海开埠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移民文化有很大的联系。随着上海开埠,上海从一个封建的商业城镇一跃成为我国近代最大的商业都市,帝国主义纷纷进驻上海,外来殖民的入侵与扩张,使得外来文化的加速传播,“……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蓝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 ①。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外国文化和文学作品的翻译、西洋学堂的建立与教育等,使上海在引进和自觉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特点。
随着上海现代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的建立,作为东方魔都的上海,吸引力与日俱增,西方的冒险家、各省市民的大量涌入,连同孕蓄的进步力量一起,使这个城市呈现一种激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不同人口、人种的交流碰撞融合,使其文化混杂的属性愈加明显,一种象征着多元开放、勇于开拓、追逐新潮但文化根底薄弱的海派文化由此建立。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原住民,以他们为代表的石库门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既相互和谐又有所不同。在半殖民地现代管理制度下形成的上海市民文化,俗称“石库门文化”,他们追求文明秩序、讲求精致生活,强调聪颖好学,行事谨慎精明。而以普通小市民为主体的石库门文化,就形成了其功利性、世俗化、消费性的文化倾向。格局和眼界都比较狭窄,是一种相对内敛、狭隘、保守型的文化性格。
可以说上海就是在这三种文化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了其多元开放、兼容并包、勇于进取、务实理性、精致柔美的文化倾向。需要多加注意的是上海文化本身就具有多元性质,而这种“多元”本身就意味着其文化内涵的立体和丰富,就像一个万花筒,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观察方式,看到的画面都是不同的。由上海这座城市培育出来的上海文化并非纤尘不染,丝毫不受坏习惯、坏风气的影响。也并非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建于苦难上的末日乐园。其善与恶、美与丑、高雅与世俗、崇高与卑下、进步与落后都是相伴相生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多面体”,因此,单独强调其文化的哪一方面都是不准确的。
二、作为上海文化精魂的王琦瑶
作为一种文化记忆中存在的老上海,总会让人联想到一个遥远模糊而又倩丽的身影。许多人倾向于用“女性”比拟上海。程乃珊在《上海女人》中写道: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灵魂,这个城市的灵魂就是女人。在《长恨歌》中,王琦瑶与邬桥阿二有一段很是奇妙的谈话,二人谈起了上海的月亮。阿二说上海的月亮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月亮,一个是月亮的影” ②。这里不妨由此把王琦瑶看作“上海的影”。
王安忆在访谈中就曾明确将王琦瑶看作上海的代言人,称“《长恨歌》则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1]。不少学者更是将王琦瑶视为上海文化的精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长久以来王琦瑶被视为上海文化精神的象征,是作为上海影子般的存在。
王安忆用王琦瑶传奇的一生讲述了上海的文化特质,使上海与“王琦瑶”之间构成一种内在联系。出身弄堂的王琦瑶从“沪上淑媛”成为“上海三小姐”,先是毅然与位高权重的李主任成婚,之后又独自生子,将其养育成人,经历种种人世变迁,最后却因一盒黄金惨死于小流氓之手。以王琦瑶传奇而又动荡的一生,总结其引领时尚、富有情调、功利虚荣、精明务实、坚强勇敢、独立自主的性格特质并不困难。而作为上海文化的代言人,王琦瑶的经历自然与上海暗合。王琦瑶凭借年轻美貌嫁于李主任;上海则凭借其地理位置的优越,在战火中异军崛起。西方的物质文明涌入,带来了思想文化的解放和碰撞,摩登新潮更是成为上海的代名词,为其赢得了“东方巴黎”的美誉。物质经济文化的极度发展,使其跃居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在这繁华的表象之下,上海时刻被西方国家虎视眈眈,居住在上海的市民,被商品经济侵蚀,道德意识的弱化,面对着战火时刻存在着身份的焦虑,整个社会浮躁不安。随着炮火的南移,上海也承受着几近要毁灭的威胁。可喜的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这座城市并没有从此沉没,一蹶不振。正如王安忆所说,上海的坚强就在于它会在旧上海的尸骸上,又生长出一个崭新的上海。
王琦瑶面对苦难的坚韧勇敢、随遇而安应该说与上海的不屈顽强是同质的,这也是作者对王琦瑶书写鲜有崇高的一面,也是王琦瑶身上最为重要的文化特质:
上海的小姐们就是与众不同的,她们和她们的父兄一样,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而且行动积极,不光是光说不做的。她们甚至还更勇敢,更坚韧,不怕失败和打击。③
李主任的飞机失事,王琦瑶又从天上转眼到了地下,可是之于她来说只是从爱丽丝搬到了平安里;面对康明逊的懦弱与逃避,王琦瑶并没有愤怒与责怪,而是想尽办法承担责任,抚养女儿长大;程先生无法直面生活的磨难,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女儿陪同女婿一起出国;最后带给她对人世一丝依恋的老克腊也相继离她远去。似乎王琦瑶的一生始终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能给她完整的归属感。然而她仍然是选择冷静又自持地生活着,正是这股坚韧的力量支撑着王琦瑶,使她比那些曾经辉煌风光的男性们走得更长、更远。能把普通平凡甚至乏味的生活过得精致美好、从容优雅,这才是市民生活中永恒而又坚毅的力量。
王琦瑶身上追求时尚、不甘落伍、务实理性、富有情调、功利虚荣、独立自主的这些特质,与上海文化特质是相合的。王安忆不厌其烦地将笔力倾注于对上海的空间景观、饮食、交际的描写,目的在于再现逝去的上海的记忆,是“直接写城市的故事”[3],直接表现“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3]。诚然,王安忆有想借王琦瑶的一生表现上海近代风起云涌的变化和历史的冲动,但是作为“城市的影子”“文化精魂”的王琦瑶,真的能代表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质吗?又或者说作者的这种都市书写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理性分析,还是仅仅简单地沦为了对上海逝去文化的介绍和普及?
三、王琦瑶与上海精神的矛盾
《长恨歌》借女性来表现一座城市的灵魂,无疑是对上海城市书写令人惊喜的一次尝试。其对市民生活的挖掘,也有相当可观之处,然而,作者并未对这一形象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对上海旧史的态度也显得含糊不清、暧昧不明,对上海现实形象的理解趋于简单化,而关于这座城市的未来走向,也显得莫知所措。
首先,王安忆在对王琦瑶的刻画上,很多都做了背景模糊的处理,以此实现对最能代表上海文化的弄堂女性的普遍象征。书中几乎没有王琦瑶与父母亲情的记忆,母亲的唯一出场,是在王琦瑶生产后的几幕,拥有的也不过是只字片语。至于王琦瑶如何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甚至又如何在乱世保留一盒金子,则都被其一笔带过。这种模糊化的处理,使得人物更好地为中心服务,那就是成为一种象征,不仅是作为上海的象征,同样也象征了一类女性——上海弄堂女性: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④
王琦瑶是最为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孩,她们追逐时髦,精致精明,又有着些许虚荣高傲。但是正如徐秀明所说,不可把上海女性的时尚前卫混淆于堕落放荡。王琦瑶选择去做李主任的“外室”,这类事不能说没有但绝不具有普遍意义。“上海的普通市民与上流人士,在文化取向上并无二致:既热爱世俗生活,又讲求优雅尊严,看不上自甘堕落之行。”[4]诚然上海文化有其世俗功利,虚荣物质的一面,但从整体上来看,在其多元开放兼容的姿态中,仍然是保持着昂扬进取、积极向上的。上海虽然是冒险家的乐园,但是源自上海本地市民的文化,有其保守谨慎的一面。大多数的上海本地市民谨慎精明,对于关系一生荣辱利害的婚嫁之事更是慎之又慎。更何况王琦瑶出身自小康家庭,衣食无忧。如此这般的“进取”,给人的可信度并不高。“王琦瑶”终归与现实中的“上海”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的。
遗憾的是王安忆始终对上海文化缺乏明确的价值判断。对于王琦瑶的态度上也是关系暧昧,甚至不免流露出欣赏与同情。在写到爱丽丝里住着的“金丝雀”,她这样赞美道:
她们个个都是美,还是高贵,那美和高贵也是别具一格,另有标准。她们是彻底的女人,不为妻不为母,她们是美了还要美,说她们是花一点不为过。⑤
王琦瑶等女性的人生选择,显然受到了上海殖民文化和海派文化中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可悲的并不是王琦瑶的自身选择,而是其背后透出的文化价值观是根本盲目的、不值得同情的。文化的多元需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然而王安忆并没有对这些不良风气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相反有些时候甚至流露出对这些女性的哀怜欣赏与感伤情绪。
其次,如果以王琦瑶作为上海文化的象征,那么其对上海形象的理解就过于趋向简单化了。《长恨歌》民间叙事方式使得王安忆对市民生活多有瞩目,然而王琦瑶等人的市民生活,更多令人看到的是每天纠结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家长里短。很显然,读者并没有从《长恨歌》的世俗生活中,看到人物创造优雅生活的才能,更多体会到的是人物得过且过,消极逃避的一种末世态度。仿佛人生只有世俗的衣食情欲在翻滚,而没有了其他,一切崇高在这里都被消解,屈服于一种原始的动物性的追求,仿佛只有这些才是生活,才是生命存在的一切真实。
如果作者只是想要通过王琦瑶展示上海世俗功利、物欲翻腾的一面,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此一来对上海文化的认识就不免流于简单,让人觉得浅薄乏味。诚然这个多元的地方,有其世俗的一面,但同样也有其崇高优雅的一面。难道只有饮食男女的世俗生活才叫真,亭子间里孕育的有识之士的进步力量,巷弄里出现的精通多国语言的仁人志士就都成了假的了吗?如此这般,王安忆所描绘的这座城市就不可避免地缺乏理想和信念感,也让这座城市的气质丧失了一定的力量感,没有质,似乎只有浮华,难以让读者领会到一个城市的精魂。尽管书中有对上海精致建筑发自肺腑的赞赏,但是这种对建筑、精致生活的沉溺是浮于表面的,人们需要看到的源自这个城市内部所焕发的一种精神,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寻求一种民间的叙事角度并不意味着让整个城市的文化走向平庸。
最后,王安忆对这座城市的未来走向,也显得游移不定。小说的结尾王琦瑶被长脚杀死,作为上海文化象征的王琦瑶,最终走向了终结,这就是说作为旧日的精致、追逐时髦、功利的上海精神走到了终点。但与此同时王安忆对现代化的商业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也有所质疑:
薇薇她们的时代,照王琦瑶看来,旧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⑥
在她笔下,上海经济的复苏带来的是人的道德水平的下滑,原先生活方式、伦理关系的瓦解。但是上海的未来又指向何方,或者说该如何重建新时代下的上海精神,王安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可以说王安忆对于上海的书写仍旧是停留在了表面的感性认识上,未有深刻的理性分析。
四、结语
《长恨歌》对上海的生存状况、文化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阐释,还是有其独特理解的。但上海文化纷繁复杂,小说再现上海的文化和历史不可避免地存有偏差。归根结底,寻其原因,与王安忆本人缺乏个人经验进而由此导致的上海想象有很大缘故。王安忆随母迁往上海,尽管长时间生活在上海,但这种“文化上的无根蒂”也让其始终对上海文化保持一个清醒冷静的审视距离,但是未有深入,其对上海文化的复现,难免带有“想当然”的味道。同时,市民生活也是《长恨歌》着力之所在,但王安忆本人长期生活所接受的是完全不同于普通市民的教育。这种成长经历上的隔阂,也让《长恨歌》笔下的市民生活难有亲切可靠,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之感。王安忆出生于“新上海”,而书写的却是极度远离她生存空间的“老上海”,间接经验难以填补直接经验的空洞,也就是说即便作者翻阅遍了故纸堆,也由于其本人的缺乏经验,导致其无法向读者传达一种清晰的经验,而只能是模糊地去想象她心中的上海世界。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页,第124页,第47页,第18页,第89页,第243页。
参考文献:
[1]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作家,1995,(10):66.
[2]陈思和.谈谈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和上海文学、海派文学——答《上海文化》问[J].上海文化,2021,(02):17-18.
[3]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作家,1995,(10):67.
[4]徐秀明.文化冲突与叙事错位——由《长恨歌》谈王安忆的小说美学及其创作转向[J].学术月刊,2017,(07):128.
作者简介:
王雅琴,伊犁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