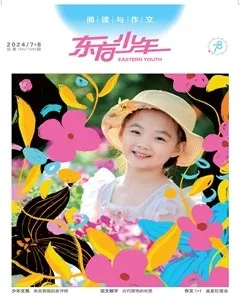月光下的池塘(外两篇)


太阳从西边的鸡公山山头沉下去,朴塘村就沉浸在了月光里。
我少年的村庄,一直是那么让人流连忘返,泛起无尽的思念。
村子里的月光,水一般柔顺。月映照在池塘的水面上,泛着银光。若是有风,水面就荡起一层层银波。银波在月光下闪烁,池塘四周蛙声响应,乡村就开始有了生命向上的呐喊。更多时候,月光像一双手,将池塘这把遗落在乡村的琴弦轻轻拨弄,乡村就变得朦胧与优美起来。
月光下的池塘是踊跃的。戏水的少年,浣衣的女子,夜归的牧人,砍柴的老者,都会在池塘里浆洗生活的劳累。老屋前有个池塘,在村庄的腹地。山谷里的泉水经过老屋后面,蜿蜒流淌到池塘,水清澈而明亮,像一把镜子,照亮村庄。因为离家近,我少年时喜欢在这个池塘里戏水,偶尔帮助母亲挑上两桶水浇菜园子。
不管是白天还是月夜,池塘总是一片热闹。村里人养的几只小鸭小鹅在池塘里日夜游逛,给本来寂静的池塘带来生命的灵动。我与小伙伴经常在池塘里洗澡,驱赶这些小鸭小鹅。每当这个时候,它们都会奋力地“红掌拨清波”,水面上荡出许多优美而细长的圆弧。偶尔,它们也会“嘎嘎”叫喊着,振着翅膀,不停地拍打水面,将月夜一再撩拨。
村庄的寂静让池塘边的小鸭小鹅悠然自得。它们时而上岸,时而游于水中。偶尔,你会看见一只小鸭一头栽入银白色的水波里,将头扎进水里,寻找水草或更美味的食物。至于屁股和尾巴,自然是高高“挺立”在水面的啦。多年后,每逢我观看跳水比赛,就会一再想起故乡池塘边的小鸭小鹅。它们就是乡村的运动员,池塘就是它们的运动场。
朴塘村的池塘四周没有垂柳,只有旺盛的水草。村里人喜欢把菜地与果园开垦在池塘周边,方便浇灌。在故乡,夏天的菜地与果园迷人无比。绿的冬瓜、豆角,红的辣椒、西红柿,紫的茄子,金的南瓜,白的香瓜,还有橘树、苦楝树、椿芽树,李子、桃子,应有尽有。一到瓜果飘香的时节,池塘边就多了热闹的故事。守园人夜半的吆喝声在村庄上空清脆回旋。一群群小孩子看着东边的西瓜熟了,西边的桃子熟透得如脸庞一样娇美,就开始思量月光下的“偷盗”。当然,村庄民风淳朴,少年们偷桃摘李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盗窃。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月光下的“巧取豪夺”恰是对美好生活的另一种向往。
我喜欢月光下的池塘,果子熟了后,有些会随风掉落到池塘的边沿。偶尔坠入水里的果子,击打着水面,“咚”的一声就沉入了水底。这时候,小伙伴们要是在池塘里游泳,就会竞相争夺。枣子熟了的时候,一颗颗红彤彤圆滚滚的枣子,如珍珠一般坠落,入口甜脆。果园主人如果趁着月光摘取,小伙伴们更是欢欣鼓舞。大家一边帮主人捡拾,一边品尝鲜美的果实。待主人收工,每个人都会得到一捧。
月下的池塘凉爽清幽。待到十五左右,月光就圆润起来。池塘在前半夜热闹非凡,等人们洗涤后上了岸,才会渐渐沉闷下去,给人一种深幽的孤寂。此时,池塘里还有一群热忱的生命游弋于水底,或者在水草边吸食露珠。它们与水浮莲一起,在月光下坚守着这一方生命之源。直到清晨的太阳从东边山顶慢慢爬上来,公鸡伸着长脖子啼唱着乡村的晨曲,池塘边又有了新的故事。
后来,山上的泉水逐渐干涸,年轻的乡亲们都奔波在外,小村的菜地果园也长满荒草,池塘的水也开始发绿。家家户户的少年不再到池塘里洗澡,池塘就变得苍茫起来。
如今,朴塘村静了,月夜也静了。唯有蛙鸣和蛐蛐的歌唱断断续续在故乡守候。
有月的夜晚,池塘上泛着银鳞般的光斑,像几滴眼泪,敲打着故乡。
月光下的纳凉
月光爬上山顶以后,夏夜的凉风就偷偷溜进了村子,徐徐地吹在朴塘村的各个角落,像一个夜行人,迈着轻盈的步子,在村子里游荡。
我回到故乡,在久违的夏夜乘着月光纳凉。多年前,纳凉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便贫瘠,村庄还是那么热烈。而今天,纳凉显得奢侈。少年的朋友们散落在外,老人们无须在夏夜里手持蒲扇,他们幸福地享受着后辈行走他乡创造的财富,并开始习惯于在室内体验电器等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与清凉。
那夜,我搬了一张躺椅、几张凳子,叫一家人在门前的禾坪上纳凉。夏夜总是那么迷人,远处月光下行路人的脚步惊动了村里的狗。一只狗叫了,整个村庄的狗都附和起来。狗叫声在月下的夏夜显得那么热切,如同一组慷慨激昂的乐章。纳凉人不需要理会这叫声,只顾夜风与月光,以及星星的伴随。月下的夏夜,有狗叫着,纳凉的即便只有一个人,都不会显得孤独。
朴塘村的月夜是宁静的,夏夜依旧如初。夜雁北归,“嘎”的一声雁啼,村庄就更加迷蒙一片。月光再好,夜雁的身影都晃如轻烟,两行模糊的影子划过天际,只听得到它们的呼唤,悠远而又深邃。当然,朴塘村的夏夜不光是雁过留声,还有许多夜鸟的歌唱,宛如大地的心脏一样跳动。我最怀念月下的猫头鹰,在山沟的深处“啼唤”。少年时,母亲经常在有月光的夏夜里讲述猫头鹰的啼哭。如今,少了聚在一起诉说家长里短的乡村,也少了纳凉的气氛。
我喜爱纳凉,亦是对朴塘村山清水秀的灵气发出的赞叹。村庄四周是山,鸟在山林中欢鸣,泉水突突流入山涧,蜿蜒流进村子的山塘水库。这里有山有水,曾经人烟繁盛。如今,月下纳凉的人少了。家家户户的电器越来越多。蒲扇、手工做的蚊烟,都远离了生活的记忆,特别是这些年,朴塘村的种地人越来越少,更谈不上种植花生、黄豆。少年时,每当暑期到来,正是收割花生、豆子的季节。是夜,皓月当空,家家户户摘花生,水煮黄豆、炒瓜子,老老少少在自家的禾坪边吃边劳作。少年时的欢呼雀跃,铭记于心。
年少时,趁着月光随二哥到田野里抓田鸡、泥鳅。准备好干松枝,提一个铁笼,点上火,到田野里四处寻找。月亮升了上来,田野四周雾露迷漫。泥鳅会大摇大摆地游出来,自由地伸展,吸汲着甘露。只要用火照着,用铁爪一把拽下去,一条肥壮的泥鳅就收入竹篓。田鸡更容易捕获,在水塘或者田埂上,闻声即可。要是收工早,家人正在禾坪纳凉,赶紧烹炒下厨,掏上几碗糯米酒,便可悠哉乐哉地品尝美味佳肴。
这些年,我很少有机会亲近故乡的月光,纳凉更是渐行渐远。当有一天,像倦鸟一样飞回村庄,月光依旧会穿越故乡的胸膛,让她感到内心在隐隐作痛。因为,游子千里,都离不开母亲纳的千层底,一针扎痛的不光是母亲的手,还有游子的心。而我,更希望在故乡的月光下,执一把蒲扇,像我的祖先们,摇晃着到生命最后的一刻,与故乡融为一体。
月光下的唱戏
双抢(夏天抢收、抢种庄稼)一忙完,村子里的喜事就多起来了。有了喜事,主人家会择日在月下唱大戏。
我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在月下看过大戏了。朴塘村的大戏总是从县城的花鼓戏剧团请来专业的演出队。花鼓戏是故乡的传统地方戏剧,我自小喜爱看戏唱戏,少年时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花鼓戏演员,丑角旦角都可以。
我在省城读书时,在湖南省湘剧院寄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看过长沙、衡阳一带的湘剧及花鼓戏表演。曲调不一,各不相同。在湖南花鼓戏中,有上百支调子。故乡自古属于衡州府管辖,唱的是曲牌联套结构,辅以板式变化,粗犷、爽朗,表演者朴实、明快、活泼。在故乡,即使白喜,都会有花鼓戏表演,而且多以小丑、小旦、小生的表演吸引观众。比如《刘海砍樵》《运粮》等,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朴塘村田地肥沃,人也精明。每年夏天双抢过后,家家户户都趁着粮食储存丰富的时机摆酒庆祝各类喜事。这对于朴塘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盛典。月光下的大戏总是吸引着四邻八村的人,只要与朴塘村人沾亲带故,都会趁着这个难得的闲暇到村里看大戏。少年时,外婆家总会来一堆远亲,每每这样的夜晚,浓烈的肉味、水酒味,还有炒瓜子、炒花生、炒黑豆的香气飘过村庄的上空,与喜庆融为一体,分不清是一家的喜事,还是一个村的喜事。
外婆、母亲和叔伯娘亲都是戏迷。大戏还没开始,喜庆人家先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戏班子里的乐声师傅会敲打起开场锣鼓,一阵催促调子,禾坪的戏台子下渐渐围满了各式各样的凳子、椅子。邻居中有精明的小生意人,一个箩盛着一担炒货瓜子,用竹筒量贩卖。有人从镇上的冰厂用塑料保温箱驮来冰捧,不断叫卖。
母亲在村子里人缘好,认识的人多。每次看大戏,很多乡邻都会把家里的炒货递一把过来,炒熟的黑豆、瓜子、花生,让人盛情难却。我看不明白大戏的内容,却喜欢看戏,皆归功于这些美味零食的诱惑。
花鼓戏的乐器都是取材湖南民间的锣鼓、小喇叭,还有铜恰、渔鼓、二胡、笛子等。曲调婉转、悠扬,演员身着华丽的凤冠霞帔或简朴的乡间装束,以小丑、小旦、小生的表演最具特色。小丑夸张风趣,小旦开朗泼辣,小生风流洒脱。步法和身段比较丰富,长于扇子和手巾的运用,拥有表现农村生活的各种程式,诸如划船、挑担、捣碓、砍柴、打铁、打铳、磨豆腐、摸泥鳅、放风筝、捉蝴蝶等。我尤其羡慕女演员聘聘婷婷的动作,兰花指持扇,轻盈的莲步,以及宽敞曼舞的水袖,令少年时的我们痴痴地崇拜与模仿。
一般人家喜庆,都会选两个以上的剧目,所以每次大戏结束,都到了凌晨时光。朴塘村的月光归于宁静,四周的暗黑斑斑驳驳。戏散了,禾坪里人头攒动,呼儿唤女的声音不绝于耳。禾坪的四周一片狼藉,瓜子壳、花生壳满地都是。禾坪外的围墙垛上,歪歪斜斜睡着各家各户的小孩儿,等待父母逐一去认、去唤。
如今,村子里唱大戏的机会不多了。前些年,在家乡遇见一次唱大戏,具体演什么剧目已记不清楚。但我要感谢朴塘村的月光,感谢月光下的大戏,让我在南方独处的夜晚,多了一份生命的归属与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