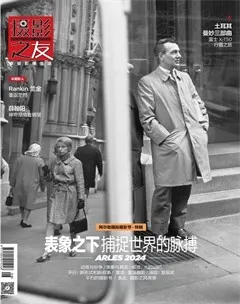薛翰阳:神奇昆虫在哪里




从2021年接触超微摄影开始,逐渐在国际摄影大赛上崭露头角,再到出版自己的昆虫图鉴,薛翰阳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这条看似顺利的道路,对于少年摄影师来说,也是不断“打怪升级”的旅途。标本的整姿与清洁工作是超微摄影中的一大难题,他搬出了超声波、洗洁精、去污药水,甚至是洗发水等“十八般兵器”,只为呈现昆虫洁净无瑕的完美姿态。可就算屏住呼吸,稍有不慎,一枚珍奇的标本也可能会在整姿、清洁或是拍摄的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不过,少年从不惧风浪,薛翰阳把每一次超微拍摄都当作是一个不断解决难题的过程。
虫生无常
自然界的丛林法则总是残酷的,如果营救被天敌捕获的可爱昆虫,那另一只就可能因此丧命。薛翰阳的图鉴中有一篇章名为《虫生无常》,记录了昆虫被捕获、孵化或是蜕变失败、死后腐败或是被真菌感染的瞬间,是这些小生命最落魄不堪的时刻。对他而言,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拍摄,与一只小蜜蜂有关。那是一只正在辛勤采蜜却因蚊蝇捕杀工作而误伤的小生命,身体上残留的花粉、工作时的姿态,让薛翰阳意识到人类卫生与舒适的生活是建立在灭杀千千万万“有害”生命的基础上的。带着复杂的心情,他为这只小蜜蜂拍摄了肖像照。


神奇的隐翅虫
刚开始涉足超微摄影领域的薛翰阳,喜欢拍有漂亮鞘翅的甲虫、有迷人鳞片的蝴蝶、有威武大牙的步行甲等这类颜值高或是有趣的昆虫。随着他对昆虫了解的不断深入,慢慢不再满足于重复拍摄“仅仅只有好看”的作品,向着更深层次的主题发起了挑战。谈到隐翅虫,这是一种他很痴迷但常常被大众误解的昆虫。隐翅虫种类繁多,只有极少数是有毒的。在薛翰阳眼里,南美很多隐翅虫金属色鞘翅的美艳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种金龟子,它们的拟态现象也很有趣。在《ArtofSmall超微昆虫图鉴》中,他专门为隐翅虫系列设计了一本刊中刊,希望读者能够重新认识这一昆虫群体,也借此机会为大家打开一扇全新的了解昆虫世界的窗户。
摄影之友×薛翰阳
超微摄影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如果说优秀的摄影作品是“大片”,那么超微摄影作品无疑是“科幻大片”,甚至是IMAX级别的视觉盛宴。初见超微摄影作品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油然而生。那些平日里受限于肉眼观察能力的细微之物——毛孔、灰尘、花粉、微小昆虫、水生生物、结晶体等,被无限放大,让我们得以清晰地审视,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体验,与第一次看《阿凡达》时的心情如出一辙。加之摄影艺术对光影的精妙控制,使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实现了艺术上的升华,变得如同鬼斧神工、天工造物般令人叹为观止。
就昆虫而言,金属质感的鞘翅、复眼、鳞片、腿上的绒毛,甚至爪勾上的肉垫,当这些部位被放大以后,就像孙悟空耳朵里的毫毛一样,瞬间变成顶天立地的定海神针;2毫米的瘤叶甲被放大20倍后,竟然如同史前霸王龙一样威风凛凛;1厘米大小的单爪鳃金龟的鳞片像金盔金甲一样闪闪发亮,隐翅虫的毛囊好似佛像上的螺髻,就连弱不禁风的小蚂蚁,把它的小脸蛋放大10倍后,那副牙口也会如怪兽一般令人不寒而栗。
因为超微摄影,我知道了很多对人类而言可能无用但也很有趣的答案:蝴蝶鳞片竟然就是微缩的鱼鳞,蜡蝉身上居然真的是蜡,水虿的牙齿是可折叠的伸缩弹簧,小蚂蚁的蛹和大象长得亲如兄弟……

你对拍摄设备进行了哪些改造?这些改造解决了你在拍摄中遇到的哪些问题?
超微摄影和传统摄影的区别就在于,追求“更大、更稳、更清晰”是它的技术使命。一般的微距镜头只能到1:1的放大倍率,超微距镜头一般最多能放大到5倍,再想拍出更大放大倍率的照片就需要用到显微镜的物镜,而使用物镜就需要有跟它相匹配的一系列配件,比如管镜、延长管等。网上能买到的配件大部分都能满足全画幅相机的使用,但自从我使用中画幅相机以后,现成的微距镜头和物镜的延长管就会在画面上形成黑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DIY。我参考了很多前辈的经验,自制了一套管镜,解决了困扰我使用中画幅拍超微的难题。
柔光问题也是拍摄超微需要解决的难题,有很多前辈拍超微的座右铭就是“柔光!柔光!柔光!”为了拍出光影柔美的照片,我在柔光工具上做了各种尝试,不过到最后发现最好的柔光工具竟然是——卷筒纸!没有什么柔光是一张卷筒纸搞不定的,如果真的搞不定,那就再来一张!
另外,拍摄前,我都会仔细观察我的拍摄对象,制定拍摄角度、光影计划,尽量让每一次的光线组合都有针对性。除了常规的光线明暗的设定,我还会考虑不同色温光线的组合、可见光与紫外线荧光的组合、多次曝光的组合来拍摄,尽量让整个拍摄过程更有趣,所呈现的作品有更多的变化。


《ArtofSmall超微昆虫图鉴》的章节名都十分有趣,还打破了传统的分类法,你如何兼顾科学性和艺术性?
这本画册在章节编排上既有前后的逻辑关系,也有整体情绪的连贯表达。
当我拍摄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了出版自己作品画册的想法。不过作为中学生,我并没有打算出版特别“科普向”的著作,也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储备。所以,我在拍摄过的作品中尝试去寻找内在联系,比如,除了蝴蝶、飞蛾,还有很多昆虫都长有鳞片,就组成了“鳞次栉比”;把特化叶形足的昆虫集合在一起,“昆虫界最美的喇叭裤”就诞生了;表现贝氏拟态、趋同演化现象的“红萤与它的粉丝”“蚁蜂与它的模仿秀”等,都把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群体集合在了一起。
章节与章节之间也有联系,比如“鳞次栉比”的最后一张马脸白埃长角象甲与下一章节“奇奇怪怪的蝇”的第一张突眼蝇都有加长版的眼柄,形成内容上的自然过渡;而它的下一篇章“我们都会螳螂拳”开篇即展示了拥有螳螂捕捉足的螳水蝇,既是对前一章蝇的篇章的延续,也预示着新一主题的开启;在“螳螂拳”章节的尾声,我特意挑选了宾刺瘤蝽作为结束,与紧随其后的“这样的臭大姐不香吗”一章之间产生了有趣的关联。因此,在浏览这本画册的时候,即使忽略具体篇章,阅读体验依旧流畅自然,同一物种跨越不同篇章多次出现,也不会有突兀之感。
在画册编排上,我特别注重在情绪表达上的节奏起伏,包括强、弱、舒缓等多种情感的交替变化。具体到各个篇章的图片选择上,不仅考虑了每张图片对观众视觉冲击力的强弱,还避免了仅仅追求高强度的视觉效果,确保情感表达不至于“一强到底”,而是如同交响乐般,有起有伏,引人入胜。
此外,我还摒弃了在目录里罗列昆虫名称的常规做法,而采用了将每一篇章的缩略图直接嵌入目录的方式,这样让读者在检索的时候可以一目了然。
虽然我用了比较趣味的方法来进行分类,但是对于昆虫的定种、学名的勘定,我丝毫不敢怠慢。除了查阅大量资料外,我还得到了国内外很多昆虫专家的指点与支持,特别是我非常仰慕的新加坡昆虫学者萧俊老师的鼓励。在这里要感谢他们的帮助,让这本图鉴在学术上也经得起推敲。

昆虫标本是如何获取的?如何看待微距摄影中的道德难题?
我们经常会遇到动物拍摄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比如之前发生过的打雨伞的雨林蛙事件,最近的摆拍活鸟事件。
超微拍摄昆虫,大部分情况下是拍摄昆虫标本,我的标本有些是自己采集或饲养的昆虫死了以后制成的标本,有些是网上购得,还有一些是虫友赠送。我自己饲养、采集来的昆虫,不管是宠物昆虫还是“害虫”,即使是蚊蝇也从不会为了拍照而活活处死,总是好吃好喝地喂养着,等它们寿终正寝后第一时间制成标本,唯一的“不虫道”可能就是让它们失去了“自由”。也遇到过一些很难得的活体昆虫,因为死去以后就会失去最佳拍摄时机,比如很多直翅目昆虫或是蜘蛛会变得干瘪甚至腐败,昆虫的复眼也会失去光泽,这也是我比较少拍摄昆虫复眼特写的原因。
现在不少手机的微距功能越来越强大,你认为新兴技术将如何影响和塑造微距摄影的未来?
“出门遇事不要慌,掏出手机拍一张”,我目前的昆虫拍摄主要还是在室内,外出采集、采风时也会带上相机拍一些单张的昆虫生态照,或者采用机内堆叠的方式拍摄,但绝大多数还是会用手机记录所见所闻。如果手机未来能够实现焦点可自动移动的机内堆叠功能,有好用的拍摄软件,一定会让超微距摄影变得更简单方便。
哪些摄影师对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应该和国内很多超微摄影爱好者一样,都是受到了英国超微摄影先驱列文·比斯(LevonBiss)作品的影响才开始自己的超微之路。国外有很多超微摄影大师,但唯独列文·比斯用商业摄影,用拍摄人像的手法来拍摄昆虫肖像,这一理念对我影响至深,而且他的作品的光影中还隐隐透露出一种东方的美学。虽然我没有机会去尝试商业摄影,但我的摄影老师袁涛、闫璐给予了我很多审美上的指引,上海的摄影家赵铭老师把我引荐给超微摄影前辈王慧良老师,让我得以真正揭开了超微摄影的神秘面纱。
对于爱好摄影的青少年,你有什么建议或者经验可以分享给他们?
没有比热爱更好的老师了,就我个人而言,是因为热爱昆虫才拿起的相机,我的摄影技术和基本功与大多数前辈老师相比,根本就是小学生,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挡我拍摄昆虫的热情。虽然在拍摄过程中免不了会追求图像的锐利、精度或是拍摄的难度,但这一切完全不是我的初心所在,我希望朋友们能从作品里看到我拍摄的态度与热情。同样,我也把我的感受分享给我的同龄人,只有热爱,才能拍出与众不同的作品。
未来有什么计划?有哪些想要尝试的新的主题和拍摄对象吗?
我希望这本《ArtofSmall超微昆虫图鉴》能够被更多人知道,在中文版面世之前,其英文版已经在海外成功发行,我十分期待它能以更多不同的语言版本在全球各地绽放光彩,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昆虫世界。
同时,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了很多拍摄计划和主题,计划深入探索这本书中已经展现的几个主题,不再仅仅局限于隐翅虫、蚁蜂、红萤,因为昆虫界中还有无数类似的奇妙现象等待我们去发掘与研究。我也期待能有更多机会与更多专家、专业机构合作,进行既有深度又具广度,甚至是面向世界的专题创作。
我即将踏入高三年级,明年也将迎来大学生涯,或许今后所学的专业未必与摄影相关,但超微昆虫摄影一定会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