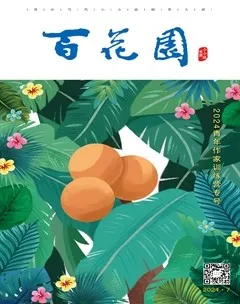发育万物
叶北海,1982年生,现居山东潍坊,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百花园》《小小说月刊》《当代小说》等刊。
于祉在国子监读书,却没考中科举,这是件很遗憾的事。
他少年时参加科考,按惯例,进场前是要搜身的,防止“怀挟”。
怀挟的手法很多,有人把小抄藏于笔管,有人把缩本置于砚底,甚至有人花重金请微雕师傅在墨锭上动刀,乍一看是梅兰竹菊四君子,放水晶镜框下再瞅,一枝一叶,满是“子曰诗云”……
好,考生所需的笔墨纸砚,由贡院统一安排,不必私下准备。
于是怀挟又转向了衣物:靴子里垫本书,衣服里加层衬,冠冕上镶块玉石。不光微雕师傅,连刺绣女工都开始捞偏门了。
好,考生所着衣冠,也由贡院统一安排。
怀挟还是禁不住,只能裸检搜身。
发辫解散,一根一根地梳;胳膊抬起来,腋下不得私藏异物;两腿分开,一只手伸进去……
也就是那一刻,于祉恼了。寒窗十载,饱读圣贤书,只图个一鸣惊人,天下皆知,眼下竟要受这等屈辱,还考什么考?当场抢回衣物,穿戴整齐,在众人错愕的眼神中扬长而去。
自此后隐居澹园,读书,写诗,练字,教学生,终生不仕。
园中无甲子,转眼就是六十年。
于祉老了,头发白了,胡子白了,连眉毛都白了,可他的心性还跟个孩子似的,贪玩。每天一早,拄着那根摩挲出包浆的古藤杖,慢悠悠地踱出小角门,上街找乐子。
潍县人好褒贬人物,闲来无事,就三五成群地聚一堆儿,说陈介祺辞官归乡,在罗家巷建了座“万印楼”,收藏三代秦汉印章七千多方、商周古钟十一件、先秦青铜器无数,那可真是价值连城;说张昭潜编定《山东通纪》,正在写《北海耆旧传》,要把潍县城从古到今的贤哲逸闻写进去,功德无量;说曹鸿勋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光宗耀祖,振兴门楣,更是潍县城的第一等大事!
于祉听得开心,脸上的皱纹绽成一朵花。
那位说了:“我们聊潍县城的贤哲,你乐个什么劲儿?”
于祉笑笑:“与有荣焉,与有荣焉。”
当然,有时也会听到自己的名字。说顺着这条巷子走到头,住着个古怪老头儿,当年曾大闹金銮殿,气得嘉庆爷吐了血;说他回乡归隐,大兴土木,建了这座澹园,自号独笑生,教了半辈子书,潍县城的读书人一多半出自他的门下;说他已一百多岁,闭馆不教了,整天神神道道,白天见不着人,晚上却在楼上跳大神,莫不是黄大仙托生的……
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听得于祉直摇头,拄着藤杖走了。
出了巷子,转到书院街。
于祉半生无事,著述颇丰,有《澹园古文选》两卷、《澹园诗集》八卷、《澹园诗话》一卷,另有《三百篇诗评》《揽古轩书画录》等,都已付梓出版,潍县城大小书铺里都有售卖。
于祉逛书铺,先看有什么新书,尤其是那些学生有没有新著作问世,再看自己的书卖得如何。闭馆谢客后,他的书竟卖得更好了。也是,这些小童生无缘听他讲课,还不兴人家买本书自己揣摩领悟?
听着书铺老板不停念叨着要加印,于祉也就乐开了花。
除了看书,他还看匾。
潍县城重文风,店铺开业都要请名家写块匾,或者写副对联挂上。“百济堂”是板桥公的六分半书,百年老店了;“南宫和乐”是刘罗锅的重墨,倒不愧他“浓墨宰相”之名;“长松酱园”则是谭谟伟的“指书”,老相识了。
还有他的题字。六十年了,他的题字不计其数。有时候碰到一块匾,看字体、笔意、落款印章,是自己写的,没错,哪年写的呢?于祉一阵恍惚,记不起来了。
有些字写得跟狗爬似的,竟然也落着“澹园独笑生”的款,让他哭笑不得。
算了,人生百年,哪能事事较真儿?板桥公早提醒过了,“难得糊涂”嘛。
有些事却不能糊涂。
东岳庙二门上有块匾——“发育万物”,古朴圆融,外柔内刚,难得。于祉站在门前,一看老半天。
庙里的烧火道工竖着大拇指向他炫耀:“这字写得不错吧?澹园独笑生的字,大手笔。当年板桥公来此游赏,也为之搁笔,声称‘余字多逊于君’。你想,板桥公是谁?扬州八怪,一手六分半书开先河。能得他老人家一声赞,那得是多大的荣耀?”
于祉把脸拉得老长——郑板桥于乾隆年间担任潍县县令,距今已逾百年,而于老头刚过了八十整寿,他的书法匾额,怎么能得板桥公的赞赏?那不成“聊斋”了?
烧火道工对他的话很是不屑:“少见多怪了不是?澹园先生是个老神仙,活了一百四十多岁,当年跟板桥公笔墨论交,那可是咱潍县城的佳话。”看游客进门,他懒得搭理于祉,继续炫耀郑板桥的墨友去了。
于祉越想越不对劲儿。别人冒他的名号,无非是赚一笔散碎银子,养家糊口,无伤大雅,可让他去冒认人家的书法,这就是欺世盗名了,不行。
第二天,他带着笔墨纸砚,到东岳庙论理来了。
他指着“发育万物”说:“这是康熙年间于适所书,大手笔,足可以名垂千古的。于祉是谁?就是我,澹园里一个教书匠罢了,跟人家没法比。再看字体,我的字,满大街都是,你去看看,比比,不一样的。”他一边说,一边写各种笔体的“发育万物”,果然不一样。
烧火道工很惊讶:“你就是澹园老神仙?”
“什么老神仙?普普通通一老头儿。”于祉继续写。再看那块匾,仿的《瘗鹤铭》的笔意,没有几十年的工夫,写不来的……
烧火道工指着他的字,笑了:“还不承认是你写的?这不一样吗?”
围观的百姓也纷纷附和,是一样。
于祉看看笔下的字,再抬头看匾,布局、章法,还有那笔画气韵,竟真的一模一样。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