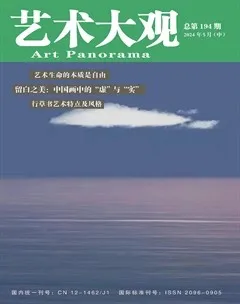影视剧《我的阿勒泰》中的诗意田园与乡愁
作者简介:才悦(1997-),女,河北承德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
摘 要:影视剧《我的阿勒泰》改编自同名非虚构小说,为一部描绘新疆北部草原生活和哈萨克族民俗文化的艺术作品。这部影视剧不仅通过视觉和情感层面的精美呈现成功地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理想化的田园空间,还通过对文化符号的巧妙运用和情感共鸣的塑造,集体召唤了观众内心深处的乡愁情感。这种田园与乡愁的互动与联结,将阿勒泰建构成观众心中的精神家园,同时也为当代影视作品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和情感体验。
关键词:《我的阿勒泰》;诗意田园;乡愁;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05(2024)14-00-03
影视剧《我的阿勒泰》围绕着几个生活在阿勒泰草原上的人物,通过细腻的叙事和精美的视觉表现,深入地描绘了北疆草原上的日常生活。剧中的人物生动鲜活,性格各具特点。轻喜剧风格的台词设定使故事显得清新有趣,饱含生活气息,情感表达自然真切。剧中自由驰骋的马儿、成群结队的羊儿、高耸的树木和英俊的哈萨克少年无一不流露着一种对于游牧田园生活中“古老而虔诚,纯真的人间秩序”的想象。本剧在对诗意田园进行建构外,还对观众的乡愁进行了一次召唤,使其在更广泛的文化和情感层面上与作品产生更为深入的认同和共鸣。
一、田园物理空间的建构
新疆的草场随着山地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分带性。牧民们世代根据季节的不同,在不同高度的草场间迁徙。在8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中,故事就是由牧民在春季向夏牧场进行“转场”这一线索而展开的。同时,在转场过程中,导演也完成了对田园物理空间的建构。
(一)浪漫化的自然景观
剧中的故事主线从彩虹布拉克伊始,途经仙女湾小道,在抵达夏牧场后迎来情节上的高潮,后又回到彩虹布拉克收尾。
“彩虹布拉克”是张凤侠生活的地方,她所经营的小卖部也坐落在这个村庄。于本剧的女主角李文秀而言,因妈妈(张凤侠)住在这里,这里便是她的家。这个村庄本叫萨依恒布拉克,但因为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便被不通方言的汉族女孩文秀称作“彩虹布拉克”。布拉克在哈萨克语中则有泉水之意。彩虹布拉克并不大,在那片草原上只有几个小房子,一个由砖头堆砌起来的“电视机”框架,这台电视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放映着这片草原上的风吹草动;也正因此,彩虹布拉克处处皆风景。
当初夏即将来临,母女二人跟随牧民一起迁徙夏牧场时,张凤侠坚持与苏力坦一家同行走仙女湾小道。在古代的传说中,如果有人在干枯的戈壁上行走至快要昏倒的时候,喝了仙女湾的河水,就会马上恢复体力。仙女湾对于牧民来说,象征着绝处逢生,所以在转场时有些牧人也会特地绕道此处祈求好运。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观众了解到仙女湾曾是张凤侠与文秀父亲第一次见面的地方,这也是她的世界里最美丽的地方。在剧中她坐在岸边面对着波光粼粼的仙女湾畅快地饮酒并诉说对已故爱人的想念之情,张凤侠由此又继续牵动着观众的情感,将其所经历的一切伤痛都化作对这片牧场深沉的热爱。
那仁夏牧场是剧中牧民们在夏天进行转场的目的地。那仁牧场在北疆的深山里,那里有着原始的牧道和未经破坏的地貌。当剧中人物翻山越岭抵达夏牧场时,观众便发现眼前尽是鲜花和草甸。那里水草丰美,随处可见的是牛羊在闲散地漫步,草原无边与天际相连,静谧又安详。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阿勒泰的壮丽景色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心灵上的抚慰与栖息。剧中的人物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也在这片草原上寻找精神的寄托,自然由此,便成了心灵的象征。
与动物和植物的和谐相处,是游牧民族生活的根本前提。剧中的人物不仅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珍惜,也传递出了人类生活与自然之间深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也展现了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方式。
在剧中,牧区的人们与牛、羊、骆驼和马儿终日为伴,关爱照料它们。牧民们以羊油做肥皂,用白桦树皮做稿纸,这片草原上的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他们面对自然毫无贪婪之情。因为爱惜牧场,所以在不停的迁徙中无以为家,只为给予每片水草恢复其旺盛生命力的时间和机会。也正是因为爱与互相尊重,这片牧场不仅养育着牧民和他们的牲畜,也治愈着在现代生活中屡屡碰壁的文秀,同时也邀请了观众们在剧中的大自然里寻找心灵的平静和慰藉[1]。
二、田园精神空间的建构
《我的阿勒泰》在视听语言上的精心设计为观众营造出了身临其境的观感。通过对广袤的草原、湛蓝的天空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描写,观众仿佛置身于田园之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的宁静与广阔。除此之外,诗意的感官体验不仅能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丰富了这部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也在观众的心中构建起了诗意田园的精神空间。
(一)理想的价值观
在《我的阿勒泰》中,人物往往是勇敢、勤劳和善良的。这些理想化的人物品质构成了田园生活的精神内核,与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给观众带来一种精神上的纯净和洗礼。
剧中的苏力坦曾是北疆草原上的传奇英雄和金牌猎人。当大多数牧民选择更为便捷的公路进行转场时,他也是唯一坚持转场绕路仙女湾的牧人。作为一个哈萨克游牧家族的大家长,他始终坚守着自身的原始文化。当他面对长子离世、儿媳改嫁,次子不愿继续游牧的现实,他知道由祖辈建立起的生活方式正在被逐步瓦解,他也慢慢地领悟到了适应时代发展的必要性之所在。出于父亲的身份,出于爱,他选择放手让家人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苏力坦喜欢骑马打猎,喜欢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游牧,所以他挥鞭返回牧场。尽管他将承受孤独,但还是勇敢地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张凤侠曾在剧中面对女儿对自己发问是否是个有用的人时,答道:“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样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早已经习惯了不停地追寻“意义”,而忘记了存在本身就有意义。张凤侠在此向女儿传递了自我接纳的重要性。她提醒女儿,无论外界的标准或要求如何,每个人的存在都有其意义和价值;她同时也在提醒观众,当今的人们常常因无法满足外部期望而产生自我怀疑和焦虑并不是一种健康的自我认知,功利主义的“有用论”也不是评判自我价值的关键[2]。
(二)温情的人际关系
哈萨克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和爱情源于“被看见”。在哈萨克语中,我爱你,便意味着“我清楚地看见你”。当讨论看与被看的关系时,人们好像难以避免地与凝视理论作出关联。但在这部剧中,“看”被还原成了最原初的,不经任何理论赘述的“深入灵魂的注视”,这种注视与权利、主客体关系或是性别差异等一切外因无关,它是一个人类发自内心地对另一个人感到欣赏和产生共情的过程。正如剧中主角文秀返回牧场后与牧民女孩托肯和库兰产生的纯洁无瑕的友谊。她们对彼此坦诚地分享少女情愫和各自的梦想。她们因为互相理解和尊重,所以互相帮助和照顾。同时,文秀与哈萨克族少年巴克提别克(巴太)之间的情谊也是建立于“清楚地看见彼此”。在两人的感情中,双方清楚地看见了对方的美好与优点,但同时也深知年轻的他们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两人在被对方理解、被对方接纳中产生了爱情,也正是出于理解和接纳,他们的爱情也没有妨碍任何一方成为更好的自己。此外,在《我的阿勒泰》中,导演也对亲情进行了诗意化的表达。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文秀奶奶的形象在小说原著中曾为外婆。导演在影视改编过程中作出这样的调整意在体现血缘并不是亲情唯一的纽带。亲情的呈现在剧中的每个家庭与人物关系之间都不尽相同。苏力坦和巴太之间的父子情暗含着代际差异的痛楚;托肯与两个失去爸爸的孩子之间的感情也必定在未来面临着众多考验,但是无论故事如何发展,所有的矛盾在剧中都在爱的指引下被化解,所有的错误也在亲情的温暖中被原谅。显然,剧中文秀与母亲张凤侠的关系是较为理想的母女形态:双方给予彼此无条件的爱和信任,在互相帮助和共同成长中让亲情给予彼此足够的力量去过好各自的生活,同时也在代际间让女性的智慧与力量得以传递,并使其迸发出最强的生命力。
除了亲情、爱情和友情之外,凸显《我的阿勒泰》中温情的人际关系的另一层面是来自两种文化背景的两种力量和信念在剧情中毫无障碍地得以共存。张凤侠作为这片草原的外来人,甚至是一个“他者”,她清楚地知道如何去尊重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与文化。她曾对女儿说,“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不能居高临下地改变他们”。导演通过剧中叙事,努力构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平等。这也是作者和导演在《我的阿勒泰》中所传递的:尊重是建立一切关系的基础[3]。
三、《我的阿勒泰》对于乡愁的召唤
对于田园的诗意化描述是中国影视作品中存在的一种典型的美学倾向,这种倾向在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作品中都有所呈现。这一点或许可以追溯到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从基层上去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之“土”是中国人的谋生办法,是命根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乡愁,与诗意田园的美学倾向一样,也源自对土地的依赖。在乡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推进的过程中,“乡”一字逐渐褪去了“返老还乡”式的最终归宿的意味,慢慢被弱化成为个体生命伊始,并且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也正是因此,农耕社会的传统型乡愁便随着现代化生活转型成为现代型乡愁。影视剧《我的阿勒泰》就是对观众心底的现代型乡愁进行的一次集体召唤。
(一)现代型乡愁
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和同质化使得许多地域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逐渐消散。人们开始怀念过去那些独特的、未被全球化影响的生活和文化,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愁。现代型乡愁是一种对过去、故乡或传统生活的怀念和情感依恋,但与传统乡愁不同,它不仅仅是由“背井离乡”的情感引起,它还涉及现代社会快速变化带来的心理和情感上的冲击。
现代化环境和现代化经验模糊了地理的、民族的,乃至国家的界限。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使许多人告别了他们的故乡和传统生活模式。这种变迁所带来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时常令人们怀念曾经的或是想象中的宁静和简单生活。怀旧者通过寻找精神归宿,试图应对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快速变化。在《我的阿勒泰》中,剧中角色对游牧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草原文化的坚守,是一种对于故乡和文化传统的深厚情感之表达。这种情感与现代型乡愁中的怀旧心理相呼应,反映了人们在变幻万千的现代社会中,对稳定、熟悉的生活方式之渴望[4]。
虽然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缩短了城市与故乡的地理距离,但它们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浅薄。进一步而言,愈发浅薄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人们的身份迷失。很多时候,寻求自我认同和情感归属的欲望便化作了对故乡和传统文化的怀念与想象。《我的阿勒泰》通过展示哈萨克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反映了集体记忆的传承,强调了人与故土、人与故乡文化的深厚连接,这与现代型乡愁中对文化根源和身份认同的渴望相呼应。在此基础上本剧还发起了对于在现代社会中保持文化认同之重要性的探讨,同时也为观众们的自我认同和文化归属感提供了一个想象空间。
(二)田园作为精神乌托邦
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对于过去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进行怀念,也成为现代型乡愁的一部分。在《我的阿勒泰》中,广袤的草原、巍峨的雪山、清澈的河流,构成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田园画卷。在剧中,壮丽的自然景观与淳朴的草原生活融为了一体,展现了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这种田园生活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联系,象征着一种远离城市喧嚣和现代生活压力的宁静与和平。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可以找到逃避繁忙现实的出口,得到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放松。剧中游牧民族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城市生活的超负荷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回归本真的精神视野。《我的阿勒泰》还通过描绘家庭、友情和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这种情感上的温暖和支持,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些画面和故事所构成的诗意田园,由此便成了观众心中的精神乌托邦[5]。
四、结束语
影视剧《我的阿勒泰》通过对田园生活和淳朴生活方式的诗意化描绘,对观众的现代型乡愁进行了一次集体召唤。它将阿勒泰化为精神乌托邦,让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温情故事对观众所面临的现代性下的精神空缺进行弥补。这部影视剧满足了观众对理想生活的向往;通过剧中对深厚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传承之表达,增强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故事情节中有关个人的成长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为观众提供了精神上的激励和支持,使人们在这片北疆草原上找到心灵的慰藉和归属。《我的阿勒泰》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情感和精神上的洗礼,带给了观众无尽的回味与思考。
参考文献:
[1][美]博伊姆.怀旧的未来[M].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贺岭,王梓妍,崔雪煜.新世纪新疆人文纪录片转型发展流变研究[J].声屏世界,2023(09):56-58.
[4]贾磊磊.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J].当代电影,1999(06):71-74.
[5]汤南南.从传统型乡愁到超越型乡愁[D].中国美术学院,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