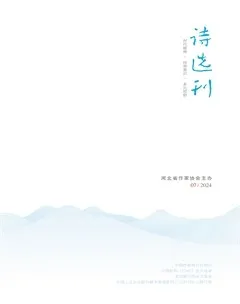闪闪发光、直入人心的明珠
2024-07-25 00:00:00王久辛
诗选刊 2024年7期
诗人普希金说: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公刘先生说;诗歌是精神的稀有元素。为什么说是明珠?又为什么说是精神的稀有元素?我的理解是,诗的语言是一剑封喉式的直抵人心的艺术。就是说,诗是以直击人心为艺术目的的艺术。如果你的诗与人心无关,或绕开了人心,或只有所谓的语言而无他指,只有能指,那么你的这个“诗”,就要被打上引号,归入非诗的一类。这就涉及了一个严肃而且庄重神圣的问题——什么是人心?人心在哪里?
在我看来,这么多年了,仿佛大家都在回避一个久违的诗歌标准:共鸣。我认为诗歌的他指,就是人心的共鸣。没有共鸣的诗歌,我以为就是没有能指的诗歌,至少不是好诗歌,因它没有情感的对应物。我知道有很多很高级的表达只能获得很少很少一部分人的共鸣,这里所谓的妙不可言,也是属于很少很少一部分人的。从探索的意义上说,为获得更大的共鸣而寻我先进的表达方式,我以为是属于学术试验——属于成功之前的千万次的失败、失败再失败的苦苦求索。这令人敬佩,而当探索的成果一旦被智慧聪明的诗人掌握再运用于创作实践并获得成功,即获得了巨大的共鸣,试验的价值和意义就显现了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共鸣与暂时忽略共鸣的试验,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诗歌创作一直都是寂寞的事业,而写出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才是诗人永恒的追求。而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成功经典,都是汲得了稀有精神而直击人心的诗人创作出来的。毫无疑问,大海不是明珠,贝壳不是明珠,虽然它们都为明珠的成长贡献了力量,但是它们永远不是明珠。明珠永远就是明珠本身,或者干脆说罢,明珠本身就是稀有的精神铸就的闪闪发光、直入人心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