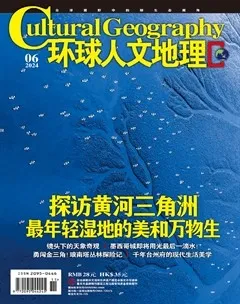勇闯金三角!

老挝北部的琅南塔省,与云南西双版纳以及缅甸接壤,属于一度令人闻风丧胆的“金三角”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游离于旅行者视线之外,至今仍是一片未被过度开发的区域。得益于默默无闻,反倒让它保存了完整的生态系统和原汁原味的人文景观。
我们有幸受到老挝文旅中心的邀请,在琅南塔腹地进行了历时三天的丛林探险。
1骑行:探索琅南塔街头风情
百年前殖民时代的印记依然清晰可见,不仅体现在建筑形制和文字上,也深深留在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里。Pheng告诉我们,当地人下午三点多就收工下班了,然后约上朋友去泡咖啡馆。
从磨丁出来的汽车沿着满是裂纹的公路驶离边境,司机不时猛打方向盘来躲避坑洞,但还是免不了一阵阵颠簸。随着茂盛的热带植物吞没了灰尘遍地的村庄,曲径通幽的丛林公路将我们领入琅南塔腹地。
不像早已名声在外的琅勃拉邦和万荣,琅南塔至今不被外人熟知,即便拥有淳朴的风土人情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都被“金三角”这枚巨大的负面标签所掩盖。在一个木屋的二楼,我们见到了此次户外活动组织方The Hiker的全体员工,主理人Tom已等候多时。The Hiker成立三年以来,每年会接待约一千名欧美人,我们是第一批中国客人。


午后,热浪退去,我们在向导Pheng的带领下来到一家租车行,计划骑车探索这个城市。与其说琅南塔是“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小镇。放眼望去,不见一栋高层写字楼或公寓,几排三四层的房子组成了这里的CBD。马路上见不到几辆车,显然也不会有非机动车道这种东西,所有车辆都共用一条道。我们头戴颜色鲜艳的头盔,脚踩“崔克”牌山地自行车,穿行在一堆破旧的摩托和三轮车之间,显得无比突兀。但路况没有想象中的混乱,反正大家都不赶时间,早一步晚一步无所谓,一副“你想先走就先走”的姿态。所以即便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当地人也能在一种无形的规则下保持秩序,这着实令我震惊。
拐弯进入一条小道。一离开主路,那些水泥建筑迅速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带院子的木质小屋。法式洋楼点缀在木屋和香蕉树之间,门廊种满花草,擦得锃亮的玻璃窗反射着太阳的金光。百年前殖民时代的印记依然清晰可见,不仅体现在建筑形制和文字上,也深深留在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里。Pheng告诉我们,当地人下午三点多就收工下班,然后约上朋友去泡咖啡馆。


朝着炊烟的方向骑行,渐渐地,路两边的房屋消失了,只剩开阔的稻田,满眼嫩绿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群山。农人们头戴斗笠在田里插秧,这里气候温热和雨水充足,水稻一年三熟,但当地人通常只种一季,其他两季休耕。我们在一座被称为“婚礼桥”的桥上驻足许久,回望来时的道路,暮色西沉,云霞被染成粉色,犹如欧若拉的裙裾在空中飘荡。
夜的幕布铺张开来,只剩西侧的天空还有微光。美景引人驻足,我和队友落在最后,没戴头灯,只能借着落日余光追赶大部队。在黑暗中骑行许久,向导Pheng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们身侧——他掉头接应我们了。我们和他聊着当地年轻人喜欢的音乐,以及过去几年间这里的变化,不知不觉追上了大部队。
2徒步:深入神奇的丛林秘境
这些神奇的物种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仿佛一不小心闯进了阿凡达的世界。我想此时就算遇到一头恐龙,也不觉得奇怪了。
第二天,我们前往南哈国家自然保护区进行雨林徒步。在保护区入口处停车时,完全看不出这有个徒步起点。树荫下坐着一群背着竹篓的年轻女子,见我们下车,她们迅速围过来,兜售一种名叫“三丫果”的水果。这种水果和龙眼一般大小,外皮是红色的,剥开后的结构和口感都和山竹十分相似。简单开了个行前会议后,我们便深入丛林。
刚开始就是个陡上坡,一尺宽的山间小径被茂盛的藤蔓和蕨类围了起来,就像一个绿色的洞穴。路上有很多倒伏的大树,从断面可以看出是虫蚁啃噬的结果。我们不得不从上方翻越或弯腰钻过。“除非完全阻碍通行,否则人们不会移除步道上的死树。”向导Thone说。

乍一看,也许会觉得沿途并没有特别之处,但留神观察,就会发现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长在角落里奇形怪状的蘑菇,像蛇脑袋一般倒垂着的芭蕉花,绒毛又软又长、好似玩具的毛毛虫……地上还散落着很多红色野果,正是刚才吃的三丫果。抬头望去,十几米高的树干周围长满了这种果子。我们好奇那些女孩是怎么摘到果子的?主理人Tom说,当地的女孩从小就会爬树,她们在丛林长大,这点高度难不倒她们。

越往密林深处走,看到的东西就越离奇。参天巨木垂下无数流苏般细长的红色根须,獠牙般的枝条缠绕在树干,形似海星的猪笼草正张嘴捕食猎物,鳞片泛着彩虹光泽的小蛇警惕地昂着头,拇指粗的马陆虫用它那上百条腿缓慢爬行……这些神奇的物种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仿佛一不小心闯进了阿凡达的世界。我想此时就算遇到一头恐龙,也不觉得奇怪。

Thone告诉我们,这个保护区是为了保护物种多样性而设立的,范围从中老边境一直到老挝北部的博胶省,覆盖了琅南塔24%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大型动物有亚洲象、虎、云豹、黑熊等,此外,鹿、野牛、野猪、猕猴、穿山甲和将近300种鸟类也在此繁衍生息。“老挝的工业不发达,但生态保护得很好。”Thone略带自豪地说。
走到一处稍宽敞的林间空地,大伙儿卸包休息,向导们开始准备午餐。他们找来一些干柴生起炭火,再用新鲜树枝搭建简单的烤架,没多久,罗非鱼的香味就飘散开来。其他食物都是现成的,包括糯米饭、肉末、竹笋和空心菜。大家围坐在芭蕉叶铺成的“餐桌”旁,用手抓着吃。食物的香味招致了众多飞虫和蚂蚁,而这些昆虫又吸引了蜘蛛前来捕食,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鸟雀——好一条食物链!
午后的密林下起雨来,很快便呈瓢泼之势。我深知在这种闷热的天气穿雨衣,身体照样会被汗湿,还不如淋雨来得痛快,因而只给背包套了防雨罩。温热的雨点劈劈啪啪打在竹叶上,水珠乱溅,地面也变得无比泥泞湿滑。虽然有登山杖,但有些下坡路还是得抓着树枝才不至于滑倒。
半小时后,阳光洒下来,雨后的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吸饱了水的植物叶片愈发鲜嫩,逆光下几近透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甜的薄荷清香。各种昆虫都出来了:吸食树汁的象鼻虫、米粒大小的银色蟋蟀、通体鲜红的蜻蜓、伪装到脚的竹节虫……我们兴致盎然地搜索着路边每一片树叶,不放过任何一处有意思的角落。如果说高原徒步的乐趣在于仰观广阔天地,那么雨林徒步的精髓就藏于脚下的微观世界。



在荒无人迹的丛林徒步6小时后,终于看到一个茅草小屋,地上有生火的痕迹。稍事休息,我们爬上一座小山丘,在山顶可以俯瞰山谷下方的梯田,七八间类似的小茅屋分布在田间地头。Pheng告诉我们,这些茅屋是农人在耕种和收获季节时的休憩场所。他又指着山脚一片被火烧过的痕迹说,这里的原住民仍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趁雨季来临前,他们会砍倒树木,晒干后放火烧出一片空地进行播种,来年再易地而耕。
下山穿过一片与人齐高的茅草丛,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Nalan村。三三两两的村民聚集在村中广场,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
Nalan村只有51户人家,没电没信号,仅有一条土路通向20多公里外的公路,而我们则是徒步了近7个小时才从另一条小径翻山而来。村里生活着老挝北部的原住民——Khmu人(中文翻译为“克木族”或“老听族”),人种学上属高棉族分支。他们依山傍水而居,平时以糯米为主食,同时也采集竹笋和蘑菇,捕鱼、狩猎,饲养猪、山羊和家禽等丰富食谱。就如Thone所说:“rely on what they can get from the forest and the river(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镇上有人每周在固定时间开皮卡,把食盐、糖等必需品带进村里,回程再将当地养殖的动物带出去售卖。但到了7~10月的雨季,道路泥泞无法行车,就只能依靠南哈河上的木船通行。至今,村里都没有医院,只有一位萨满巫师通过特定的宗教仪式和草药为人们治病消灾。

我们住进一间吊脚楼里,和当地人一样席地而睡。在地板铺上被褥,挂起蚊帐,就成了一张简单的床。整晚耳畔都是虫鸣,就像在丛林露营一般。
3皮划艇:在南哈河上激流勇进
我们在高速前进中须时刻躲避这些障碍物,或左腾右闪,或低头钻过,就像在玩现实版的“神庙逃亡”。
第三天,我们要两人共划一条皮划艇,沿着南哈河顺流而下。这条以保护区命名的河流在此处只有十来米宽,但沿途吸纳众多山涧溪流,最终向东离开森林注入南塔河时,已然成为可驳船的宽阔水体,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的第一条重要支流。
搭档Vong是一位来自附近村落的原住民,四五十岁的他皮肤黝黑,技术过硬,坐镇船尾把控方向,我坐在前头负责出力。我们手握桨杆有节奏地左右划动,很快便掌握了划船的基本要领:水面平静时奋力划船,过激流时把控好航道,看到浅滩暗礁则第一时间规避。
没划多久,一只掌心大小的蜘蛛出现在我的右腿上,我伸手去抓,它敏捷地跳到左腿,顺着腿肚子向上爬。再次驱赶它时,这只灵活的家伙一跃而起踩着水面溜走了。又在偶然间,灰色的蝴蝶停在手套上,我的划桨动作完全惊扰不到它们,它们似乎把我当成一棵在风中摇摆的树。岸边有大片竹林,干枯的竹竿如利剑般插入水中;卡波克树垂下蟒蛇般虬结的根茎和藤蔓;橡胶树粗大的树干倒伏在水面上,俨然架构起一座横跨两岸的桥。我们在高速前进中须时刻躲避这些障碍物,或左腾右闪,或低头钻过,就像在玩现实版的“神庙逃亡”。

沿途经过数个村庄,小朋友们在河里嬉水,看到我们纷纷钻出水面挥手,口中喊着“萨拜迪(老挝语:你好)”“拜拜”。据向导说,当地孩子很小便开始帮忙干农活,热了就来河里游个泳,凉快了再回去干活。而对很多村子来说,南哈河不仅是水源,也是洗衣沐浴的场所,还是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
我们在Namkoy村上岸,穿过一大片土豆田到达村里的取水站。一米见方的水泥池子上有一个水龙头,和Nalan村一样,这里也是通过水管从南哈河取水,简单过滤后就变成烧茶做饭的生活用水。这个项目是德国公益组织援建的,覆盖了保护区内的大部分村庄。水池边堆着一些发酵过的草秆,据向导Thone介绍,当地的Lantaen族就是用这种植物提炼出靛蓝色颜料染制衣服。Lantaen族最早是从中国南部迁徙而来,定居在南哈河的支流上游,所以也被称作佬魁族(Lao Houay,意为“在溪流边的老挝人”)。他们的文字是在古代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们看了看竹浆纸上的文字,每个字大致都认得,却读不懂连起来的含义。


见我们造访,好些孩子聚集到茅草亭,她们把腰包、杯垫、香袋等手工制品放在竹匾上展示给我们看。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学校——一间简陋的木屋。黑板上方挂着两张政治人物的头像,地上摆着几张七倒八歪的桌子。屋檐下挂着的“上课铃”吸引了众人目光,这竟然是一枚中空的炮弹,壳体锈迹斑斑,尾部的数字钢印仍旧依稀可辨。据向导 Thone说,这是越战时期落在老挝境内为数众多的炮弹之一,至今仍有很大一部分未排除。
告别村庄,上路3小时后到达一处三角洲,一条棕红色的水流在此注入南哈河,令河水变得浑浊。不远处一艘蓝色木船上,船夫坐在船尾划桨,两个男人站在船头收网。我听到搭档Vong在船尾哼起歌谣,对他来说,这样的皮划艇旅程就如散步般惬意吧。随着河面变得开阔,岸上出现电线杆,吊脚楼也越来越多,为期三天的丛林之旅进入尾声。
(编辑 王凤麟)

作者简介
周运
环球旅行家,摄影师,户外爱好者,热爱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深入秘境,探索未知,并将所见所思付诸镜头和笔尖。各大平台认证作者(网名:天天的世界地图),累计发表文章逾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