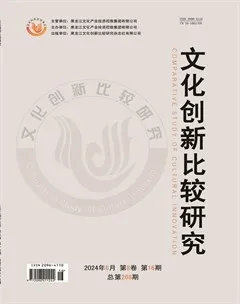辽金以前北京房山大理石使用历史考述
摘要:大理石材质细腻温润,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和价值观念,被广泛应用于石雕石刻和建筑当中。房山具有丰富的大理石资源,在元明清时期大量用于桥梁、宫殿等建筑的建设及各类碑刻,但目前对先秦至辽金时期大理石的使用情况了解较少。该文通过对文献及相关地区墓葬出土文物的梳理,发现房山大理石的使用与佛教传播、城市发展变迁息息相关。隋代以前,大理石主要作为一种玉石类资源进行使用,而且曲阳石雕的兴盛减缓了房山大理石的开发。隋代房山石经的雕刻,见证其开始进行大规模使用,之后渐渐用于各类佛教造像、石雕,房山大理石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关键词:大理石;石质文物;汉白玉;佛教;玉;雕刻
中图分类号:K8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6(a)-0064-04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Use of Marble in Fangshan, Beijing, Before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WANG Feng1, LU Jiabing2, LIU Muzhi3, WEI Shuya4
(1. National Centre for Archaeology,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13, China; 2. Beijing Stone Carving Art Museum, Beijing, 100044, China; 3. Beijing Haidian Foreign Language Experimental School, Beijing, 100195, China; 4.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Marble, as a kind of exquisite stone and keeping with the aesthetics and val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widely used in stone carving and architecture. Abundant marble resources were found in Fangshan district, which were exploited largely during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l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use of marble from the Pre-Qin to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use of marble and the spread of Buddhism, urban development was closely related through literature and unearthed artefacts from tombs in the related areas. Before the Sui dynasty, the prosperity of Quyang stone carving industry slowed down the development of Fangshan marble industry. As a result, marble in Fangshan was used only for jade objects in a long time. The large-scale utilization begun from the carving of Fangshan stone sutras in the Sui dynasty, and then the marble in Fangshan was used for various Buddhist statues and stone carvings gradually, indicating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rble; Stone cultural relics; Hanbaiyu; Buddhism; Jade; Carving
石质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北京地区石质文物遗存众多,其中石刻存量极大,现已知的石刻有近三万件,多存于首都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云居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等文保单位。刘卫东老师在《北京石刻史话》[1]中对北京地区石刻文物做了系统梳理。从新石器时代石斧、石铲等文化遗物到永定河故道被水冲刷出来的东汉石人,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佛教造像、碑碣、墓志到历经千年完成的“房山石经”,从辽金元时期的“秦王发愿纪事碑”、龙津桥到明清时期大量的建筑石刻、石雕,乃至民国时期的方尖碑、纪念碑等。石刻材质从初始的花岗岩一类逐渐转变为大理石为主。吴梦麟和刘精义先生,曾对北京历朝营建用石,尤其是明代宫殿陵寝采石进行了研究,表明大多数石材均来自房山区大石窝镇的大理石(青白石、汉白玉等)[2]。房山大理石有多个品种,如汉白玉、黄大石、青白石等[3],其中汉白玉质地细腻、洁白如玉,最为出名。但是,汉白玉史上并非专指房山产出的大理石,而是对白色大理石的习惯统称,产地主要有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保定市曲阳县、四川雅安市宝兴县等。因此汉白玉材质的文物,不一定为房山地区产出,还需细致甄别。
笔者认为,房山大理石的使用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先秦至南北朝的初始时期、隋唐至辽金的发展时期、元明清的鼎盛时期。元代在北京建立大都后,房山大理石大规模开采用于桥梁、宫殿、碑刻等,《故宫遗录》《五杂俎》《日下旧闻考》等文献中多有记载,北京现有元明清时期的大理石遗存实证也极多,故不再赘述,主要对第一和第二阶段进行梳理。
1 先秦至南北朝
房山地区大理石早期开采使用的记载基本未见,但在相关地理文献中,将其称为“婴石”“白玉石”“燕石”或“燕山石”。
《山海经·北山经》中提道:“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婴石。”晋代郭璞云:“言石似玉,有符彩婴带,所谓燕石者。”[4]关于燕所在地,《史记·周本纪》中有:“封召公奭于燕”,引用《括地志》“燕山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又引用《宗国都城记》“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5],所以“燕山”的地理位置在《括地志》中是在渔阳(今密云)东南60里,为蓟州区域。但是在1986年,通过对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发掘,尤其是1193号大墓[6]出土了铸有周王“令克侯于匽”等重要铭文的青铜盉、罍各一件,盉、罍上的铭文明确记载了周武王册封太保召公奭于燕的史事,明确了在西周时召公封地燕在现在房山琉璃河附近[7]。因此可推测《山海经》中的“燕山”是在如今的房山区,所提“婴石”也应该是郭璞解释的燕石,即大理石。
西周时期,传统用玉制度逐渐形成。《周礼》中记载:“(君子)凡带必有佩玉……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8]另外,在西周墓中也多发现葬玉。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玉石中,有白玉质的玉戈、玉圭等,另有白色石管、玉片等[9],虽未见科技分析结果,但此遗址距离房山大石窝仅20余公里,其中部分很有可能取自房山“婴石”。在陕西地区西周墓中,也多次发现汉白玉质的饰品,例如:宝鸡贤山寺沟III墓地和V墓地中的汉白玉片串饰,荒塬坡IV墓地的汉白玉圆饼形饰和汉白玉管[10]。但是距陕西较近的大理石产地,既有秦岭,又有岐山,所以来自房山地区可能性较低。
东周时期,《礼记·聘义》中有:“子贡问孔子曰:‘ 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对于其中提到的“珉”,柳志青等[11]经各类文献考证,认为“珉”是白色大理石。至于“珉”的产地,《山海经·中山经》中有所提及:“又东北百五十里,曰岐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白珉,其上多金玉”;“中次一十一山经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珉。”《山海经·北山经》中称房山大理石为婴石(燕石),所以“珉”虽然被考证为白色大理石,但并不指房山所产,而更有可能来自《山海经·中山经》中记载的山脉。赵越[12]通过对260 座东周燕国墓葬随葬陶器形制分析对比,发现燕、齐有较多接触,在虚粮冢、丰宁县凤山镇战国墓等墓地中也多发现玉石陪葬,虽未见具体材质分析,但当时房山的大理石也有可能随当时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而流通使用。
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新疆的优质和田玉料大量进入中原地区,由于其温润细腻,深得贵族喜爱,因此高等级玉器及墓葬玉衣多选用新疆和田玉。北京大葆台西汉墓虽然早年被盗,但仍出土74件玉器,其中玉变形夔龙纹璜、玉环等精美玉器均呈白色[13]。老山汉墓也出土3件较为完好的玉器,专家普遍认为是新疆和田白玉,并非汉白玉。随着汉朝统治力量的增强,与西域等地的经济流通被中央朝廷垄断,诸侯国难以得到优质的和田玉,使得制作玉衣所需的玉料只能就地取材,所以逐渐出现了用汉白玉等其他材质来制作玉衣、玉器的现象。例如:望都汉墓M2中出土了汉白玉石猪形手握、汉白玉蝉形琀1件,汉白玉石耳塞2件;东汉中山简王和穆王的玉衣是汉白玉制成,并非和田玉[14];蠡县汉墓出土汉白玉玉柙片222枚[15];东平县王陵山汉墓中出土汉白玉猪1件,汉白玉片1 647片[16]。但是,这些墓葬所在位置离河北曲阳大理石产地更近,而且曲阳石雕业在两汉时期已经初具规模,所以此时汉白玉的用料和加工更有可能来自曲阳。
除了葬玉,两汉时期墓地石刻也逐渐兴起,但在北京地区发现较少,仅现存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刻”“永定河拥盾石人”“三台子汉画像墓门”等少数石刻,目前研究并未证明其为大理石材质。
魏晋南北朝佛教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使得曲阳白石除用于建筑、墓葬雕刻、动物雕像之外,更多的是开始雕造佛像,曲阳汉白玉石雕发展进入繁荣时期,主要集中在河北易县至邯郸这一区域,山西、山东、陕西等地也均有曲阳白石造像的传世与出土[17]。相比之下,房山大理石此时仍基本被当做一种玉石资源,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圣水》[18]提道:“圣水出上谷,故燕地……水出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径大防岭之东首,山下有石穴……圣水又东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中提到燕地有圣水,圣水途经大防岭后向东经过多产珉玉燕石的玉石山。其具体位置,清末民初杨守敬与熊会贞作《水经注疏》,吸取历代《水经注》的研究成果,以《水经注笺》为正文,在圣水部分考证到[19]:“圣水以今地望准之,《水经》当云出涿郡良乡县西北圣水谷,与上谷无与……《寰宇记》大防山在良乡县西北三十五里。在今房山县西北二十五里。”赵永复在《水经注通检今释》[20]一书中根据杨守敬《水经注疏》和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又结合各方研究成果对水道进行了解释:圣水即今大石河、琉璃河,流经房山。所以《水经注》中的“珉玉、燕石”,基本确定为如今的房山大理石,当时仍作为玉石使用。但此时已经将房山大理石同样认作“珉”,而不局限于《山海经·中山经》记载的“珉”的产地,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燕石”和“珉玉”属于同一类型的石材,并加以开采利用。
2 隋唐至辽金
隋唐时期,伴随幽州(北京)佛教文化的兴起,房山大理石开始用于碑刻、雕像及石质构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自隋代开始雕刻的房山石经,是北京地区大理石大规模使用的存证。房山石经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云居寺,是我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的石刻佛经文献。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元年(605年),为高僧静琬肇始,云居寺历代僧众、幽州地区官民及多位游访至此的高僧续此事业,于14 278块石碑上镌下的1 122部佛经,其中隋唐时期刻经4 196块,辽金刻经10 082块。直到清康熙中期溟波和尚镌刻近20种佛教经、咒,竖立在寺内佛殿前和地穴边,至此房山石经历时1 100年雕刻结束,尤其是石经山雷音洞内发现的隋、明石函,是大理石雕刻的精品[21]。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研究报告指出[22],雷音洞中所藏的146块刻于隋唐时期的国宝石经,其石料主要是青白石质大理石,并推测隋唐早期刻经的主要石料采掘地应是独树村,即现今的房山岩上村一带。
唐代幽州地区已开采房山大理石用于雕刻和佛教造像,将成品或石材进贡至长安。《明皇杂录》[23]中记载:“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利。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 华清宫内汤池的考古发掘也印证了《明皇杂录》中所提精美雕刻所在。范阳位于北京以南,距离房山较近。唐代郑嵎《津阳门诗注》云:“石瓮寺,开元中以创造华清宫余材修缮,佛殿中有玉石像,皆幽州进来,与朝元阁造像同日而至,精巧无比,扣之如磐。”[24]可见佛教造像已大量使用房山大理石。北京姚家井唐信州刺史薛府君墓,出土了5件兽首人身汉白玉石雕,分别为十二生肖中的龙、蛇、羊、鸡、猪,是十分精美的雕刻艺术品[25],并基本可以确定取材于房山。以上记载和实证,表明唐代的房山大理石雕刻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繁,社会极度不稳定,生产生活遭到很大破坏,关于房山大理石仅发现少量实证。例如,北京南郊的辽(五代)赵德钧墓,考证其年代约公元937—958年,墓中发现汉白玉碗[26]。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献于契丹(辽),宋朝建立后,多次尝试从辽手中收取幽州(今北京)未果[27]。故此时房山大理石的开采使用可借鉴辽、金史料和文物实证。
辽代疆域内现存的大理石制品常见汉白玉佛教造像,例如,辽宁省朝阳博物馆馆藏汉白玉观音像(原位于朝阳凤凰山天庆寺)、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汉白玉释迦佛涅槃像。辽国原本并没有佛教传播,但随其领土不断扩张,治下汉民等各族人口不断增多,在建造城池的同时,也建设了许多佛教寺院,通过佛教文化帮助稳定社会[28]。结合当时管辖范围,辽代汉白玉类佛教造像或者汉白玉原料应主要出自房山,并随佛教传播在北方流通。同时,宋代士人依然保持了对大理石(汉白玉)的喜爱,用于欣赏把玩,例如:宋代杜绾作《云林石谱》中写道:“燕山石出水中,名夺玉,莹白而温润,士人琢为器,颇似真玉。”[29]可见,当时虽然认识到大理石并非真玉,但由于其符合士人或儒家的审美观,是莹白温润可“夺玉”的。此外,虽然燕山石在辽金控制范围内,宋朝士人依然能够获取,说明房山大理石的生产制造和流通已经颇具规模。
贞元元年(1153年),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迁至燕京(今北京),定为中都,主要区域位于现在的西城区和丰台区,并在房山地区修建金陵,此阶段中都大兴土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鼎盛[30]。《金史·礼七》中提到:“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坛于中都。……中央覆以黄土,其广五丈,高五尺。其主用白石,下广二尺,剡其上,形如钟,埋其半。”[31]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资政殿大学士范成大出使金国,对沿途的风景名胜进行记录并将其整理成《揽辔录》,其中记载:“丙戌至燕山城外燕宾馆。……过石玉桥,燕石色如玉,上分三道,皆以栏楯隔之,雕刻极工。中为御路,亦拦以杈子。两旁有小亭,中有碑曰‘龙津桥’。”[32]说明当时随着中都的大规模建设,大理石不再局限于玉石,以及佛教造像、石雕等方面,而是开始用于桥梁及重要建筑的建设。房山大理石由此开始伴随元大都、明清都城的建设,进入开采利用的鼎盛时期。
3 结束语
北京房山大理石资源早在先秦时期便已被发现。在两汉魏晋时期,虽然玉文化和佛教雕刻兴盛,但是河北曲阳石雕行业的发展,导致房山汉白玉很长时间范围内仅作为一种玉石进行使用,直到隋代雕刻房山石经才开始大规模开采,用于佛教造像、碑刻、雕塑及少量石质构件。金朝设中都于北京之后,房山大理石进入全面开发利用时期,不断为北京地区的碑碣、雕像、大型建筑等添砖加瓦,成为北京地区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两汉至南北朝期间,房山大理石的利用情况缺乏记载和出土文物的科学分析与溯源,曲阳石匠在房山大理石开发中的作用也不明朗,还需要通过更多研究来厘清当时的社会生产和文化交流情况。
参考文献
[1] 刘卫东,刘语寒.北京石刻史话[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22.
[2] 吴梦麟,刘精义.房山大石窝与北京明代宫殿陵寝采石:兼谈北京历朝营建用石[C]//中国紫禁城学会.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10.
[3]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文体中心.“国宝”汉白玉石雕文化艺术发展史[C]//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2011—2013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集.[出版者不详],2013:5.
[4]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116.
[5]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 中国杜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0(1):20-31.
[7] 薛兰霞,杨玉生.论燕国的五座都城[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6(1):88-93.
[8]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1482.
[9] 杜金鹏.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宝玉石器研究[J].东方考古,2019(00):114-133.
[10]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28-129.
[11]柳志青.破译孔子所述的玉和珉[J].浙江国土资源,2004(2):56-58.
[12]赵越.东周燕国墓葬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9.
[13]周南泉.北京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玉器古代玉器系列讲座之六[J].收藏家,2001(8):18-22.
[14]王静.汉代玉衣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8.
[15]文启明.蠡县汉墓发掘记要[J].文物,1983(6):45-52.
[16]蒋英炬,唐士和.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6(4):6,189-192.
[17]王林丹.河北曲阳汉白玉石雕的历史考察[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5.
[18]郦道元.水经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5:186.
[19]郦道元.水经注疏[M].杨守敬,熊会贞,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099.
[20]赵永复.水经注通检今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29.
[21]管仲乐.房山石经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9.
[22]张小英.千年房山石经,石料从哪儿来[N].北京晚报,2019,11:19.
[23]郑处诲.明皇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4:28.
[24]金申.佛教美术从考续篇[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143.
[25]卢亚辉.唐信州刺史薛府君墓所见幽营二州薛氏[J].北方文物,2023(5):77-83.
[26]苏天钧.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J].考古,1962(5):246-253,11-12.
[27]曾凡玉.北宋燕山府[J].西部皮革,2017,39(12):209-210.
[28]李靖.朝阳博物馆馆藏辽代汉白玉观音像的保护与修复[J].参花(上),2021(1):76-77.
[29]杜绾.云林石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2:148.
[30]丁利娜,张中华,孙峥.北京金中都城墙遗址2019—2020年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2023(6):59-75.
[31]脱脱.金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459.
[32]范成大.揽辔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