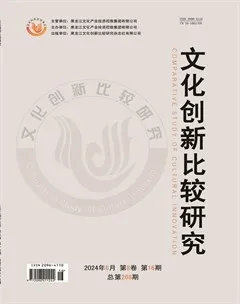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在英汉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摘要:该文运用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对赞比亚作家多米尼克·穆莱绍的作品《哑巴之舌》的部分翻译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该小说的翻译文本运用了翻译转换理论中的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下的结构转换、类别转换及单位转换。具体而言,层次转换中使用了时态转换和单复数转换;结构转换中涉及了肯否定转换、主被动转换和前后置定语转换;类别转换中包括了英语介词转译为汉语动词和英语形容词转译为汉语动词;单位转换涉及单词转化为短语和句子转化为分句。该文进一步验证了翻译转换理论对小说文本英汉翻译的重要指导作用,以期为未来的英汉翻译实践提供相关经验。
关键词: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英汉翻译实践;小说翻译;《哑巴之舌》;多米尼克·穆莱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6(a)-0029-05
The Application of 7zZqGL0ifg8BiQB7tEG5ww==Catford's Translation Shift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Practice
—Taking Chapter 8 of The Tongue of the Dumb as an Example
LIU Yizhuo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Catford's Translation Shifts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of Zambian writer Dominic Mulaisho's The Tongue of the Dumb.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ed text of the novel uses level shifts and category shifts which include structural shifts, class shifts and unit shifts. To be specific, tense conversion and singular-plural conversion are used in level shifts. The structural shifts involve positive-negative transformation, active-passive transformation and attributive transformation. Class shifts inclu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into Chinese verbs and English adjectives into Chinese verbs. Unit shifts involve the conversion of words to phrases and sentences to clauses. This paper further verifies the important guiding role of Translation Shifts in novel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levant experience for the future practice of E-C translation.
Key words: Catford; Translation Shifts;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practice; Novel translation; The Tongue of the Dumb; Dominic Mulaisho
卡特福德在其著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第十二章“翻译转换”(Translation Shifts)中论述了翻译转换理论。他认为“转换是翻译实践最基本的方法。翻译本身是指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把一种语言的声音、文学、词汇和语法系统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各个系统。只要我们承认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就必须承认翻译转换的合理性”[1]。他还借用了韩礼德的系统语法及对语言的分类来说明翻译转换现象。系统语法理论有三套基本层次(形式、实体和上下文)、四个基本范畴(单位、结构、类别和系统)和三个阶(级阶、说明阶和精密阶)。卡特福德根据语言的层次和范畴,将翻译转换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层次转换分为语法和词汇两个层次,范畴转换包括单位转换、结构转换、类别转换和系统内转换四个范畴[2]。
1 《哑巴之舌》及翻译文本介绍
《哑巴之舌》(The Tongue of the Dumb)是作家多米尼克·穆莱绍(Dominic Mulaisho)(1933—2013年)出版于1971年的非洲赞比亚小说。不仅是赞比亚作家对海涅曼(Heinemann)的“非洲作家系列”(African Writers Series)丛书的第一篇贡献,也是最早在世界闻名的赞比亚小说之一。多米尼克·穆莱绍是赞比亚小说家和公务员,曾就读于津巴布韦大学,学习经济学、历史和英语。他以两部小说——《哑巴之舌》(1973 年)和《雷鸣般的烟雾》(1979 年)而闻名,但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赞比亚政府工作,曾担任赞比亚教育部常务秘书、矿业发展公司执行主席、赞比亚银行行长等多个高级职务。
小说讲述了卡翁加山谷中的姆波纳村里,议员鲁宾达一直觊觎酋长的位置,用各种方法试图取代酋长,最终并未成功的故事。姆波纳村先后遭遇洪水、蟒蛇、蝗虫、饥荒、旋风的袭击。白人还对他们提出了纳税、驱逐麻风病人、接受白人的宗教和文化习俗等要求。鲁宾达利用民众的不满,公开挑战酋长,指责他把王国出卖给白人,还违反了部落的习俗。然后他提出了最严重的指控:酋长和他的同伙——老师、寡妇娜托比都是女巫,从而发起了一场推翻酋长的运动。最后酋长和他的同伙被证明清白,鲁宾达被村民抛弃,死于野外。小说重建了非洲土著与欧洲殖民文化之间的对抗与融合。
翻译素材选自该书第八章的部分内容,共3 010字。讲述了在姆波纳村经历饥荒的背景下,被村民排挤的纳彤碧带儿子姆瓦佩外出寻找食物,途中遇见白人传教士,返回村庄后仍被村民排斥,写信向堂弟寻求帮助的故事。本章原文语言平实,注重情节建构。在词语运用上不拘一格,例如用一组名词来表达动词意义,用一组动词来表达名词意义。在句子结构中,有许多名词、连词、副词等,它们的用法与中文有很大不同。因此,作者采用卡特福德的翻译转化理论,探讨该文本的翻译策略。
2 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在《哑巴之舌》英汉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2.1 层次转换
层次转换指“处于一种语言层次上的原语单位,具有处于不同语言层次上的译语翻译等值成分”[3]。语言层次通常涉及音位、字形、词汇和语法,而其中,字形和音位之间无法直接转换,也不能与另外两者进行转换,但是词汇和语法之间却可以相互转换。因此,层次转换通常指从语法结构到词汇结构或者从词汇结构到语法结构的转变。
2.1.1 时态转换
在英语语法中,有时态和体的划分,其分类主要通过单词的形态变化表现出来,如英语时态中的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体类中的进行体和完成体,都有相应的语法规则。而汉语并没有相对应的形态变化,需要通过“已经”“了”“过”等副词和虚词来表达时间关系。因此,在英汉翻译时,英语中通过单词形态表现出的时体变化需要通过汉语副词、虚词等词语来传达原文意思,这属于词汇和语法之间的转换。
例1:
原文:"It is against our tradition," said Lubinda for the seventh time, "to rebuild a house which we should have destroy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cause he that lived in it had died. "
译文:“重建一所房子是违背我们的传统的。”鲁宾达第七次说道,“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人已经去世了,我们本应在第一时间摧毁它。”
分析:英语用“had+done”这一形式,表示在过去某一时间之前已经完成的动作。例1中,通过“said”可以看出整个语境发生在过去。用“had died”表示鲁宾达在说话时(这一过去动作发生时),住在房子里的人,即杜拉尼已经去世了。在此结构中,had作为助动词并没有实际意思,它的使用是为了向读者表达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 die作为实词,表示“去世”。因此,在英汉翻译时,需要用词语“已经”表示在说话前“杜拉尼去世”一事已经发生,属于从语法到词汇的转换。
2.1.2 复数转换
在单复数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也存在差异。英语是屈折词汇,其名词的单复数有形态的变化,可以在词尾添加“s”或“es”来表达复数含义。而汉语则没有这样的形态变化,主要是通过量词或“们”“许多”“大量”“多数”等词语表示复数。
例2:
原文:Thugs have frustrated our tradition, our ritual.
译文:暴徒们破坏了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仪式。
分析:例2中,英语名词 “thugs”被译为“暴徒们”,增加的“们”这一词,可以看作表复数的“s”的翻译等值成分。若是去掉“们”一字,译文会表意不清,读者也随之产生是“一个暴徒”还是“多个暴徒”的疑惑;加上“们”字,表明暴徒的数量不止一个,能更好地传达原文意思。
2.2 范畴转换
范畴转换是指“翻译过程中脱离形式的对应”(departures from formal correspondence),范畴转换主要分为结构转换、类别转换、单位转换和内部体系转换[4]。
2.2.1 结构转换
结构转换主要体现在语法的结构转换上。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二者既有共性,也存在着诸多差异。语言学家王力指出“在句子结构上,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西洋语言无论需不需要主语,都要求句子形式的一致;而中国语言则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拘泥于特定结构,只要能使对方听得懂就行”[5]。英语大量使用定语从句、分词结构、短语等,而汉语并没有如此多的对应结构。因此,结构转换就变得很有必要。
(1)肯定和否定结构转换
在表达肯定和否定意义时,英汉语言所用词汇和语法并不相同。如果一味按照源语的肯否定表达来翻译,会使译文表意不准确、不流畅,使读者难以理解。因此,在英汉翻译时,要跳出源语框架,灵活变通地应用肯否定结构,努力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相符的效果[6]。
例3:
原文:For two days they walked on without meeting anybody or coming across a village.
译文:他们走了两天,没有遇到任何人,也没有碰见任何一个村庄。
例4:
原文:She had realized that she could not go on and on from one village to another, never saying what she had come for.
译文:她意识到,她不能一直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而从来不说她来村庄的目的。
分析: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肯定表达和否定表达,英语否定句中常见“no”“not”“none”等否定词,而汉语否定句中常见“不”“无”“非”等否定词。除了由否定词构成的否定句外,英语中还存在许多带有否定意味的肯定句,句中虽没有出现诸如“no”“not”“none”等否定词,但出现某个词派生出的反义词或是自身带有否定含义的词。这种情况下,译者往往需要将原文中的肯定句转换成译文中的否定句,将其中的否定含义明晰化,以符合汉语的思维习惯。例3和例4中英文并没有出现“not”“no”等否定词,在翻译时,理应避免使用汉语的否定词汇。但“without”一词本身便隐含着“没有、缺乏”之意, “never”一词也含有“从不、未曾”之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仍然要将”without”和”never”的隐含否定意思使用“没有”“从不”这类否定词汇来表达。
(2)主动和被动结构转换
英语和汉语都有主被动结构的区分,但使用偏好有所差异。英语因注重形合、句法结构及表达形式而多采用被动结构。汉语由于受主体思维影响,多使用主动结构。此外,被动结构的标志词“被”字在中文中含“蒙受、遭受”之义,使汉语“被”字句于被动结构外多了一层不如意和不愉快的语义色彩[7]。因而,由于主被动结构的使用偏好差异,在英汉翻译时常发生主被动结构的互换。
例5:
原文:He repeated, somewhat irritated by Lubinda's impassivity.
译文:他又重复了一遍,对鲁宾达的冷淡多少有些生气。
例6:
原文:According to our tradition, the dead man's house must be demolished.
译文:根据传统,我们必须拆除死者的房子。
分析:英语中常常使用被动结构,汉语中常常使用主动结构。在翻译时,如果完全根据英文中的被动结构来译,则不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例5中,笔者将英语中“he(受事) +was irritated by(行为)+ Lubinda's impassivity(施事)”的结构转化为汉语中“Lubinda's impassivity(施事)+irritated(行为)+him(受事)”的结构,即将英语中的被动结构转为汉语中的主动结构——“他对鲁宾达的冷淡多少有些生气。”这一表述使译文更加流畅,更加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例6中,动作的实施者是“we”,而动作的承受者是“the dead man's house”,通过“be demolished”这一动作连接起来。若是翻译为“死者的房子必须被拆除”,句子过于烦琐与晦涩,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因此改为主动形式“我们必须拆除死者的房子”。
(3)后置定语与前置定语的结构转换
根据所在位置的不同,定语一般分为前置定语和后置定语。用在所修饰词之前的定语称前置定语,用在所修饰词之后的定语称后置定语。由于英汉语言在语法结构、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汉语常用前置定语,而英语多用后置定语。因此,译者在英汉翻译中不得不按照汉语的句法特征对原文重新进行编排,修改句式、调整语序。
例7:
原文:Mwape, who had gone ahead of his mother, saw the man.
译文:走在母亲前面的姆瓦佩看见了那个男人。
分析:例7中的主语为Mwape,其后面的“who had gone ahead of his mother”为定语从句,修饰Mwape。若是机械地根据原文语序翻译,则译文形式为“姆瓦佩走在母亲前面,他看见了那个男人。”但由于汉语追求简练,这种形式对应而得出的译文过于烦琐,并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因此译文中将后置定语“who had gone ahead of his mother”转变为前置定语“走在母亲前面的姆瓦佩”,以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
2.2.2 类别转换
类别转换也称词类转换,产生在与源语单位处于不同类别的译语单位中,如英语介词与汉语动词、英语形容词与汉语动词。
(1)英语介词转译为汉语动词
英语中有的介词(如across)在与with连用时,有些介词(如against)在与be连用时,带有动作的意味。而汉语中,人们常常使用动词,因此,为了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在翻译为汉语时往往也会译成动词。
例8:
原文:It is against our tradition.
译文:重建一所房子是违背我们的传统的。
例9:
原文:Towards the evening of the second day and after through the thick bush, they suddenly came upon an open and cleared space, and then a field of corn.
译文:第二天傍晚时分,他们穿过茂密的灌木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阔的空地,紧接着是一片玉米地。
分析:英文中多使用介词,而汉语则多使用动词。为更符合中英文表达习惯,在翻译时可以根据上下文和句意,将表达动词意义的英语介词和汉语动词相互转化。在例8和例9中,“against”原为介词“反对”;“ through”原为介词“通过”。将原文词性直译难以译通,且against前面加上系动词be时,通常带有动词意味,这时可以将其转换为动词“穿过”,直接形象地再现鲁宾达提出质疑和纳彤碧带姆瓦佩外出寻找食物的场景。通过类别转换,不仅使译文表达更加流畅准确,还使译文更加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2)英语形容词转译为汉语动词
例10:
原文:The man was stunned.
译文:老师惊呆了。
分析:该句中的“stunned”意思是形容词“惊呆的”,用来说明老师听到纳彤碧拒绝和她回家后的反应。在翻译时,若不改变词性,照搬该词的表达结构,翻译为“老师是惊呆的”,读起来刻板且生硬。因此,要将形容词“惊呆的”转换为动词“惊呆”。通过词性转换既可以将静态的句子动态化,突出老师的惊讶,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又可以达到表意清晰、语义顺畅的目的。
2.2.3 单位转换
单位转换即“源语中某级上一个单位的翻译等值成分为译语不同等级上的单位这样一种形式对应脱离”[8]。英语和汉语语法中均有词组、分句和主句的分类单位,除此以外英语语法中还包括语素和单词,汉语语法中还包括字、词。英汉不同级别单位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1)单词转化为短语
例11:
原文:Besides, she knew the teacher, he was an understanding man.
译文:此外,她知道老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分析:汉语多使用短语,四字短语尤其深受中国人喜爱,可以使表达更加简洁灵活,韵律整齐,朗朗上口。因此,在英汉翻译中,英语单词在很多情况下会处理成汉语短语。例11中, “understanding”一词表示“理解力强的”,但汉语重意合,在此处若是用“理解力强的”一词,译语语言生涩。所以,按照汉语习惯,将原文"understanding”一词译成四字短语形容词“善解人意”更加贴切。
(2) 句子转化为分句
例12:
原文:He blinked his eyes and knit his massive brows. He stood waiting to see who the strangers were.
译文:他眨了眨眼,皱了皱眉头,站在那里等着看那些陌生人是谁。
分析:例12中包含两个独立的句子,若按照原文结构翻译,处理为两句话,则为“他眨了眨眼,皱了皱眉头。他站在那里等着看那些陌生人是谁”,会使译文前后文割裂,不够连贯。笔者在翻译时观察到这两个句子主语一致,因此,考虑将原文第二个主句降级为分句,与前一个句子共用一个主语,变为“他眨了眨眼,皱了皱眉头,站在那里等着看那些陌生人是谁”,这样表达既符合汉语追求简洁的特点,保证了译文内容的连贯性和流畅性,也充分表达了原意。
2.2.4 系统内转换
系统内转换发生于体系内部,指原语和译语的结构在形式上大致对应,但在翻译时却要在译语体系中选择一个非对应的术语[9]。此类转换在英法翻译中常常见到,因二者同属印欧语系,两种语言有诸多相似点。比如,英语和法语数的体系在形式上相对应,但在翻译时,英语名词的单数经常译为法语名词的复数,法语名词的单数需要译成英语名词的复数[10]。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内部语系的转换并不常见。笔者在此次实践过程中也并未遇到此种类型的翻译转换。
3 结束语
在本次翻译实践中,笔者结合实践文本的特点,采用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列举了十多条例证,探讨了层次转换、类别转换、单位转换和结构转换的应用,验证了翻译转换理论对小说文本英汉翻译的重要指导作用,有助于提高汉译作品的翻译质量。
此外,此次翻译实践再一次加深了笔者对英汉语言差异的认识。如英汉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使得两种语言在被动与主动形式、肯定与否定表达及定语的位置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英语注重形合,而汉语注重意合;英语惯用长句,而汉语惯用短句。
当然,本次报告还存在很多局限和不足。本报告中只探讨了句子及以下层面的转换,未涉及宏观层面的翻译转化情况。受翻译内容和篇幅所限制,分析实例并没有展现所有的翻译转换类型。在译文质量方面,由于笔者语言表达能力还有限,译文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 穆雷.卡特福德与《翻译的语言学理论》[J].语言与翻译,1993(2):54-56.
[2] 穆雷.评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J].外语教学,1990(2):37-42.
[3] CATFORD J.A Linguistics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4] 王青.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在Privac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汉译中的应用[D].南京:南京大学,2016.
[5]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5.
[6] 逯继仙.转换理论指导下侦探小说的英汉翻译[D].太原:山西大学,2020.
[7] 李珊.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8] 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穆雷,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92-93.
[9] 田京林.《人工智能应该做什么:构建任务授权的框架》及《图像字幕:将目标转换为文字》翻译实践报告[D].青岛:青岛科技大学,2021.
[10]刘婷婷.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指导下的非文学翻译[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