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虚无,他们花钱发疯

在远离城市人烟的郊区森林,一群人驱车而至,在树林中坐下来调整呼吸、感受情绪。随后,各自在地上找到一根趁手的木棍走入密林中。
他们分散开来,驻足在自己喜欢的空地,然后,一边握着手中的木棍疯狂敲击地面,一边不断发出大声的尖叫。
这并非什么生物变异、丧尸大片的拍摄现场,而是一场有组织的“愤怒仪式”。这些特意远道而来的、尖叫着的参与者,可是为了这场酣畅淋漓的“发疯”花了大价钱—即便是单纯的“一日疯”,也要花上220美元(约1600元人民币),如果附带“发疯”前后的相关行程及心理按摩,整个套餐最贵可以接近8000美元(约5.8万元人民币)。
近期,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发疯潮流蔚然成风。
“发疯”并不陌生。在中文社交网站上,“人哪有不疯的”也曾一度占据社交网站头条,人们用搞怪的图文表达自己在生活压力之下“美丽的精神状态”。但在这些网友们还仅仅停留在“发疯文学”的线上抱怨层面,国外的“疯子”们,已经在现实中砸下重金、抡起棍棒、发出尖叫……以一种意料之外的吊诡方式,向不如意的生活开炮。
付费发疯
今年6月,米娅·班杜奇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招募帖子。在招募页面,法国卢瓦尔河谷的特色城堡建筑作为背景,“Claim your queendom”的花体字文雅地叙述着这场活动的目标—“领取”属于你自己的女王。
熟悉米娅·班杜奇这个名字的人,很容易发现幽静城堡与冷静文案之下的端倪—这位班杜奇,曾组织过多次“收钱发疯”的项目,想必这“领取”女王的方式,也与发疯脱不了干系。
这个宣泄过程要求至少持续20分钟,直到参与者的手臂麻木、疲惫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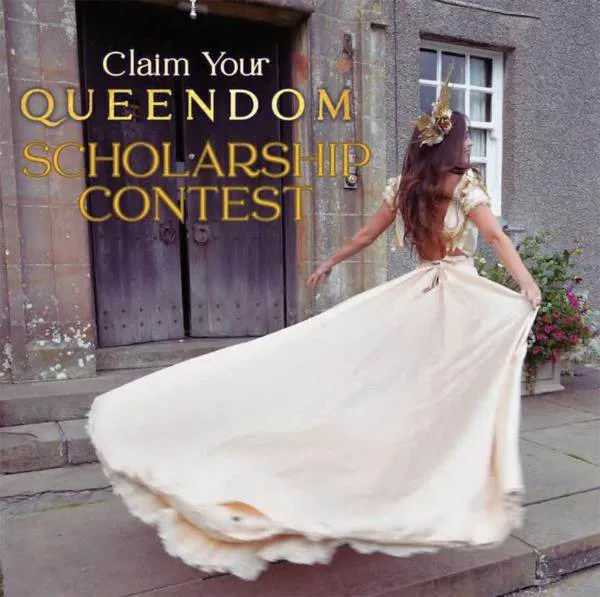

果然,在招募细则里,班杜奇表示本次活动“包下了法国的场地让你宣泄内心情绪”,只要付费,就可以尽情发疯。如果选择8月加入,人均“只需要”6000—8000美元(约4.2万—5.6万元人民币),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和“不会再有的划算价格”。
之所以敢开出这样的价格,是因为班杜奇在“发疯导师”这个赛道已然小有名气。过去几个月,她举办的主要针对女性客户的“愤怒仪式”就广受欢迎。
班杜奇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网络安全工程师。最初的“愤怒仪式”,是她自己面对生活压力的独特方式:一旦觉得情绪无法排解,就一个人跑到远离城市的森林中,先静坐冥想,再大喊、尖叫、用树枝在无人的森林中“搞破坏”,以此宣泄情绪,再回到城市生活中扮演情绪稳定的人。在意识到这种定期“发疯”让自己更快地卸下情绪重担、更健康地应对生活以后,班杜奇开始邀约自己的朋友一起加入,直到闻讯而来的人数不断拓展,“愤怒仪式”也做成了一门生意。
和今年8月这次尚未开始的、法国庄园内的“发疯”不同,此前在森林中举办的“愤怒仪式”价格相对“低廉”—费用大概在2000—4000美元间。
仪式开始前,班杜奇会引导参与者先简单进行冥想,向自己的内心探寻,诚实地面对那些令自己情绪崩溃的部分。冥想过后,大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发疯”。
而作为“导师”,班杜奇会鼓励参与者在脑海中一直念着刚刚冥想时想到的糟糕部分,想象自己“正在遭受不公平的、令人气愤的对待”,然后将这股愤懑化作不控制音量的尖叫与用棍子疯狂敲打地面的力度—这个宣泄过程要求至少持续20分钟,直到参与者的手臂麻木、疲惫不堪,再也无法继续为止。
“原始尖叫疗法”
花钱“发疯”,到底有没有效果?
对同为网络安全工程师的“买家”金伯利·赫尔穆斯来说,这个回答是确凿无疑的“Yes”。两年前,她与丈夫离婚,身心俱疲的她选择付费参加班杜奇组织的苏格兰静修之旅,想在旅途中摆脱失意婚姻带来的痛苦。静修旅行中的这场有组织的“发疯”,并不在她行前的了解范围内,但有导师引导、有伙伴一起,显然让不那么体面的宣泄变得无比合理,她也成了尖叫着用树枝抽打地面的一员。

“奶头乐”不会带来真的快乐,忍耐、压抑与机械顺从也缺乏意义,不如“发疯”。
结束时,她手中的树枝早已被抽断,因为动作太过激烈,她周身沾满了自己溅起的泥土,手上还有树枝的割伤,看起来极为狼狈—但有些前所未有的、直面自己带来的轻松却在气喘吁吁中缓慢升腾。
按照她的描述,在扔掉棍子跌坐在地上休息时,她发现自己对前夫没什么怨恨,甚至那桩失败的婚姻似乎也无足轻重—在这个与自己较量的发疯时刻,她意识到,真正让自己对生活感到难以言说的痛苦的,其实是另一件童年旧事。15岁那年,她亲眼看着好友去世,痛失挚友、直面苍白的死亡,15岁的她心中就此隐藏了无法抹去的悲伤。只是一个孩子的悲伤与恐惧并未被及时体察与纾解,它们成了未经处理、无法面对的隐疾,在她此后的人生中如鬼魅般时隐时现,直到这次,她才终于借着名正言顺的疯狂,与心魔面对面斗争—然后放过自己。
金伯利·赫尔穆斯的感受并非“花钱发疯”后的自我安慰。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亚瑟·贾诺夫就曾开创并实践过一种名为“原始尖叫疗法”的心理治疗方式,它的实施方式与“发疯仪式”相同:通过大声发出尖叫、击打某些物品来完成治疗过程。
亚瑟·贾诺夫认为,生活中经历过的痛苦都会在内心给人留下一个印象,成为最终可能会在精神与感情上威胁到人心理健康的潜意识。在科学引导下进行的尖叫与击打,并非随意的大呼小叫,而是将那些负面的潜意识投射出来重新审视与释放—这一招对因压抑的童年创伤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有效。
用荒诞对抗“草台班子”
意识到这种“发疯”能让自己卸下那些阴暗角落中的重担、在走出树林回归正常生活后明显能感受到更多幸福、平静与快乐之后,金伯利·赫尔穆斯开始多次“回购”,频频参与“付费发疯”。

除了班杜奇组织的活动之外,如今,付费参加“发疯仪式”的选择很丰富,地点也从郊区树林逐渐向环境更优雅的庄园迁移:6月,作家杰西卡·里凯蒂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办“神圣愤怒”女性静修会;7月,一个名为Secret Sanctuary的组织要在加拿大艾伯塔省举办“神圣愤怒仪式”……
事实上,“付费发疯”也并非班杜奇等人原创的新鲜事。早在数年前,“发泄屋”就曾风靡全球,只要支付相应的费用,就可以到经营者设置好的房间中砸碎碗碟、家具,在墙壁上涂鸦,暴打橡胶假人……更有甚者,还可以支付更多的费用将房间DIY成更贴近现实的场景,比如布置成自己的办公室,将假人套上老板的衣服打一顿泄愤。走出“发泄屋”的那一刻,或许与“发疯仪式”的人们结束“发疯”一样,无论现实中棘手的问题有没有真的得到解决,至少这份钱花出去、力气击打出去,在头脑与体能的全面疲惫里,获得某种如释重负的安歇。
比起真实地面对与解决问题—比如精进专业能力以期在工作中进步,比如好好对待感情以求圆满,比如探访逝去好友的家人获得新的情感联结,“发疯”,真的能让人更容易获得幸福吗?
在《虚无主义》一书中,荷兰哲学家诺伦·格尔茨这样定义“虚无”—一种如今广泛的社会情绪:发现生活无意义,但仍然假装没事地继续活下去;发现现实是非人化的,但仍然选择接受它。这与曾经风靡的“鸡汤”,罗曼·罗兰的那句“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不谋而合,它们指向的生活终点都是“幸福”。
但终点非常遥远,眼下的琐碎与烦恼却近在咫尺。为了安抚自己,人们会沉浸在“奶头乐”与盲从中,比如沉迷短视频、拒绝深度思考、机械打卡上班……
但“发疯”—无论是停留在互联网上的发疯文学,还是线下的“发疯仪式”,虽然看起来荒诞,却无意识地揭发了广泛、寻常的虚无主义—“奶头乐”不会带来真的快乐,忍耐、压抑与机械顺从也缺乏意义,与其隐忍,不如“发疯”。
世界是巨大的草台班子,如若每个角色按照既定的标准老老实实演下去,或许无人发现我们曾经看重的一切是一场荒诞的戏。但如今,“发疯”撕开了一道口子,人们看穿了生命本身的虚无、幸福的难以抵达、工作的无意义……那么不妨将现实全部降级为游戏,允许疯言疯语,允许不伤害他人的尖叫与击打……在人生这场游戏中,发疯是正义,毁灭或许也意味着重生。
特约编辑姜雯 jw@nfcma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