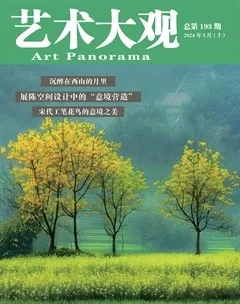肖邦《降A大调圆舞曲》op.42的创作特征和演奏方法







摘 要:肖邦身为浪漫主义时期的卓越艺术家,与西方音乐史上众多作曲家有着显著的区别。他的一生几乎全身心投入钢琴音乐的创作中,在钢琴音乐领域树立了一座不可撼动的丰碑。圆舞曲无疑是肖邦钢琴音乐中最熠熠生辉的明珠之一,无论是其抒情的还是华丽的圆舞曲作品,都深刻烙印着肖邦的个人思想与情感,是他情感世界的真实写照。本文以肖邦的代表作《降A大调圆舞曲》op.42为焦点,从曲式结构的精妙布局、节奏特征的独特魅力以及旋律特征的动人之处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剖析;旨在全面揭示这部作品独特的创作特征,并探讨其演奏方法,进而使我们对肖邦的《降A大调圆舞曲》op.42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更加欣赏的目光。
关键词:肖邦《降A大调圆舞曲》op.42;创作特征;演奏方法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05(2024)13-00-05
一、肖邦及他的圆舞曲
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这位19世纪的波兰钢琴巨匠与杰出作曲家,自幼便沉浸在音乐的熏陶中。受热爱音乐的父母影响,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1830年波兰起义的爆发,迫使他离开故土波兰,前往法国巴黎寻求新的生活。此后,他创作的众多钢琴作品无不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流露出对国家沦亡的深切憎恶以及对故乡的深情怀念。
肖邦被誉为“钢琴诗人”,他的作品几乎只为钢琴创作,包括58首玛祖卡曲、19首波兰舞曲、4首叙事曲、21首夜曲、4首即兴曲、24首前奏曲、17首圆舞曲、2首幻想曲。圆舞曲也叫华尔兹(waltz)是钢琴的一种体裁,源自欧洲16世纪的民俗舞,19世纪后,奥地利的约瑟夫·兰纳和老约翰·施特劳斯一起确立了“维也纳圆舞曲”这种体裁规范,使之成为实用的舞蹈伴奏。肖邦的圆舞曲不同于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他的圆舞曲节奏较为自由,速度变化比较大,钢琴音色非常丰富,所以肖邦的圆舞曲是在音乐会上独立演奏的钢琴作品,而不是作为舞蹈伴奏的圆舞曲[1]。
肖邦在其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共计17首圆舞曲,这些作品按照音乐风格可划分为两大类别:华丽的圆舞曲与抒情的圆舞曲。在华丽的圆舞曲中,《降D大调“小狗”圆舞曲》与《降E大调华丽大圆舞曲》无疑是更具代表性的杰作。这类作品将舞蹈元素加以理想化的艺术创作,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舞蹈画卷,本文即将深入探讨的《降A大调圆舞曲》正是此中翘楚。另外,肖邦的抒情圆舞曲同样引人入胜,如《升c小调圆舞曲》等作品,它们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悠扬的旋律著称。本文将聚焦于《降A大调圆舞曲》的曲式结构与创作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揭示其独特的音乐魅力,并进一步助我们领略肖邦作品中所要传达的深挚情感。通过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我们将更加深入地理解肖邦圆舞曲的精髓,感受其音乐艺术的无穷魅力。
二、肖邦《降A大调圆舞曲》op.42的创作背景与曲式分析
(一)创作背景
肖邦的《降A大调大圆舞曲》op.42诞生于他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1840年。此时,肖邦在圆舞曲的创作上已臻至成熟之境,他对钢琴演奏技巧的发挥愈发重视,展现出卓越的技艺和深刻的理解。正因如此,该作品被许多人誉为肖邦圆舞曲中最杰出的典范。相较于他之前的圆舞曲作品,这首曲目的成熟度更为显著,充满了肖邦特有的音乐风格与个性魅力,堪称其音乐创作中的一颗璀璨明珠[2]。
(二)曲式分析
此曲是一首回旋曲式结构的圆舞曲(见表1)。
前奏(1—8小节):在降A大调高声部主调的悠扬中音颤音烘托之下,左手自第5小节末拍始,引领着一段缓慢而柔和的波浪式旋律缓缓展开。与过往圆舞曲中前奏常有的预示和铺垫功能相异,此曲前奏的音调独具描绘性特质,旨在细腻地勾勒音乐画面,为后续的乐章奠定独特的情感基调。
第一插部B(9—40小节):这段音乐呈现为一个重复双句体的方整乐段。其核心动机I源自第9至10小节,展现出一种级进的波浪式旋律发展。随后,第11至12小节通过动机I的下二度模进进行变化,而第13至14小节则是对动机I的倒影处理,形成了一种对称的旋律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第14小节,音乐中引入了新的元素——四度音程的跳进,这一新颖的音乐语汇随后得到了扩展,表现为五度、六度音程的跳进,为整段音乐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和动态变化。在第25至40小节中,该乐句以高八度的形式对第一插部进行了重复演奏,整段音乐在结束时,和弦收束于主调降A大调的主和弦之上,随后无缝衔接至主部[3]。
主部A(41—56小节):本乐段采用重复双句体的方整结构,整体布局为8+8的形式。此乐段的核心音乐材料为琶音,其表现形式为上行与下行的音阶进行。乐段初始时为一小节的琶音上行,随后再度迂回上升一小节,继而展开为两小节的琶音下行。乐节的长度得以延展,曲调愈发显得炫技且辉煌。主部的首句(即第41至48小节)结束于降A大调的重属导七和弦,第二句收尾时落在属七和弦上构建出一个开放性的段落。紧接着,音乐直接过渡至第二插部,实现了段落间的流畅转换。
第二插部C(57—72 小节):本乐段为复奏的双句式结构,采用8+8的方整形式。在旋律的演进中,以音程的大跳为主导,营造出一种欢快愉悦的氛围。特别是在58、59以及62、63小节中,跳音的运用恰似舞蹈中的跺步,既展现出优雅的风度,又不显呆板;既充满欢快的节奏,又不流于轻佻。本段音乐在结束时,其和弦巧妙地落在了主调降A大调的主和弦上,随后进入主部的第一次再现。
73—88小节为主部的第一次再现。
第三插部D(89—104小节):采用重复性双句体方整型的音乐段落,同样是遵循8+8的方整乐段形式。该乐段在音型上更具特色,89和90小节的平缓节奏与91和92小节的紧凑节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在调性方面,本乐段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的降A大调转至近关系调降E大调,为音乐注入了新的色彩。本乐段的第二乐句(位于97至104小节)作为对第一乐句(即89至96小节)的重复演绎,采用了高八度的演奏方式。在乐句的结尾处,和声的运用稍有变化,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终止,为整段音乐增添了独特的韵味[4]。
105—120小节为主部的第二次再现。
第四插部E(121—164 小节):采用三句体乐段的形式,其结构为16+16+12。在整首乐曲中,第四插部被认为是最具有歌唱性的部分。下行级进的音乐旋律和柔和的音调,都展现了一种充满无奈和悲伤的情感。在不断变化和重复的音乐句子中,三连音的音型和声部的加厚处理,使得这种情感的表达变得更加深沉和厚重。同时也为整个旋律增添了一种强烈而又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从第158小节开始,新的材料的出现把情感推向了顶峰,副属和弦、连续的模进和紧凑的节奏型相互交错,共同构筑了这一令人兴奋的音乐段落。
165—180小节为主部的第三次再现。
第五插部B1(181—212小节):乃是对第一插部B的变化再现。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当进行高八度的重复动作时,结束的位置从原来的主调主和弦变为导七和弦的第二个转位,此举为音乐注入了新的色彩。此外,在旋律声部方面,采用了分裂的手法进行发展,从而构建了一个开放性的乐段,使得整个插部在结构上更富层次感和变化性。
213—228小节代表了主部的第四次呈现,而这一次的呈现则是主部内容的再次变化。明显的差异在于旋律发展主要以模进为核心。第一个乐句(213—220小节)是由两个四小节长度的乐节组合而成的。第二乐句(221—228小节)主要采用222小节作为核心内容,进行连续的下行模进,进一步丰富了音乐的层次感和动态变化[5]。
第六插部D1(229—261小节):作为第三插部D的变化再现。通过运用模进的手法,让主题旋律在不同的调式调性上得以展示,呈现出丰富的音乐色彩和变化。
262—276小节主部迎来了其第五次的变化再现。终止于属七和弦中的第二个转位上,随后直接过渡至尾声部分,使得整部作品在结构上更加紧凑且富有逻辑性。
尾声(277—289小节):继续使用第一插部的音型,但其音域已经扩展到近六个八度。随着力度的逐渐增强和速度的加快,尾声展现出壮观的景象,使得整首曲目更加绚烂夺目、激昂澎湃。
三、肖邦《降A大调圆舞曲》op.42的创作特征
(一)节奏特征
1.交错拍子
在肖邦的圆舞曲创作中,他独具匠心地融入了交错拍子的技巧,使得不同的拍子相互交融,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节奏韵律。
在该曲第一插部B部分中采用了交错拍子的写作手法,右手所演奏的旋律为二拍子,而左手伴奏的音型则是标准的圆舞曲式中的三拍子。这种三拍与二拍的巧妙结合,赋予了旋律独特的双重魅力:一方面,它展现了深沉的抒情之美,仿佛歌声在悠扬回荡;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圆舞曲固有的舞蹈性和节奏感,使人仿佛置身于欢快的舞会中(见谱例1)。
2.赫米奥拉节奏
赫米奥拉节奏作为音乐理论中一项历史悠久的理论,其源头可追溯至古代的乐汇——赫米奥拉比例。在音乐的理论体系中,这一比例展现出多重含义。一方面,使用纯五度的音程,其对应的振动比率是3∶2;另一方面,它也体现在节奏的比例上,同样是3∶2的比例。这一比例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要考虑的是不同声部的纵向节奏比例,如左右手的发音比例是3∶2;其次在横向关系中,节奏的前后比例关系。特别是在保持拍号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音的调整,将“两个三拍子”的小节转化为“三个两拍子”的小节节奏模式[6]。
这种三比二的赫米奥拉节奏在该曲的第一插部B中得到了应用,B部分的高声部的旋律自由流畅,具有鲜明的6/8拍特性,而伴奏部分则以3/4拍子为基调,二者的交织使得旋律部分在伴奏的衬托下愈发凸显,更富表现力。
3.延迟重音
在肖邦圆舞曲的节奏设计中有重音延迟的加入,这一特定的节奏模式是玛祖卡舞曲独oWm6w7iM2P3FvHfW/Q8sAw==有的。肖邦玛祖卡舞曲中的重音位置呈现出多样性,通常设置在长音符、附点节奏或装饰音的位置。这些重音可能出现在小节的第一个节拍上,或者是第二个节拍,甚至是第三个节拍上,展现出丰富的变化性。
在该曲第三插部 D部分中的第95、96、104小节处采用了民族舞曲玛祖卡延迟重音的节奏模式。这种别具一格、独具匠心的“波兰式”圆舞曲节奏,为那些习惯于“蓬嚓嚓”风格的传统华尔兹的维也纳市民带来了全新的体验。此外,肖邦圆舞曲与民间舞曲之间深厚的联系也在这种独特的节奏模式中得到了体现,展现了他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与传承(见谱例2)。
(二)旋律特征
1.运用动机重复的创作特征
在肖邦的圆舞曲创作中,重复动机这一写作技巧被广泛运用,这不仅是技巧的运用,更是他音乐作品内容表达需求的核心体现,彰显出他独树一帜的感性风格。肖邦巧妙地通过旋律与节奏形式的不断重复与变化,展示其音乐的艺术表现力,从而塑造出别具一格的音乐特色。
在该曲的精妙第一插部B部分,肖邦巧妙地运用了重复动机发展的写作手法,其核心动机精心提炼自第9至10小节,犹如一颗情感的种子,在音乐中生根发芽。通过动机的重复与发展,肖邦旨在深刻展示一种难以割舍、无法摆脱的深厚情感,并借此表达情感上的执着与坚持。这种匠心独运的写作策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使其更加细腻动人,而且深入阐述了浪漫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情感至上、个性张扬。通过这种方式,肖邦成功地将个人情感与音乐艺术融为一体,创作出了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不朽杰作(见谱例3)[7]。
2.采用下行音调的创作特征
在肖邦的圆舞曲中,旋律常展现出下行趋势,即便是最小的结构单位,也遵循这一特点。
当乐曲行进至主部的第四次再现,即第221至228小节时,我们可以发现这段音乐主要以222小节的音乐材料为基石。作曲家巧妙地运用连续的下行模进手法,构建出一个循环往复的旋律段落,如同时间的流转,不断向前却又带有无法挽回的哀愁。这段旋律不仅展示了肖邦精湛的作曲技艺,更深刻地传达了他对命运无常、难以捉摸的感慨。每一次下行的旋律都仿佛是对时间流逝的无奈叹息,流露出对逝去时光的无限追忆与无法阻挡的沮丧之情。这样的音乐表达,让人们在欣赏美妙的旋律之余,更能感受到作曲家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见谱例4)。
3.连续音程大跳音型的出现
利用模进的创作方法,构建了一个连续的音程大跳音型,这种独特的音型经常在肖邦圆舞曲的某个尾声部分展现出来,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主部A的创作中,肖邦特意采用了连续音程大跳的音型,这一精心设计的音型不仅悦耳动听,更深刻地揭示了作曲家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与矛盾挣扎。它仿佛是一段心灵解脱与恢复宁静的旅程,映射出肖邦一生中流浪他乡、历经沧桑的艰辛与追求。最终,这种音型也象征着肖邦在去世后找到了他生命的根源与归属,成为他音乐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见谱例5)。
四、肖邦《降A大调圆舞曲》op.42的演奏方法
(一)节奏与重音的把握
该曲运用了赫米奥拉节奏的写作手法,赫米奥拉节奏要求演奏者在演奏时能够明确地区分并表达同一拍内的不同节奏,这如同画家使用双手作画,需要精细的协调与控制。在练习过程中,演奏者应先分别练习两个不同声部的旋律线条,待熟练后再进行双手的合奏练习,以确保能够准确地呈现这种复杂的节奏形态。另外,重音弹奏在该曲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演奏者必须在表演前仔细研读乐谱,同时严格控制强弱拍与重音的位置。此外,为增强练习效果,演奏者还可以采取分手单独练习的方法,以更好地掌握和表现曲目的精髓。
(二)节奏音型中低音远距离跳进
在该曲子的主部A出现低音远距离跳进,要求演奏者在右手弹奏时,应巧妙运用手腕的带动,使旋律表达得流畅且连贯,如同掌握音乐的“呼吸”一般。对于多次重复的旋律部分,演奏者需通过细微的变化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同时,双手间的强弱对比应精心安排,以凸显主旋律的魅力。左手在演奏低音部分时,要确保每个音符都清晰明确,从而使得整体音响的三个层次分明可见,营造出和谐而富有层次感的音乐效果。
(三)旋律的歌唱性
在处理旋律时,我们需要重视其歌唱性。在肖邦的音乐创作中,旋律的呈现或者称之为旋律的歌唱性,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使得其作品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在演奏该曲时,我们首先要单独练习旋律部分,并结合弹奏进行歌唱练习。当左手弹奏和弦的时候,需要保持平静,这样做是为了更有效地突出主题旋律的歌唱特质。同时,细心聆听每一个和声的发展和转变,深入探讨其与旋律之间的联系,使和声和旋律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五、结束语
肖邦的《降A大调圆舞曲》op.42是一首充满华丽与辉煌的圆舞曲,璀璨夺目,气氛热烈而活跃,音乐中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强大的力量。要想更好地演绎这首钢琴曲,我们必须深入领会乐曲中的情感内涵。这意味着我们不只是要对音乐有深入的认识,还需要对其细微之处给予足够的关注。一首优秀的钢琴曲是由许多复杂且具有代表性的元素组成的,其中,旋律与节奏便是最重要也最为基础的两个要素。本文深入探讨这首作品的曲式分析、创作特点和演奏技巧等多个方面,目的是帮助演奏者更全面地理解该作品的核心,从而更好地把握其音乐风格。
参考文献:
[1][波]雷吉娜·斯门江卡.如何演奏肖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2][苏]A·索洛甫磋夫.肖邦的创作[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
[3]刘金玲.肖邦圆舞曲的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5.
[4]袁蓓.肖邦圆舞曲的创作及其演奏研究[D].武汉音乐学院,2007.
[5]袁蓓.肖邦圆舞曲的创作风格分析[J].音乐创作,2012(07):149-151.
[6]吴李真.肖邦圆舞曲的创作及其演奏研究[J].黄河之声,2021(02):126-128.
[7]宋晓丹.肖邦钢琴曲《圆舞曲》演奏分析[J].黄河之声,2021(21):124-127.
作者简介:黄研(2003-),女,河南新密人,本科,从事音乐表演研究;廖彬(1979-),女,重庆人,博士,副教授,从事音乐表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