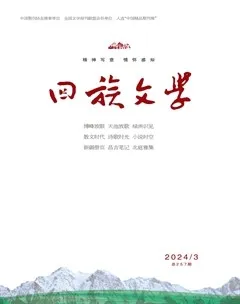戈壁风刀
陈东
我在戈壁无人区遇见了胜利兄弟。
一样的扎根荒原,一样在风中坚守,一样成为风景里的猎猎旌旗。
淡蓝色远山与淡蓝色的天空相融仅剩发丝一线,它们起伏连绵,向东向西,向高向远,打开了整个视野。我瞳孔缩到了最小,焦点落在无限远,那里不再是大平原,不再是皇皇之水,不再是阡陌纵横,也不再是高楼大厦。那里空无一物。
我该拿什么当作参照物?只有风。风是这里的主宰,吹走了繁华、躁动,吹走了车水马龙,吹走了灯红酒绿。眼前,无数石头互相拥挤、依偎,甚至碰撞,构成了蜿蜒向远的缓山。那山与枯水期的黄河的河床一样,袒露着温润的粉红色。那之上,赤红色的连续油管装备如一条跨越远山的长虹,六千米长的连续油管随着注入头的推进,缓缓探入哈拉阿拉特山5井。
我的胜利兄弟在井场,在罐区,在蜿蜒伸展的进井路上,像一颗颗赤红的石头,坦然接受戈壁风刀的雕琢。
1
戈壁滩是千百干涸河床纵横交错的山谷,一本泛黄的苍茫之书。毗邻魔鬼城,镶嵌在哈拉阿拉特山和成吉思汗山之间的山谷营地,在蜿蜒曲折的进井路的连接下,像极了山神胸口的宝石项链。阿拉德油田在这里,它是胜利油田的第七十九个油田。
它孤占无人区,要戈壁的风替代所有语言。
风不停吹,裹挟着哈拉阿拉特山谷的火热,吹我的头发,吹我的脸庞,吹我的脖颈,像吹干戈壁滩百万年的泪水一样,也准备将我整个吹干。在它吹干之前,我要和风一起飞奔,奔向井场,奔向作业兄弟。那时,他们围坐擦拭刚刚从注入头更换下来的摩擦块。我和相机的闯入,让他们错愕。“我也是作业工,同行。”我笑。他们问:“山东人?”“唉,山东人。”
“我老家德州,所以名字叫张德生。”带头的壮汉笑起来,他憨厚的笑容里有着山东汉子的爽朗和豁达。摩擦块擦得锃亮,银白色又照亮红黑色的脸庞。和大平原上的连续油管一样,他们的设备也将由此向下到达六千米的油层。和大平原的作业不同,它是视野里唯一的高物,耸立入云。德生入疆已有两年,孩子刚一岁。在他印象里,故乡是梦里的襁褓,是妻子的床头,是父母温暖的餐桌。到达千里之外的他们,与亲人相聚的唯一方式是在疲惫的深夜里,奖赏自己一个美梦,梦里啥都有。德生说,他跟儿子视频,儿子一笑,他也笑;儿子再笑,他再笑……笑到笑不出来,德生就挂断电话,走出值班房,抬头去望戈壁滩的满天繁星,问问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到只眨眼,不流泪。
因为爱,我嫉妒风沙,它们与三千六百公里外的我的胜利兄弟为伴;我愿成为风沙,那样可以与戈壁滩的胜利兄弟朝夕相伴;可我忌惮的又是风沙,它吹干了我的脸庞,吹干了我的脖颈,痒痛爬满了脖子,一滴泪滴落,都会痛到钻心。
风中的刀叫作荒凉,德生说那是戈壁给的礼物。探寻戈壁之前,关于孤独的问题罗列在采访日志里,在山谷之风吹我的那一刻,被扔进风里,无迹可寻。因为远离人群,因为风,戈壁滩成了诗歌的最后一片自留地,成了孤独无可入侵的真空地带。
来有风的地方!比如山谷,比如我脚下的乌尔禾,充满童话般的奇幻。乌尔禾,蒙古语“套子”的意思。无人区的孤独与顽强相互依存,五彩石、梭梭树、骆驼刺、狐狸……也许风设下的陷阱,只是为了套住河谷。只要河谷不离,风一直吹啊吹,吹到海角,吹到天涯,吹过千秋万古,一切都会回来。
“戈壁的荒凉,像三千六百公里外的故乡。望着它,也望着家。”德生像个诗人,要我好生羡慕。也许德生也会跟着戈壁石头们一起,慢慢玉化。
石头、石油,都是美丽的传说。胜利人为了这个传说,踏入渤海湾的石油地质大观园,在济阳大坳陷为国找油。而眼前山谷中心也是硕大无朋的坳陷。同样的盆地、同样的皮带抽油机、同样的千型井口、同样的白板房聚拢而成的营地,同样开荒拓土的石油精神……一切都是历史的重演。
巡井的脚印一串串,营地起,油井终,一串便是一巡,一巡就是一串。在无人区巡检,没有挂牌摘牌的烦琐考核,脚印证明一切。
开拓的脚步跨越三千六百公里,可传统的延续经久不衰。当年在盐碱地如此,现在在无人区亦如此。越是回归传统,越能找到扎根坚守的根与魂。
我弯腰去问石头,解读戈壁留下的千百年谜语。
远处的、孤立的、无名的粉红山丘是魔鬼城的延续,不久的将来也会被风吞入肚中,咬烂、嚼碎,再吐出来,在天地间留下残骨。那时,它依旧呼啸。
从干涸的河床抠出石头,通透和奇形都不足以令人错愕,意料之外的是,干涸的河床下,内里的土壤却湿润。风吹干的水没有随风离去,而是像钻土的蚯蚓似的,一点点浸入石头,洗净杂质,也润透灵魂。水吹进了石头,石头吸干了水。
风以痛雕琢石头,时间化水入石,就有了“水头”。等水头足了,石头就成了玉,被人带入繁华集市,待价而沽。德生说:“山谷里有无数石头。你和石头,一个在平原,一个在戈壁,互为陌生,本无牵挂,可一旦捡起来,你和石头就有了关系,它是你的石头,你是它的主人。”茫茫人海,缘分总是蓦然偶得,可千里之外与石油重聚,便无法简单“自缘其说”。也许,寻油的使命早渗入他们的血脉。依着传说去寻,再远的路都能找到。
初秋的正午,连续油管的四段钻塞作业刚刚完成,六千米的连续油管留在井内,顺着油管向外喷涌的正是哈拉阿拉特山特产的超稠油。喷涌而出的超稠油借助高温高压流动着。它们拥挤在管道中,不断喷涌。黑色的油流是见不得光的胆小鬼,一旦见了,便硬化如戈壁的石头一样,黝黑坚硬,堵死整条管道。依赖于地层的超高温超高压,它们才得以快速喷涌。“装满,走咯!”收油人大吼,罐车发动,卷着阵阵黄沙驶出戈壁滩。
镜头里的哈拉阿拉特山在变,原本山脉与云的分界次第溶解,我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云。德生说不只是山,路也如此。山谷本没有路,走过了就是一条路。不久之后,石头会淹没它,人们又会打开新路。路的方向,取决于人的脚步。修井的路穿过一个又一个山谷,过了一个又一个山梁。他们走过了那么多山川沟壑,一定见过更多的玉石,捡过更多石头。这放眼望不到边的山谷,比它们更远的,恐怕只有这戈壁的风刀吧。
2
风,耳边嘶吼,渐渐吹干我身体里的水。
石头呢?也许更渴吧!因为戈壁的干渴,河流走了,森林走了……风还是风,山还是山,一直吹,不断垮塌,再成山,再垮塌。时间是这场变迁的唯一见证,可它依旧搞不清究竟是风滞留了河床,还是河床挽留了风,是谁把眼泪化成美丽的五彩石堆满了山谷,又是谁在一颗颗五彩石里浸满了水头。站在石头上,站在云层低矮、生灵萧索的戈壁滩上,我看到它们,竟是万千山峦。
风吹过,无影无形,无常无征,无言无情,空留一条干涸的河床,权作玉的修道场。
风割我的脖颈。我想到的不是五彩石,而是后悔忘了戴脖套。此后,它会留下一层层斑驳红肿,灼烧黑夜里的我。但我并不抱怨。风穿过耳畔,带来的不只是痛,还为孤独骄傲的躯壳洗礼,要我以赤裸之心与戈壁坦诚。那时,它带我进入谷底,寻找风的眼泪。
戈壁的玉以稀为贵。火山石、泥岩、金丝玉、鸡血石……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可大家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块绿色的石头。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被夺去的绿色便是戈壁滩最后的诗意,必须经由石油人唤醒,与深地的石油一同输送出去,描绘祖国的绿水青山。我们弯腰曲背漫山寻找,希望有一块最爱的玉出现。
石头堆积的山谷里,风为我耳语,千万年大河熙攘,千万年枫林火红,千万年草长莺飞,地裂山崩、洪水潮涌、风蚀峦坠。我感觉到河床的颤抖,浪花的虚像在脑海奔腾万里,瞬间爆发又瞬间消失,激荡心灵又不着痕迹。原来风中藏着的,是万物更迭的过去,也是生灵守望的当下和未来,是石油积蓄的宝藏。
德生说他干过卡车司机,干过集市小贩,城市的故事每天发生。初到戈壁,他发现石头里藏着的故事比城市多上千倍万倍。再后来,他明白,经历百万年的石头更纯、更粹。
3
大风吹我,一粒风中的沙触碰我指尖,所到之处皆是纯净。山仍在,只是风磨平了所有棱角;河床仍在,只是风带走了所有温柔。我伫立古老河谷,伸手去抓一朵哈拉阿拉特山的云,在掌心,又在千里之外。像一只紧握万物的巨手,哈拉阿拉特山的蓝色脊背横亘在云与山谷的边际,覆盖谷底。
我幸运地遇见了高中学长李焱。与他谈高中时的文学初心,谈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也谈远离故土的坚守。
李焱时不时捡块石头,在手里搓一搓递给我,告诉我它们好在哪里,有的圆润细腻,有的透亮,有的形态有好寓意,总之各有各的好。好石头跟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
一块石头就是一件心事、一首诗。可大多数人的心事,就像一封从未拆开的信。李焱问我:“每个人都配得上一首诗,你会怎么写?”
行走戈壁,就是走在诗中,是拆开河床上一封封信,打开一扇扇遥远心门。那是出走的河流遗失的许愿墙,那么多愿望和期待。至于坚守戈壁的他们,我想,他们打开的宝藏更丰富。
李焱说人这辈子就像这石头,努力闪亮,为了被人捡走。发现,捡起;扔掉,再捡起……从一片戈壁到另一片戈壁,或者到达更远的地方。它们的出走,取决于采石人的眼光。
“戈壁滩的石头,和人们手里的石头,谁更孤独?”他问的不是石头。我猜。
石头捡了,话说完,不知不觉就离开了谷底。
李焱驻足说:“把话说给戈壁的石头吧,等走出去,什么都忘掉。”
这是他们用诗歌与石头达成的默契。
透过光去看石头,是风的眼泪,每一块都带着新生的血丝或肌肉或脂肪。阳光穿透云层时,哈拉阿拉特山的云像沸滚的水汽团,几近溢出。可哈拉阿拉特山又安静着,披着皑皑白雪,静望万物。
世间万物的情感是无形的丝线结成的网,不惜才散,不真便凉。我和玉石,与戈壁纵然不舍,也不得不离,不得不断。我终究还要回到人群中,终究要等到下一次,与他重逢。
[栏目编辑:付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