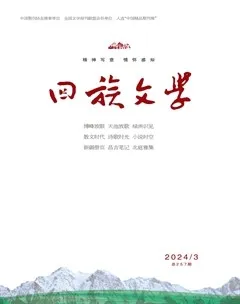大河
师师
吃完一块酥脆的椒盐饼,对老家和外婆的思念,似乎得到安抚。那总是莫名而起的牵挂,似一程无法说明意义的行走,以这种地域性极强的面饼味道传递,并如盘龙河的水起伏、变化,渐行渐远间又不时打几个旋涡来回溯。
1
盘龙河是外婆家门前的一条大河,古名壶水,绕城盘曲潆洄如龙,所以又名盘龙河。外婆家在小西门街,街道沿河。
我的婴幼儿期是外婆带,蹒跚学步时就陪她到河边洗衣服,淘米洗菜,所以跟她亲,跟她家门前的大河也亲。到了上小学,与外婆相隔两地,只有寒暑假才回去小住,但对她的依恋已烙入骨髓。回老家,必会与外婆亲昵,尾巴一样跟着,尾随她逛菜场做饭,堂前洒扫后院浇花,到隔壁易家两兄妹来叫,又立刻转性一般,和小朋友玩在一起。
那个年代的小城游乐场很少,夏天我们最爱做的就是去河里游泳。一个假期天天泡河水中,等收假回家,个个都晒得黢黑。还常去门前河滩上挖沙蟹,堆巨大的沙堡。那时的二舅、小舅很年轻,总与我们在河边玩,领头往水草丛里点炮仗炸河鱼。这种事只要外婆看见,一定站大门前高声骂道:“幺麽,两个大狮子头,你们把我的娃娃让水冲跑嘛,我不扯你们两掴耳。”两个舅舅是充耳不闻的,嬉皮笑脸地绕道后院翻篱笆墙回家。而每天早起,坐在河边米线店,面向河水吃米线就椒盐饼,绝对是旧时光里外婆给予的雷打不动的传统标配。
在河边,总遇到街坊梁大爷家的狸花猫。它喜欢在我脚背上不停迂回,想让我抚摸。有年暑假,几乎没有见下雨,河滩上干爽爽的,我们折下水边的芦苇枝铺地、搭窝棚,过家家。河沙好白,芦苇枝绿得深沉,狸花猫被大家时刻抱在怀里,轮着当过各自的孩子。
赶街天,我最爱坐在大门前看热闹。天亮不久,老屋对面河滩上就支起许多汤锅摊子,摊主们先下河洗涮大铁锅,再架上粗木柴烧火,熬大块的肉、成扇的排骨或大骨头。一会儿工夫,河边就飘过来浓郁的只属于街天的独特肉香味。卖柴草和卖牛羊鸡鸭活口的,在另一侧排成几排,赶集的人越来越多;过完正午,人又越来越少。汤锅摊子倒是从早到晚都热闹,城里的、进城的都会来吃,以男人居多。他们三五成群,就着牛羊肉烂烀,喝着最便宜的当地烧酒,大声聊天,聊得天花乱坠,聊到太兴奋,可以见他们手舞足蹈,唱山歌,直至夜幕降临。摊位上如果坐不下,就有人端着酒碗和肉碗,蹭到老屋的房檐下吃喝,而外婆,很鄙视喝得迷糊的男人,吆喝家里孩子回后院玩,说不允许看这些吃死牛烂马的浑人,但我真的很喜欢听他们天南地北地神聊和高声歌唱。
盘龙河,在我幼年的眼中,有太多有趣的场所,现今消失得无声无息。这些曾经的存在,我放在记忆里和文字间,如记下河水潺潺的声音,小心而隐蔽地保留着,防止丢失。
母亲是外婆最大的孩子,我们兄妹仨也成了外婆最早的孙辈,备受她的疼爱。母亲随军调动,外婆为照顾我们,陪着去到部队大院。好像在我六岁左右,外婆终因不习惯外省的生活环境,返回边地小城。所以,在籍贯上的故乡我待得极少。身为军人的父亲,带着我们辗转一个又一个军队大院。我对故乡的概念,就是父母日常提到的老家;而老家在我心间的意义,等同于外婆。
2
盘龙河一直在,与外婆家木板楼的老屋隔着一条五六米宽的街道。
老屋正对的河岸,有几十级石阶延向河床,这就是街坊邻里口中的水码头,也是小西门街挑水、洗菜、洗衣服的地方,整天人流不息,热热闹闹。印象中,只有深秋至冬日,河水才清澈。春雨一落,河水就开始泛浊,到夏季会夹杂泥沙,成淡黄色。如遇暴雨就成深黄,且河面浩荡、河涛咆哮。每年的年三十,河水明净,夜里零点一过,街坊四邻都向水码头奔跑,使用各种大小不等的装水物件,下到河边打水,年俗叫抢头水。只要能第一个盛起水,狂奔回到家,就预示那家人全年福气满满。
老房子的堂屋门临街,与门平行有一扇巨大的窗,白天打开,便于采光通风,晚上用一块一块木板子,对着上下两头的凹槽竖排插紧。小时候随父母回老家探亲,一个微风缓缓的晚饭后,外婆吸着她小巧的水烟筒,淡淡地告诉我,很多年前,堂屋是作为店铺使用的。一条摆放各种货物的长柜子,就紧紧靠着那扇大窗。家境鼎盛时,帮工请了好几个,负责搬货送货,外婆迈着正宗三寸金莲的小脚,带娃缝衣烧煮洗涮。
某段时日,家里生意突然好得不得了,一个卖柴米油盐、布匹鞋袜、针头线脑的杂货店,那些天里,多少货也不够卖。不多日,卖货赚得了一麻袋又一麻袋的金圆券。外婆的公公掌家,看着锁在房间内猛增的钱,他激动到晚上睡不着,可也就仅仅欢喜了很短的日子,有风声传来,说钱不值钱了。果真,没多时那些钱就被宣布成了废纸,老人家闻讯急得口吐鲜血。外婆说,她公公边吐血边跌跌撞撞去河边清洗,回家时依然满脸血渍,生白布的对襟衫,胸口一片血红。从此,家道中落,辞去所有帮工,自己照顾铺子的事宜。家里太忙时,烧煮用水都是外婆去河里挑。至今,想起这些,我都不知道外婆在当时的情形下,是怎样迈着小脚去挑水,又是怎么走过水码头一级又一级湿滑的石阶的。
外婆言语间的盘龙河,渗透心酸,泛出清幽的哀怨。
外婆从城北嫁到城西,在小西门街的大家庭,颤悠着小脚,操持上上下下的家务。这条河,注视着她生儿育女,注视着她命运多舛。这个经商家庭,接到命令下放边远山寨。就这样,那个小村的牛圈,由几根长木棍象征性分隔后,一半养牛,另一半住人。我的外公就是在这里离开人世的。外婆后来的回忆,充盈着悲伤。
外婆的头发很早就白了。短短几年的下放,她经历了中年丧夫、痛失两女一儿的悲剧。一个缠足的家庭妇女,哪怕再勤劳苦干,仍落得食不果腹、衣衫褴褛。在外婆几近绝命的日子,村中长辈垂怜孤儿寡母,以老家人的厚道仁慈,默许这形容枯瘦的妇孺五人返回。
家中老屋早就被人占了,万幸,偏厦尚存,深夜悄悄回来,还有个勉强容身之所。街坊们谁也没有去告发我们这一家人。外婆也有过轻生的念头,但考虑到还有儿女,又强撑起来。生活艰难贫苦,母亲经常要熬长长的黑夜。已是中年的她,学会了夜深人静时抽水烟。晒干的烟叶切成细丝,在每个夜晚,外婆拈一撮放在水烟筒上,用引火的松明子点燃,深吸一口,吐出长长的白烟,黑夜的昏暗,仿佛能被推开一点。她带着这辛辣的烟草气,支撑自己苦难中的行走。
还好,我母亲勤学而泼辣,从少女时就能帮衬外婆顾家。中学毕业,她报考师范院校,毕业后分配至偏远山区工作。她以手上微薄的薪酬加借款,赎回了被外人几经易手的老屋。自此,外婆才算略松一口气,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再后来,母亲遇到父亲,相爱、出嫁,生活日渐向好,有了我们,外婆随即享了天伦。到三位舅舅成家立业,表妹表弟们陆续出生,外婆搂着一众孙辈,亲亲每一张小脸,真正有了儿孙绕膝的幸福。
小学一年级起,我识了些字,开始喜欢看小人书。有天斜靠在外婆怀里翻书,她注视我手上的《红楼梦》绘本片刻,突然说出诗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惊得书都掉在地上,瞬间被莫名的情愫触动,尽管没有详解,可已感到与母亲教给的童谣不一样的温润。从上中学起,我爱上写作到如今,却总找不到适合的言辞形容我那一刻的状态,似乎是文学之途开了蒙,又似乎在一个美好的梦境里没醒来。后来与母亲聊起外婆背诵《诗经》中的诗句,母亲却说外婆不识字,但娘家是大户人家,应是听过私塾先生给她兄弟们讲课,那句诗就记下了,时过多年睹物伤情,看着我手间的书本所以长叹。我是外婆疼爱最多的孩子,她教会了我文学意境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那就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外婆为我吹过一次六孔箫,她面色平和,箫声舒缓而悠扬,我耳边仿佛那些诗句再次萦绕。外婆女儿身时,抚琴吹箫勤于女红,一直清瘦美丽。我可以猜到她的内心,本是个娇娇柔柔,也曾临水的伊人啊。
时光匆忙,我刚成年的那个4月,一个春寒四溢的清晨,外婆听着河水的流淌声,没有任何征兆地在老屋里骤然而去,走出了时间,过完了平凡而艰辛的一生。她逢遇的人间时光,如河水,兼得了风平浪静、波涛起伏,以及泥沙俱下。
3
盘龙河淘洗过的母亲,生活中有温润有困苦,酸甜苦辣如河水一样盘曲。
母亲曾和我念叨过她的童年,作为家中长孙女,从小衣食无忧。母亲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祖上从湖南永州充军过来。据说起因是家中老少传言康熙某妃子是大脚,不知谁告了密,由此招来祸端,发配云南。后人到边地却也开枝散叶,且都经了商,在当地的生活可谓丰足。母亲一出生就被捧于掌心,待适龄了,早早送去学校,并没有因为是女孩子而受轻视。
外曾祖父每晚要吃隔壁食店的馄饨。母亲稍懂事,就天天被差使去买,所以,能得到外曾祖父的分食。“这在我小时候,真是极大的宠爱了。”母亲只要提及,总是感慨。母亲还记得,家里八仙桌上,常年放着椒盐饼和荞酥,都是十个一叠用纸包好的,给孩子们每天做零嘴,随吃随拿。夏天的月圆夜,外曾祖父会把躺椅搬到大门口,吹着河风,给孙辈们讲故事。那时,月光洒满河面,孩子们围绕在老人身边。话音之间,母亲的眼神清纯,嘴角上扬,仿佛回到了她的童年。我脑子里瞬间呈现出当时的画面:盘龙河宽阔的河面水波微漾,躺椅上摇着蒲扇的外曾祖父啃嚼着每晚独属于他的一扇红糖,愉悦地看着他的孙辈,而一群孩子嬉笑地吃着椒盐饼自顾玩耍着;那一刻,月色洁白,他们身上都笼罩着清淡的银光。
外曾祖父在街坊间口碑极好,人称蒋大善人。他日常爱接济人,隔壁四邻赊账给货的事常有。年关如谁家着实困难不能结账,最后也会一笔勾了,不了了之。母亲刚上学时,家中买过一只大犀牛角,有小孩胳膊粗,自家做药用。慢慢地,外人得了心衰、惊风、上火都来讨要。外曾祖父从不拒绝,即时取下,在糙瓦片上一圈圈地磨,待磨出细粉就包好白送,分文不取。长长的犀牛角经不起众人索要,不久就磨耗殆尽。至于后院种的芦荟、穿心莲、半夏,更是人尽皆知,有人急用时就会自己穿过铺子去刨,外曾祖父还总乐呵呵的。他心态平和,在这条街上活到寿终正寝。
在失去父亲和同胞弟妹的岁月,母亲快速长大,成为外婆最有力的家庭帮手。母亲是全家宠爱中长大的孩子,从小胆大,有责任感,品学兼优,在学校参加了各种课余学习小组,学到了许多理论知识。为保护家人,她学会强势应对外来的责难,必要时,她一定先讲出最高理论,再引经据典去陈述。许多想找碴儿的人渐渐地也不敢再上门挑衅。母亲个子高挑,很能吃苦,日常承担下去郊外砍柴、采野菜野果的琐事,每天像个大人,在外婆外出糊火柴盒或帮人缝补衣服时,她就下河挑水、烧饭,照管我的两个舅舅。
博尔赫斯曾说过:“生活是苦难的,我又划着我的断桨出发了。”最难的日子,母亲和舅舅常躲在大门后,从门板缝隙里看着水码头洗菜的人。只要有人一洗完离开,他们就迅速从家里跑到河堤下,捡起河边的老菜叶和菜帮子,清洗干净带回家,切碎,和着玉米粉或红薯、瓜菜煮,那是全家人主要的食物。年三十晚,家中依旧一锅糠菜,年幼的三舅舅坐在大门口啼哭,吵着要吃糖,外婆侧身在门边抹泪。街坊黄四婆实在看不下去,从家里切下几片两指宽的饵块粑粑,悄悄兜围裙里拿来塞给外婆。这位并不宽裕的邻居,让贫寒的一家人在大年夜每人吃到一口细粮。
多年之后的冬月,大河舒缓,回到小西门街,我再次见母亲给黄老太太送钱送物,母亲的神情像感恩,也像延续外曾祖父的乐善好施。我记事起,外婆就爱煮糖水饵块,家里的年夜饭,母亲必做炒饵块粑粑。这两种口味的食物,原料都是饵块粑粑,对我的意义,却成为吃糖水饵块立刻想起外婆,吃炒饵块就是母亲的味道。
亲历过饥寒,母亲养成了爱惜食物的习惯。我眼里,她这种爱惜有偏执的成分。后来生活好了,她对食物却一如既往地珍视,甚至生出朴素的信仰。任何一口吃食,她从不浪费,且在见到谁有对食物的不珍惜,就会说:“这是衣禄,不能扒洒(浪费)。”
生下儿子后,我对食材保质期尤其关注,很害怕过期食品给宝宝任何伤害,一旦保质期临近总是提前丢弃,为此,没少被母亲大声呵斥。她对我两餐后倒掉的鸡汤不舍,对我丢入垃圾桶的过期虾干不舍,对我丢掉的临期奶粉或别的食物,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舍。她说“:当年要有这么好的东西,你两个娘娘和最小的舅舅不会死。”
母亲是不听劝的,一些隔夜的饭菜,她固执地坚持己见,热了又热,直到吃完。而我能做的,就是瞒着倒掉并谎称已吃。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曾经的生活经历,总会在某个触景生情的场合,让母亲伤感。
母亲老了,发色花白,问她有没有憎恨过人生遭遇的不公,她沉思许久,轻巧地放下一句:“现在回头,觉得所有吃过的苦,锻造了自己的坚韧和宽容。”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母亲此生没有大任,一介平凡的小学教师,任劳任怨地传道授业解惑。桃李就算没有满天下,也分布了祖国各地,这一点,从她不时接到的问候电话,逢年过节学生来探望,足以说明。
平寂的日常,我与母亲安静相处,她的眼里没有忧伤,全是我熟悉的和暖。这种状态,滋润了我的静穆。母亲本本分分工作到退休,赡养外婆,养育我们,带大了她的三个孙子。不知不觉,成为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她满脸慈祥。
4
现在想想,从小至成人,我对盘龙河的记忆,是碎片化的。
隐约记得,有次大河涨水,小西门街被淹,外婆家没有幸免。老屋一楼的前后大门都被打开,河水哗哗地进出。我趴在二楼的楼梯口,看着几乎平了楼板的水面,觉得自己也在流动,似乎马上会一头栽进水里。然后,听到母亲叫我,二楼的窗户外,有军人划了橡皮艇来接。母亲背着弟弟,一只脚跨出窗口,另一只还踏在窗内的木板上,返身向我伸着双手,后来怎么走的,全无记忆。只在以后的梦里,不时会见到母亲叫我时那种焦虑的神情,还有她向我伸出双手的样子。梦里仍记起那天的河面,波涛汹涌。母亲说我当时只有两岁半。
另一次,家里杀大骟鸡,没死,骟鸡嗓子沙哑着惊叫,挣扎着冲向堂屋大门外,刹那间蹦到了水码头的石栏杆上。家里三个舅舅跑出去追,搞不清谁把它捉回来的,反正晚饭吃到了鸡肉。我的小搪瓷碗端着满满的鸡汤,坐在小凳子上,吃了一脸油。外婆一次次掏出手绢,给我擦手擦脸。手绢带着桂花香皂的香气,至今回旋在我的嗅觉里。母亲说那时我三岁,从小记性好得不得了。
再一次,是大舅舅结婚,不知为啥我非要离开婚礼现场,回家后又哭闹得不行,终于把父亲给哭烦了。他常年在部队,与我们聚少离多,刚赶回来参加婚礼,却没想到我这么淘,终于没忍住气,把我揪过来往屁股上狠抽。漆黑的夜晚,我跑到河边哭到快要昏厥,直到外婆那声“妹宝”的呼喊传来,才停止号啕。听说,深夜外婆把父亲一顿臭骂,那时,我三岁半。
之后,记忆就没有了连续。留下的片断,是小时候吃椒盐饼,太酥脆了,总是捧不住,掉地上,外婆和母亲就用碗盛好,让我端碗吃。久而久之,这成为整个大家庭里的奇观,我是从小到大,吃椒盐饼必须用碗的人。
我整个的成长期,只有寒暑期偶尔返回老家。在老屋后院,我们表兄妹围着外婆生起的风炉烤糯苞谷,一起割院子里的草,卖给隔壁马店换钱买零食。当然,更多的就是下河游泳摸鱼虾。至于坐在老屋门口冲着大河发呆,仅是我独有的习惯。当我人到中年,回望过去,猛然觉得,自己也过着流水般的人生。很多过于常态的时刻被遗忘了,留下来的人或事,有欢喜有悲伤,其间的疼痛,随着时间流逝才得到治愈。
八岁那年暑假回去,小舅舅很高兴,专门安排我们兄妹仨去看电影,座位在二楼一排。当时旁边别的孩子打闹,冲楼下吐了口水就跑。楼下人上来向我们狂吼,声称他是城里的大人物。当晚,不管我们如何申辩,那人一直叫嚷着要把我们关起来。人生第一次遭遇冤屈,又没有大人陪同,身体里涌出漫天的无奈、无助,我和小弟吓得大哭,哥哥与那人争论着,勇敢地挡在我们前面。闹得不可开交时,同排座的一位上厕所返回的观影人证明是别的孩子所为。父母和舅舅们听街坊告知也赶到,母亲坚决认定她对我们的家教不可能有这种行为发生。对方理亏,亦迫于我父亲的军官身份,草草道过歉溜走了。回家路过河边,我突然大吐不止,半夜发起高烧,外婆说是受了惊吓。这件事,对我幼小心灵造成极大伤害,那个假期,我的玩耍区域仅限于老屋到河边,哪怕去二十米开外的食店吃米线,如果没有大人在,绝不迈步。只有大河能让我宁静和安心,河水的流淌,岸边皮哨子果树在风中摇摆的枝叶,这些自然的生成,让我能弥漫一些孩子的欢愉,忘记曾经遭遇的不堪。
年少寡言的我,不会向任何人提及那种胆怯,但深深的记忆,造成我长期社恐。长大了,凡遇大事或突发状况,我必然立刻呈现那个夜晚的状态:后脖颈发凉,浑身发抖。很长时间里,我对老家是又爱又怕的。儿子降生,我倾注全身心去爱他,孩子从婴儿到高中,在能力达到的范围,我尽量陪在他身边。用母亲的话描述:“你对孩子使出了我作为母亲也想象不到的心力。”谁也猜不到,我是多么害怕我童年经历过的那种冤屈在未知的时刻被我的孩子碰到。我怕那种没有依靠的无力慌张,以及那一刻曾闪现过的以死明志的一丝念头。
读过米沃什的集子《面对大河:米沃什诗集Ⅳ》,很喜欢里面的句子:“松树受过伤,却在不可遏制地生长。”外婆、母亲和我,祖孙三代,在生命历程中,或多或少都如松树受过伤,但是,我们也如松树般顽强地生长。
老家,属于离开了老家的人。不在一起生活,外婆就时常给我家邮寄椒盐饼和油辣子,这成为与老家最直接的联系,刻在我心底的一个角落,滋生长久的牵挂。外婆走了,整个老宅子的占地一分为四,母亲和三个舅舅盖起各家的小院子。钢筋混凝土的两层小楼,窗明几净,再也听不到老屋里上楼梯时木板发出的咯吱声。第一次到新家,莫名生起大大的陌生,所有的崭新似乎与我无关,没有哪个角落存有我的幼年痕迹,更没有旧时光的斑驳。我眼里的星辰消失了,流落在大河上。在后来不时回去的时日里,我常常茫然无措。不久城区河道治理,河水分流,小西门街从此告别了水患的发生,那个有老旧气味的木楼,那个屋外总在夏天发大水的雨季,真的与外婆一起,永远离开了她的河流。
盘龙河的水码头,记录着这条河与我家的岁月,而我一直找寻的思念,却是从小就拥有的大河记忆,只是这隐匿的过往,暗自在心间茂密。
因为工作性质,每年需要去检查小城的许多单位。忙碌之余,我仍然会抽出片刻,到老家的河边走走。风中,我闻得到河面升腾的水汽。那里头仍有原来熟悉的感觉,带着水草与沿岸不同季节的人间烟火味。想起外婆,我有时仍不能控制眼泪,心脏如遇针刺,追念的痛感漫过全身。我希望,外婆看得见我在生活中的奔突,我还算诸事顺遂的人生,大多时都明朗、灿烂。我在外谈起老家,必然不自觉就提到椒盐饼。我极其努力地夸耀它的美味,如酥脆、鲜香。对外婆和老家的怀想,不知不觉,浸入了我安静的生命行程中。
[栏目编辑:马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