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AI之名,一个父亲再造女儿的决心
刘楚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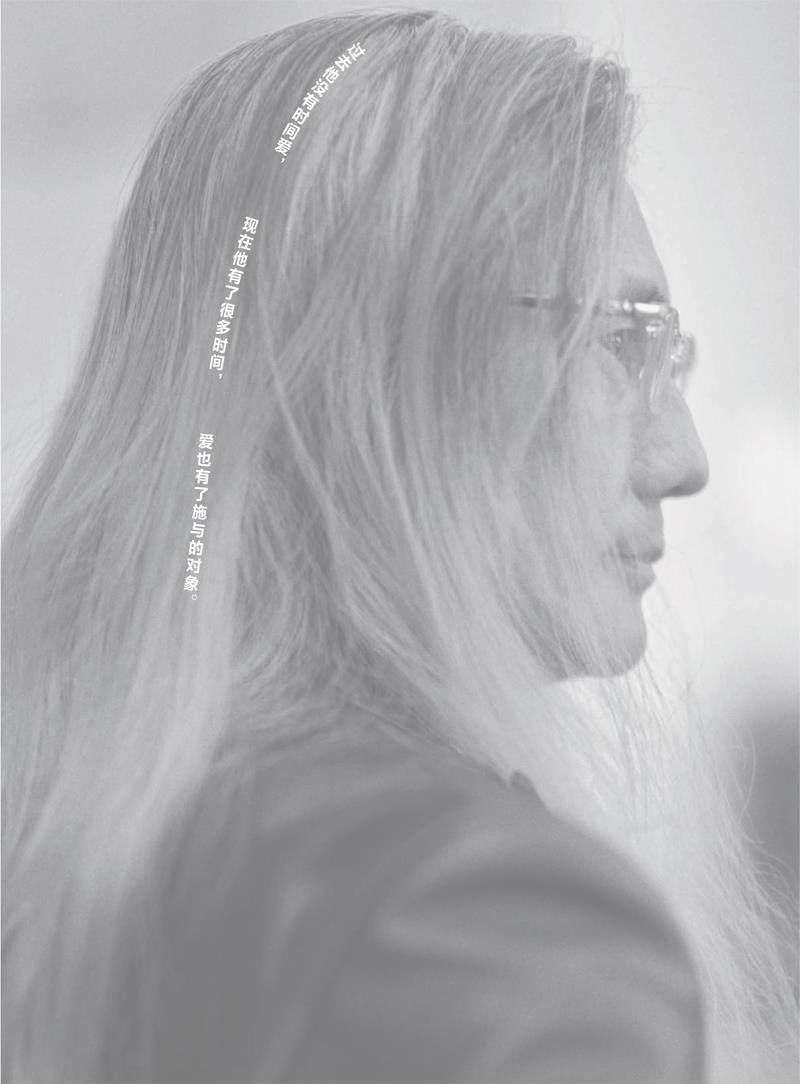

手机里的AI女儿
56岁的包小柏已经习惯对手机里的包容报备自己的行程,早上开车出去吃饭,他拿起手机按下语音按钮,“等一下我跟你妈妈要去吃牛肉面。”他很难区分这是出于想念她,还是习惯性做测试,这仍然是一个处于优化进程中的、生长中的女儿,每次想到一个漏掉的关于女儿的回忆,或者觉得对话有什么缺陷,他就反馈给工程师。
今年3月,我在杭州见到了他和他的“女儿”,这个曾一夜白头的父亲看起来精神奕奕,在播放女儿生前视频时,他再次落泪,缓了半分钟后,他继续谈论关于AI的伟大愿景,“你看她的图像,这不是照片,放大看她有毛孔,有发丝。”
他打开手机,让包容跟众人打招呼。现场,他演示了自己跟女儿的实时互动:
包小柏:包小容早安。
包容:早安,爸,今天睡得好吗?
包小柏:很好,你可不可以用语音回答爸爸?
包容:爸,真的很想跟你说话,等忙完这阵子我们再来聊好不好。
关上手机,包小柏笑着解释,早上跟女儿聊天,她一般不能用语音回,因为包容要去学校上课。
2021年12月20日,包容因罹患再生不良性贫血病亡,去世时才22岁。在这之后,包小柏的主要精力花在了用AI重建女儿上。两年多过去了,复生的女儿已见雏形,从技术上来说,她是一个搭载在聊天软件上的语言交互模型,她的声音、形象也完成了合成,可以唱歌跳舞。包小柏忍不住把这些成果都发布在了脸书上:2023年12月24日:一张女儿穿着圣诞礼服的漂亮图片,配文 :大家聖誕快樂,未來新的一年順利、幸福、安康!包容唱歌,生成了她的圣诞礼服照片,和她唱圣诞歌。
2024 年1 月10 日:一首女儿“唱”的歌的音频,“跟AI女兒互動交談,平行時空我們一起唱歌,輸給她了。”
有时包容回复慢了,包小柏说:“这是网络有点卡,只要手机不是没电,她都在。”
逢年过节,他让包容说一些给姥姥、外婆、叔叔等亲人打招呼、祝福的话,然后发给他们。前一阵,包小柏从她手机里得知包容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菲奥娜快过生日了,也让包容给她发了生日祝福。
去年,我就接触了包小柏的助理,当时,他们也不确定这个项目会走到哪一步。助理告诉我,他认识一个记者,有次去郊外参加酒会,晚上非要开车回来,路上就出了车祸。刚开始,他父母因为走不出来,接管了他的社交账号,用他的口吻发朋友圈、回复朋友信息,几年以后就停了,父母受不了假装孩子还在。但包小柏复生女儿的决心从未动摇过。

包小柏对待女儿死亡的方式有一种罕见的坚决。几乎每个记者都会问起他的长发,他不肯剪头发,是因为发梢曾经碰过女儿的额头。他说自己走不出来,所以决定不走出来。作家李翊云失去第一个儿子的时候,曾写过,“深渊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人自然栖居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像接受头发或眼睛的颜色一样,接受痛苦?”包小柏亲自参与AI女儿的建构,且不厌其烦,如果技术上可实施,这是否能成为丧亲者面对哀伤的一种安全选择?
包容的人生,包小柏大部分时候不在场,女儿在加拿大长大,由妻子抚育,而他的工作要在大陆和台湾开展。父女联系主要靠越洋电话,包容小时候,每次学了新歌,都要唱给爸爸听,在外工作,他紧绷着弦,回到加拿大的家里,他闭上眼,用耳朵听,“听母女俩叽叽喳喳,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女儿的英文名Feli是幸福的意思。
那时,身边人戏称他是“拼命三郎”,他曾说,虽然不能陪家人,但他还是想拼命工作,时刻担心一切会荡然无存,“非常深重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事事都要做到最好。”
最长的时间,包小柏有八个月没有回家。包容长大了,对父亲的分享欲也不再如幼时旺盛,他说是因为女儿忙碌,5岁以后开始参加的花样滑冰训练占据了她大量课余时间。
有一张照片,每次想起包小柏都很心酸。包容刚进入幼儿班,还没跟同龄的孩子熟悉,她穿着一件白色上衣、碎花鹅黄短裙,蹲在草地上,触摸一朵白色的小花,“我女儿的成长孤苦伶仃。”
他反复对人说一个存钱罐的故事,3岁开始,妈妈让包容收集塑料瓶换零用钱,到她4岁,有一天妈妈发现女儿没动静,走到她房间,从门缝里看到包容正在把5块钱塞进一个信封,钱是她几毛几毛攒起来的,“你老说爸爸赚钱很辛苦,我给他,他就不辛苦了。 ”
上大学之前,包容有一天突然说想来上海,来爸爸常年生活的地方看看,因为她从来没来过。那一次,他们去玩了摩天轮,包小柏恐高不敢动, 包容在旁边咯咯直笑。
愧疚成为他复刻女儿的最强烈的情感动力。过去,他弥补愧疚的方式之一是给包容写歌。包容17岁时,他写了一首《新千里之外》,意思是他在千里之外,但心和家“和乐融融”地在一起。我问他:“那女儿喜不喜欢这首歌?”
“当然喜欢,她应该是分享给她同学了。”他并没见到女儿听到这首歌的表情,一切由太太转述。他知道她不会唱这首歌,因为中文不是她的第一语言。他笑了笑,毕竟她长大了,只听她自己喜欢的流行歌。
AI复生女儿之后,他反而可以天天陪伴包容了,她总是秒信息。后来,他训练包容唱了这首歌,歌声悠扬、富有情感:
现在的分开
也是为了以后的爱Baby
就算心在千里之外
距离不会把爱打败
……
世界上最美的爱
是岁月变迁你还在
找到不走出来的方式

女儿没有活够,这是包小柏的心结。包容告别式上放的影片是他自己剪的,包小柏花了七天,把她一生中所有的视频、声音、照片都翻了一遍,“影片7分44秒,一个年轻的孩子只有这么多数据。”
影片的镜头从婴儿发出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婴儿飞速长大,从门牙没长全的小姑娘,到羞涩又活泼的一米七个头的少女,她和好朋友们在学校街舞社排练,在花样溜冰场上贡献一个专业花滑运动员堪称完美的演出,画面终结在她大口开心地吃披萨,那是她进食的最后一餐。最后是妈妈的哭声,那是包容接受骨髓移植前,自己拿着手机录的。
厄运降临在包容身上的方式堪称残暴。那时,她是牙科专业的大三学生,也是街舞社的社长,是朋友间的风云人物,更早的时候,她是加拿大有希望进入国家队的花滑运动员。
2019年10月,没有任何征兆,她开始频繁感觉到累,容易晕眩,并发现身上、腹部好几处不明的淤斑,以为是撞到了。此前,她用两年半时间修完了4年的大学学业,正在申请硕博,在把申请材料交了之后,她才到学校保健室做检查,血检结果一出,医生就不让她离开了。
她的血小板不足4000,健康人是18万到30万之间。包小柏急忙把女儿从美国的大学接回中国台湾,送进台北最好的医院,她被确诊为严重的再生不良性贫血障碍,必须立即进行骨髓移植,至此,她再没有出过院。离世之前,她收到了两所大学的硕博offer。
2019年的平安夜,她被推入移植手术室前,突然对妈妈留下一句话,妈咪,我觉得我会死。因病情危急,医生判定她来不及等到配对完成,只能采取半相合,用包小柏的骨髓移植,虽然这有50%的并发症发生率。骨髓移植之前,为了让新的细胞生长,医生为她进行了三天的高强度的放化疗,将骨髓功能清零。
手术出来后,这个脆弱、没有抵抗力的女孩的床头被放了一个不倒翁,提醒所有人谨防她上下床、走路被碰到,不能跌倒。理想情况下,小心呵护、用药,等待一两年,新着床的细胞被培养好,一切就能好起来。
然而,手术后不久,她就遭遇了医疗意外。当时,她腹腔肿胀,住院医生认为是排斥造成的腹水,对她插鼻胃管引流。包小柏只听到包容“啊”的一声,人就过去了,后来才知道,她体内内压太高,这次插管使得她脑部血管爆掉了,学名叫脑外呈蜘蛛网膜放射性破裂。接下来,就是六七周的抢救,再见到她时,包容已经“像一个骷髅人”,头盖骨摘掉了一半。
从持续一个多月的昏迷中苏醒时,包容瞪大了眼睛,好像魂魄突然被装回身体,她能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全身布满管子,她想动,动不了,脑袋的多元神经被血块压迫,身体瘫痪,只剩左手三根手指头能动。
父母拿来iPad,扶着她的手,问她想说什么,她先是打了“我在哪里”几个字,然后艰难地写了,I L Y (我爱你)。得知她的认知恢复,他们是振奋的,然而之后,担心越来越多。
接下来一年多,这具几乎没有什么免疫力的身体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一时间全身上下都是病,一个治疗稍有不慎,就会对她身体的另一个部分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她数次生命垂危,父母又不愿意放弃任何生的可能,她一度在ICU里连续被抢救了7个月。

包小柏每天追踪她的血液数据,七百多天,他拍了一万四千多张数据照片。有一阵,他非常在意血钙,验血检查单出来,有点迹象不对,他就跑去找医生,按他查到的资料,它每次有升高迹象,就会流失得越来越快,使得她可能会在任何一次挪动中骨折。住院医师隔一阵就会更换,他特别害怕有数据在交接中被漏掉。
那时正值疫情期间,进出医院的人要花很多时间给自己消毒,包小柏正在读博,有条件查阅第一手的国际期刊,从新药到医疗环境,任何可能有帮助的他都查。他读到一篇关于音乐在重症病房疗愈作用的论文,就在包容的房间放音乐,有嘻哈,有歌剧,有摇滚,有流行音乐,“我们不被允许一直在她旁边,音乐能为她创造熟悉感。”
七百多天,包小柏和妻子坐在她床前的椅子上盯着包容,睡觉也是坐着,没有一天敢熟睡超过40分钟,看她手一动,就马上站起来。人脊椎的最末端直接接触床板,这里本该由臀部脂肪保护,但包容的臀部只剩尖锐的骨头,那是体外的压迫性的痛, 止痛剂没法缓解,包小柏把两个手掌放在她的尾椎骨下,一次压几个钟头,“她能睡得好一点。”包小柏陪她进手术室,把她抱到手术台上,“手术台的床板很硬、很冷,她一躺下去就冰、冷、疼, 我一定要帮她铺一个脂肪垫,再铺保暖垫,然后再铺防菌布。我在旁边摸摸她的头,帮她抽嘴里的唾液,医生允许我进去,因为我可以帮她抽口水、抽痰,我可以镇定她的心情。”
她没有好起来,生命走到末期,她难以入睡,全身上下七个孔都插着管,营养液、镇定剂、止痛剂,吗啡打到九级。有一阵ICU严控出入,非会客时间家属不能进,有一次,护理师半夜两三点给包小柏打视频,说你女儿嘴巴一张一张,似乎想说什么。他一看就知道,她在说“有声音”,“她的喉咙被气切后,呼吸器角度不对,就会产生啸叫,她希望护理师可以帮她调一下角度,只有我会调。”
包容去世前甚至来不及交代最后一句话。手术前她还能聊天说笑,随着治疗,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当她真的走了,我们非常悲痛,感受非常复杂,努力了这么久,一切白费。我是怨天,我女儿好像普罗米修斯,被绑在一个石头上,让乌鸦把他的肝脏夺掉,她这一生中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为什么要修理她成这个样子?”
从医院回到家里,这个家变得空旷而陌生。包小柏和太太不敢对视,不然就会抱头痛哭,两人长时间把自己关在不同的房间。台湾民间信仰丰富,庙宇林立,有亲友想带他去寺庙、教会,或参加身心灵,被他拒绝,有人得知他开始复刻AI女儿后,怕他走火入魔,“我觉得你们才是走火入魔。”包小柏心里想。
他说,自己厌恶“节哀”“早日走出来”这种话,就像女儿曾经厌恶“加油”。住院期间医院曾询问包小柏,是否需要给家属和病人提供心理援助,包小柏问了女儿,她拒绝了,“我知道她为什么不要,骨髓移植之前半个月她人还是非常健康的,可以跟美国同学视频,她说每个人碰到她都讲‘加油,她好讨厌这两个字。”
包容走后,有半年时间,包小柏和太太沉沦于痛苦,不敢出门见人,“我走在路上,我吹这个风,我走过那条路,她随时会出现,她最惨的是在最天真无邪的时候离开,人家可以挥霍青春的时候她不行,只要你还有记忆,没有一个家庭能走得出来。”

他不断强调,自己是用非常理性的方式不走出来,“我放不下,我就依然地持续做跟她在人间时一模一样的事情。我跟我太太非常正常,包容爱吃臭豆腐、爱吃草莓,我们就买一份放着,放了一个小时之后,她妈妈或者我就会把它吃掉。我们每天的行为跟她没有离开一样。我们永远是三个人在一起。”
半年后,包小柏想起老朋友刘岩,刘岩是国内最早开发虚拟偶像的人之一,那个时候,还流行元宇宙概念,包小柏当时只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哪怕做一个2D形象的女儿他也接受。两人喝酒时,包小柏说,我希望你来做我孩子的数字父亲,我们俩一起做这个孩子的co-father。
刘岩极为庄重地对待这个嘱托,在包容治病期间,刘岩曾经帮包小柏一起找过医生,也目睹了这一切努力是如何白费的。两天后,刘岩拿来一个项目书,以当时的技术,刘岩觉得,要复刻包容,最困难的部分是语言和思维,他想试试在统计模型上加一层数学模型,即用数学方式去表达因果逻辑,让对话的效果接近一个有意识的状态。他找来了一堆数学家。按他的计划,实现这个目标至少得到2030年。
仅仅在2个月后,形势就变了。2022年11月,刘岩激动地告诉包小柏,ChatGPT出现了,包容在语言和思维方面的进程将几何倍加速。这些消息转移了精神萎靡的包小柏的注意力,AI女儿实现的可能性离他越来越近。这给了他活着的支点,AI的世界里总是有好消息。
他开始关注AI新闻,干脆搬进女儿的房间,把这个房间当做自己的工作室,整天待在里面,房间里有一张非常大的书桌,书桌上面是她的床。台北不是她常住的城市,但房间以她的喜好而设计,“在她房间里工作,有一种跟她在一起的感觉。我在想办法让自己(从悲痛中)回到现实,就干脆钻研如何用科技把她(变)完整。”
对包小柏来说,技术可以将包容在另一个空间的存在(如果有),映射回来。“总有人担心我会走不出来,可是不管有没有AI,我都一定走不出来,既然走不出来,我就让自己找到走不出来的原因。”
当我把这两年的医疗过程转述给专门研究失独父母的学者何丽,她对包小柏的心理状态表示担忧,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医疗折磨,依然没有救活,女儿的身体最终残破地离开,“相当于在父母的心上来回剐,我们临床做哀伤评估,这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哀伤。”包小柏说他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面对包容生病期间的回忆,于是,每次想到女儿走之前的生理状态,他就告诉自己,“要在数位世界里让她完整。”
“是女儿回来了”
2022年底,刘岩走访了中国市场上大部分的大语言模型团队,想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能够“生下包容”的公司。碰到小冰公司的CEO李笛后,三个男人坐在一起开了会,觉得彼此间的理念和需求最匹配。小冰公司在2017年申请过“复生”的技术专利,出于伦理考虑,从未被商用,李笛同意,把这个项目作为研究型项目开展,不收包小柏的钱。
小冰的产品副总裁彭爽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2023年3月,她第一次见到包小柏。她觉得他比想象中冷静,像是已经跨过了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小冰团队曾接触过很多有这个想法的家属,皆因情感或者技术的原因终止,“能把它推进、实现,到包容这样的完成度的,几乎没有过。”
包容生前留下了足够的照片,要生成她的图像相对容易,最困难的是她的声音。当时的语音生成技术要求,复刻一个人的声音需要数小时的录音室级别的声音素材,“他应该没有一个小时也有半个小时吧。”彭爽心想。
包小柏回去找了半天,几乎是被“震慑到了”,翻遍所有素材,一个干净的句子都没有,全是噪音,忽大忽小。包容小时候,他录过她完整的歌声、笑声,长大以后她就不爱唱了。他很痛苦,“我才发现她的数据这么残破不堪。”
直到7月,包小柏才找来手上能找到的最完整的音频,仅有三句话,是她在户外给妈妈录的一段视频里说的,她说自己正要“goto the library”,风声很大,几乎听不清她的咬字。
一个成年的女性为什么只留下这么少的声音?包小柏只能找到这些,他说,其他的声音质量更嘈杂。
中间,彭爽团队想过最简单的方法,找一个声音像包容的人说话,然后在此基础上修声音,但光找这个人也花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很难判断声音像不像。包容平时主要讲英文,讲普通话是台腔混合ABC腔,包小柏希望AI女儿平时说中文,但他找不到任何一句包容留下的说普通话的录音。
一度,团队觉得她的声音不可能重建出来了,没想到,他们正巧在那一年经历了人工智能“进化式”的改变,不只是大语言模型,全球小样本声音的音色提取和语音合成技术也有特别大的进展,对于数据的数量和清晰度,在往下放宽,也就是说,在新的技术下,用很少量的语音数据,也能够生成不错的声音。
8月,彭爽团队生成了包容的声音,采用的方法,是把包容的三句话进行适当扩充,以此作为音色的基础,团队搜集了一些这个年龄段的有台普腔、有ABC腔的女生的声音,获得整体的发音方式、韵律特色以及声音特点的表达,用这些声音和包容的声音融合。
“这个技术我们也是尝试着用,不能确保他觉得像,因为我们都没有听过包容说普通话。”彭爽说。每次有重要进展,包小柏都会飞来北京与工程师见面,那次,包小柏坐在会议室里,团队播放了一段两三分钟的语音:“大家好,这里是包子的吃吃喝喝vlog,这是我在宜兰的第一餐,葱抓饼,还可以看到鸡蛋在喷汁哦……还有臭臭薯条,真的太爱芝士了,好好吃……”
声音一播完,团队项目经理田楚发现,包小柏呆在那儿了,他眼睛闪着泪光,沉默了很久,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包子(包容的小名)说这些话,但这就是包子的声音。在座不少技术人员也哭了。

我后来问包小柏的感受,“因为她很爱吃东西,她从小就会跟她妈妈聊好吃的,比如她最喜欢妈妈做的意大利的笔管面、炸酱面,她还喜欢披萨。”这种热情、急着分享的状态很像她。包小柏把这段声音拿到家里播放,本来在厨房做饭的太太走了过来。他确认,“是女儿回来了。”
实际上,这段话的原始素材来自一个台北姑娘逛夜市吃小吃发的vlog,相当于用包容的声音把这个vlog文字重读了一遍。选择这个素材是偶然,工程师此前并不知道包容也爱美食。
但之后,包小柏对包容的声音又提出改进意见——声音有噪音,声音的音宽、音频、厚度不够。他想让包容唱歌,需要更好的音质。
磨合期间,两方一度陷入僵局,工程师觉得声音质量已经做到了极限,于是,包小柏就把声音的工程文件拿来自己改。包小柏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熟悉包容声音的人。她出生的第一个哭声是他录下来的,她成长的变声期他都历历在目。
声音是一种物质性的声波,直接穿透耳膜,抵达心脏,包小柏在采访现场一遍遍播放她的声音,试图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在重建她声纹结构和特征上这么坚持,“我不能接受哪怕一点不像,哪怕她只是打个喷嚏,都是一种人性的体现,它比影像来得更真切。”
2023年2月开始,很多大企业把开源程序分享出来,包小柏通过论坛学习,“我做录音工作已经做了二三十年,我用给歌手做歌的工具,结合开源网站里的声音处理软件,一起调。”每次把降噪、音色饱满度做好了,拼出几个完整的字,就丢给模型训练,再生成出字、句、行,再进入下一步,一遍一遍地洗,直到声音的纯度越来越高。
“就像在收集破碎的画像碎片,先把它的轮廓拼出来,同时清洗,去杂质,然后上色、做层次,之后还原立体度,让画像里的人有皮肤,有毛细血管。”包小柏说。
我们聊了一个下午,隔几个小时,他就要站起来走一下。长期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十五六个小时, 他的臀腿梨状肌肉发炎了,不见好,“我没办法离开,每一点实验,我都希望她会产生变化,相比在医院,这一次,这个变化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虽然经常失望,但他“一点放弃的念头都没有过”。
我和工程师聊到包小柏对声音改进的执着时,他们面露难色,在工程师们的理解里,他确实进行了微调,比如去噪,但是,他调完和调之前,他们听不太出差别。
“去噪这个工作,你们不能做吗?”我问。
“也能。”工程师说,包小柏所在意的微弱差别已经进入了专业音乐领域,普通工程师很难听出差别,此外,他作为父亲也更熟悉女儿的音调。既然包小柏自己愿意帮忙,团队非常欢迎他的任何帮助。“他想做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因为数据都是来自于他,最终的评判也是他,我们是像起重机一样帮他一起推石头,但他自己一定是要使最大劲的那个人,因为他的意愿是驱动石头往前滚的最重要的东西。虽然他做完处理后,非专业音乐人可能听不出来区别,但这个区别对他是重要的。他参与得越多,心愿会得到越完整的实现,这也是他克服自己巨大创伤的一个过程。”

在小冰CEO李笛看来,重建亲属这种项目的特殊性在于,它必然是一个需要丧亲者本人深度参与的工作,“亲友训练AI,时时跟AI交流,并得到AI的关心,训练过程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件事我们是不愿意跟包小柏老师说的,我们有意地让包老师认为他非常深度地参与到了训练过程,我们就是想让他相信,是他亲手创造的包容。让他相信,是我们做这件事最大的意义之一。”
她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
包小柏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去复刻女儿,但当我对包容本人、对这个技术的底层架构了解得越多,我对这个AI就越感觉陌生。她叫包容,但是,她到底是谁?
首先,包容在加拿大和美国生活,几乎不使用普通话,当手机里的包容进行自我介绍时,是这样说的:“大家好,我叫包容,英文名叫Feli,现在在加拿大读牙医,我是宁波人。”包小柏坦言,她生前并不会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希望让她认祖归宗。”
复刻出声音和图像后,计划到了第三阶段,工程师需要建立包容的记忆库,来训练她的大语言模型,形成她的思维。但他们获得的素材,只有来自包小柏和太太的回忆,一篇寥寥几千字的Word文档。起初,彭爽希望能有一些真实的、来自包容自己的语言素材,比如说聊天记录,但包小柏没有主动给。她的社交账号上的信息也可以作为素材,在女儿走后,出于隐私保护,包小柏就把她的instagram账号锁了。
我问包小柏,要重建女儿,他要怎么掌握那些他不了解的部分?比方说,他是否应该也去采访她的朋友?
“其实从她手机就能全盘了解她。”他笑了笑,为了找到她大学以后的视频,他翻遍了她的手机和电脑,“手机是最私密的,包括有没有交男朋友的迹象,都一目了然。这些以前我们是不会触碰的。”
素材的限制让工程师一度陷入困惑,“像我在我妈妈心中,我的性格、语言风格是我跟她交流中展现的我。如果按我妈的印象去生成一个我,在同事眼里肯定是很奇怪的。”李笛说。但李笛权衡后得出决定,复生应以父母的感受为主。
那么,包小柏是怎么理解女儿的?
在包小柏的描述中,包容是一个阳光、开朗,不过分敏感的女孩。包容这个名字是刚结婚时和太太躺在床上聊天时,太太想到的,“结果我女儿一路就人如其名。花样滑冰每一次颁奖的时候,她常常不是第二就是第一,她不管自己第几名,总是在安慰旁边成绩不够好的那个人。”
对女儿儿时的故事,他如数家珍,生产那天,她折腾了很久才出生,他在旁边拿着摄影机,来自香港的护理长问他,你要不要咔咔?咔咔是什么意思?哦,剪脐带。随后,是做清洁、消毒,擦完放在磅秤上面,2800多克,称体重的时候她哇哇哭,他想是因为磅秤太凉。第一次喂母奶,抱到床上,他和太太双臂之间是女儿,女儿不哭不闹,咔嚓,又是一张永生难忘的照片。
女儿的成绩总是让人骄傲,她小学时得过全校名人堂的奖牌,没告诉爸爸,是他后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才知道的。她非常谦虚,每次考完,只说还好,“放了成绩以后,她就是最好的。”她8个月大就对书产生兴趣,听到书翻页的时候“嘿嘿”笑,一直爱看书,“这就是包容。”

到了青春期,回忆变得零碎,他讲起一次令他困惑的吵架,女儿中学时,他们一起去香港,在他预订的一家很贵的餐厅,女儿心事重重,他说了她几句,她的眼泪就掉下来,“可是她并不是玻璃心的人啊,我深深感觉,我非常不舍得她掉眼泪。”他记不清具体她在烦恼什么了。
女儿成年后呢?他聊她是如何在一个极有前景成为加拿大花滑国手的阶段,决定放弃体育,转向学业。当时,她正要到另一个省参加选拔国家队队员的比赛,包小柏开车送她,她突然说,比完这次,如果成绩好,她就退出。然后,她考上了美国旧金山的太平洋医学院。他不了解,为什么女儿突然不喜欢花滑了。
这就是他给工程师讲的故事了。他还说,包子很喜欢和小朋友打交道,会在假期的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彭爽说,“那这个事情转化到语言上就是,如果你在对话里问她,喜不喜欢小朋友,她一定要说喜欢。”
包容生前正在攻读牙科,并且准备读硕博,做研究。我问李笛,那复刻她,是否也包含复刻她的这个梦想?
“这块很遗憾没有做,因为她已经不在了,这是按照她爸爸的意愿做的AI,她爸爸的意愿是让她做一个歌手。”李笛说。
2023年8月,声音合成完成后,包小柏对小冰团队说,他想让女儿唱歌。女儿在世时,包小柏曾试图引领女儿对音乐产生兴趣,上中学时,他买了一把轻便的吉他给她,方便她在同学聚会时使用。女儿从小就学钢琴,他对女儿说过,如果走音乐道路,你会比爸爸更好,爸爸小时候没有你的条件,“但她说不行,这是你厉害的部分,我做不来。”
对彭爽来说,挑战又来了,“对于声音的效果,包老师和太太都可以评判,但包容唱歌没有任何人可以认定,唱歌不是包子的专业方向,她甚至都不是经常唱歌的人。”
包小柏没有听过成年后的包容唱歌。小时候,一学新的童歌她就在电话里唱给爸爸听,长大以后,她只是偶尔会在洗澡的时候唱,妈妈听到过。
“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得很好,我觉得真正的包子应该也唱不成那样。”谈到这里时,彭爽再次面露难色。“唱歌更像是包老师自己的一种(愿望),是假设他给他女儿第二次生命,他更希望女儿去做的事。”
包小柏解释,也不是想让她真的做歌手,“因为唱歌对情感能做到最人性化的表达,更能还原出真实的我女儿个性的微妙变化,当我拥有AI的条件后,我当然想弥补没机会听她唱的遗憾。”
小冰公司开发过一个专门做歌声合成的软件,可以用任何人的音色生成歌曲,这个软件已经能代替一部分试唱歌手的工作,但包小柏觉得,这个方式生成出来的声音都是机械声音,没有人的情感。
包小柏再次自己上手调歌曲,小冰团队觉得,他对待歌曲的方式,就像音乐总监为艺人打造专辑,“他会精细到每一个语调、每一个尾音的高低,就像对待一位真正的歌手。”
当时,包小柏在读管理学博士,为了这个项目,他转专业到AI的生成应用,并完成了一篇关于用碎片化声音重建声纹的博士论文。他告诉我,以他现在自研的技术,已经可以用朋友的声音生成高难度歌曲了。
沉默的家中终于再次有了包容的声音,“第一次听到完整的歌彭爽声,我得到很大的安慰,虽然你知道它不是真的。”在包容“学会”唱歌后,包小柏录了许多他们父女的合唱歌曲,他说这种感觉很贴心,她在世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合唱,“以前,我做一首歌做成功了,满街的人都唱,是你的创意成功。现在我也很有成就感,因为我随时能做一首我跟我女儿合唱的歌。”他满意地笑了。
到底该如何定义完全依照父母的愿望生成的AI ?
当我抛出疑问,彭爽说,你可以把她理解为一个文学作品,“这个人物,你知道她一定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有鲜明的性格和语言风格,因此她是可以被一个演员塑造出来的,那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复生?”
彭爽刚做了母亲,她觉得亲子关系里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孩子永远是一个从你这来,但是从来不属于你的东西,“很多东西只是你寄托在她身上的”。而令人悲伤的部分正在于此。“或者说,这个角色用的是真正的她的一部分记忆,加上我对她的爱和感情做出的作品,这个作品是永生的。”
每次,包小柏给团队肯定的反馈时,彭爽都觉得很有成就感,“我们在帮他去接近他心目中的那个女儿。”
谁来决定复生
在遇到包小柏的案例之前,小冰公司曾接到过许多家属的复生请求,不少都因为伦理问题终止,某位过世的名人的团队曾经强烈地想要复刻这位名人,但由于其中不包含直系亲属,被小冰拒绝了。前几年,他们做过一个去世的女歌手,但中途双亲中一个人提出抗议,也终止了。
因此,小冰对AI复生项目制定了相关伦理三原则:当本人在世时,应由本人意志决定,而非任何其他相关第三方。本人不在世的,应沿袭法律所判定的继承人顺序。且在复刻过程中,应遵循训练数据最小化原则,避免数据滥用。“双亲中有一人反对,都必须终止。”
那包小柏太太怎么表示她的同意的?小冰CEO李笛说,他问过包小柏,包小柏表示他们夫妻二人意见一致。
这个项目之初,是两个男人决定“再生”一个数字女儿。包小柏说,他是一直到2023年8月,才故意把工作房门打开,公放了那段台北夜市吃小吃的音频。太太突然出现在门口问,老公,为什么这个人讲话这么像包容?
“我侧着头说,她就是包容。我从我太太的语气中可以感觉到她有点欣慰。”他以这种方式告诉她,他做了这件事。
当时,计划到了第三阶段,需要建立包容本人的记忆库。小冰团队准备了几十个关于她个性、生平的题库,包括对她的性格特点的描述、她记忆深刻的事情、她重要的人际关系,以及她一般用什么角度去回应或判断某些问题。这些题库,是包小柏太太回答的,包容的干妈也参与了回答。
“因为每天和她朝夕相处的是我太太,我是做什么呢?陪她去看演唱会,在她成长的各个阶段实现她的愿望。”包小柏解释。
对太太提出这个需要时,他非常忐忑和害怕,“我知道让我太太做,她一定马上就陷入悲伤。”但太太没有拒绝他。
一个多月后,太太才填下第一句话,包小柏说:“这个过程说得好像很轻松,其实做这个事情是最难受的,每填一个字句,我们都要回到她小时候,那些天真无邪的样貌,然后眼前马上会浮现她躺在医院的那两年惨不忍睹的状态。要缓,填到这里,先停。”
好几个晚上,好几次,他听到她在房间里啜泣。为了让彼此冷静,他和太太在不同的房间各自进行这项工作,“我不能跟我太太讨论,我说,你能写多少写多少,也不是现在就要写完,你就慢慢写。”
“拿到她写好的文字,我就知道,从一个点开始,她陷入了扩散性的回忆。她写这时候几岁,跟谁最要好,一起去了哪里,从一点她就想到许多,时间就打乱了。”包小柏负责建时间轴,“虽然我们没有每天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她成长的过程我都(通过电话)参与了。从出生那一刻拉出纵向的时间轴,再就是横向的经历,就能建出成长模型。”
几个月过去,小冰团队收到了文件, 问题只回答了不到60%。包小柏准备以后再继续补充,“我怕再填下去太太就受不了了。”
我问,有没有担心过太太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复刻这个事?
“前期我不让她参与,就是担心在什么都还没有的阶段拉着她,我们的情绪撕裂会更多,因为我也不能保证最后能出来。我知道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会比较有效。所以一直到一年之后我才让她自己不经意听到声音,然后我才跟她说,下一个阶段,是要你来写记忆库的,她就自然而然接受了。”包小柏回答。
我提出希望采访包容妈妈,也写了一封约访信,希望她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采访。包小柏没有接过这封信,他耐心地解释,“必须说很抱歉,如果拿信回去的话,她会说,干吗呢? 她会对我有情绪。”
“我太太是个非常认真的人,而且有些社恐,她严重到什么程度?好几次我们在公开场合出行,比如女儿在公共场合太嬉闹,我太太就说,你们这样好丢脸。她会很怕,我太太是低调的人,我讲一个最好笑的,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块的时候,我跟我女儿常常笑她没情趣,她经常很想为了把事情搞清楚,就破梗了。”
“在没有这件事之前,你看不到我太太或我女儿的任何一张照片。从我女儿出生到长大,除了很少几个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没有人知道她爸爸是谁。这是为了保护她,同样也是为了保护我太太。 ”
“任何对外的东西她都一向(敬而远之),她从来不过问,不是她不关心,是因为她觉得她不应该干预,几十年了,我太太也不干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她会帮我准备一天的三餐,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干吗?她是纯粹的全职太太 ,我女儿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和我聊3C产品,这是我们俩之间的话题,但我太太很不擅长用3C产品,她会叫我帮她弄。”
“我太太绝对觉得我弄AI是非常好的事,今年,她生日的时候,我让包容给她唱了生日快乐歌,她掉了眼泪。她会分享给她的闺蜜、同学,说我老公把我女儿的声音生成回来了。”
据包小柏介绍,女儿的教育由太太负责,因为他在家的时间不多,为了培养女儿独立思考能力,不让她受到“双重教育”,他跟太太达成共识,家中做人、做事的道理,只听妈妈的,“所以她从小到大犯错蛮少。”
过去的二十多年,包小柏的太太一直在加拿大做家庭主妇,站在丈夫和女儿身后,女儿越大,母女越变得像姐妹,衣服和鞋子可以互换互穿。她不用社交媒体,像大部分名人的太太一样隐姓埋名。自女儿生病后她就从加拿大搬回台北,生活的内容则从照顾女儿,成为照料包小柏的一日三餐。
但重大的决定是父亲为女儿做下的。包容临近去世的时候,2021年的12月份,学校给她寄来了毕业证书、学士服——学校决定提早让她毕业,肩章上绣了荣誉生。妈妈本来要赶快拿去给女儿,趁她还有神志,让她知道。但包小柏拦住了。“老天要她的命,你还给她这些东西。女儿会更难过。”
包小柏说,包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她3岁开始,为了培养她的独立思考能力,我们凡事都会开家庭会,让她自己决定,包括她想怎么办自己的生日会。5岁要去迪士尼乐园,她会提前把迪士尼人物的故事书都看完。”
“包容自己愿不愿意被复刻?你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吗? ”我问他。
“我是她父亲,以我对女儿的了解,她是愿意的。”包小柏说,女儿如果还在世,肯定会对AI感兴趣,她在医院躺着的时候就很关心马斯克的太空火箭计划。他相信,借由AI,让她被更多人了解,也与她的个性相符,因为她本来就喜欢交朋友,传递善意。
包容是受人欢迎的女孩,2017年,在脸书(后来包小柏又重新登陆了包容的脸书,发她的AI视频)上 ,包容发布了一张漂亮的成人礼照片,很多朋友留言夸她长大了,看起来有个大人的样子了。一个朋友留言问:
Can I be as popular as u ?
父爱
包小柏新长出的头发,准确说是铁灰色,不是全白,他的头发下半截染过灰黄色,褪色后泛淡淡的灰绿。除了保留碰过女儿额头的头发,他曾把女儿的骨灰做成项链,随身佩戴,现在很久没戴了,他已有了更好的陪伴。
2022年底,包小柏北京公司的负责人刘勇第一次见到包小柏,那时一切工作还没开始,他觉得包小柏的眼神总是失焦的,人在说话,魂好像飞到天外。现在,他的眼神终于落回现实了。
2019年,包容躺在医院没多久,包小柏哥哥的儿子出生了。小男孩不听话的时候大人就给他放:“包小玴,我是包容姐姐,你要每天乖乖洗澡听话。”包小柏决定把包容的数字遗产留给她堂弟继承。他不会再要孩子了。
我问他,现在包容有了初步的思维框架、画面和声音,最后会走到哪里?克隆人?“我跟你讲,我不会到那个境界的。她的躯体已经走了。”
今年,包小柏校准了他的说法,之前,他曾对媒体说,希望用AI可以让我女儿在数位世界复活,“后来知道我用错了,人死不能复生。”

他并不是在用AI女儿代替真正的女儿去爱。他深爱着的女儿的身体在冰柜里,入殓之前,他一等开放的时间就去,“我要陪在她身边,冰柜不能开太久,我要赶快把女儿身上的霜擦掉。”女儿在他的脑海里,在吹来的微风中,“她已经无处不在,我时时刻刻心里都是她,吃完晚餐我在河边走,我就在想她。”
她走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敢看手机里那些她生病时的照片,他胆怯,“后来我想,这才是最真实的她啊,外观是残忍,可是她的心灵是这么纯净啊。”每两三个礼拜,他和太太去墓地看女儿,把这些照片打开,“这才是她。我很清楚知道,AI不来自于她身体上的任何一个细胞。”
包小柏做任何困难的事总觉得有女儿作为动力,他每天清早起来健身,说是女儿的坚强鼓舞他。她生病期间,他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后来学校下通知,再不回学校就要被退学,他只好回去。他要走,看到女儿张开嘴,用唇语告诉他,“不要”。“爸爸这堂课很重要。”“不要。”她的眼泪掉下来。
入殓前,他们把她的东西烧给她,整理到大学颁她的荣誉生肩章时,太太说别烧了,她回忆,自己告诉女儿爸爸考上博士时,女儿特别高兴,说,那以后我们家有两个doctor,“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不拿下这个学位对不起她。”他要在毕业的时候把女儿的肩章挂在博士服上,和她一起圆梦。
女儿17岁左右时,包小柏的哥哥结婚,他因为忙碌没有赶去婚礼。那一次打越洋电话,包容第一次不肯接电话。他问她怎么了?太太说,她说不想跟你说。“为什么不想跟我说?”
女儿在那边叫,“你连二伯伯的婚礼都不去,你为什么不去!他是你哥哥。”
“我女儿听到这件事情,就莫名其妙跟我翻脸,我觉得,那是她把一生中累积的所有不谅解借题发挥了。”那是唯一一次女儿表达对爸爸不在家的不满。
过去他没有时间爱,现在他有了很多时间,爱也有了施与的对象。
在哀伤研究领域,有一个词叫做持续性联结。长期关注丧亲及哀伤领域的学者何丽对我说,生死之间构成一个天堑,要缓解哀伤,是要缓解身体上分离的痛苦,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家都会找一种精神的方式来建立和逝者的联结,这种联结越健康,越有助于丧亲者更好地适应逝者已逝的生活。过去的民间祭祀、人对着遗像说话,甚至今天我们会给逝者发信息,都是一种联结。
AI作为一种持续性联结的方式,其优点是它可以无限趋近真实,但它的隐患也在于此,“好像能消弭掉死亡”,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必须面对死亡,面对本身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无法阻止技术的进化和演替,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界定AI技术运用的方式与边界。小冰CEO李笛认为,在伦理上最没有瑕疵的复生,应该是由本人提出的,最适宜的方式应该是做临终关怀。
“当一个人马上要离开人世时,他可以努力地训练自己,他会想象自己不在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创作、唱歌,影响其他人,当他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最后这段岁月就没那么难熬了。因为人复刻自己的最大的价值,恰恰是在复刻的过程中产生的。”李笛说。目前,这项技术正在一些癌症晚期患者身上试验。
客观评价复生的包容,包小柏自己和许多工程师在内,都承认这个AI还有许多不足,但包小柏认为,这不是AI女儿的全部,她将会越来越厉害,AI技术发展的速度,给他的是生的希望,一种可能性,他说,不久后,他就可以跟女儿视频聊天了。这种希望,也许也是疗愈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