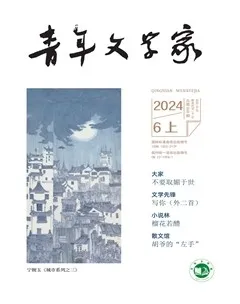记忆的灯
沈文炳

我的老家在陇东高原的残塬沟壑区,祖辈人曾经历了“黑灯瞎火”的漫长岁月。
清油灯,是深居大山里的先祖们使用历史最长的一种灯。祖父说,他小时候,老家人就沿用着祖辈传下来的清油灯。那时候,能买得起一盏铸铁的油灯都是富裕人家。铸铁油灯底部是一个直径十五六厘米的铁盘,中间竖一根食指粗的高约三十厘米的铁柱,顶端一个盛清油的小铁碗。棉花捻子浸入小油碗中,另一头儿探出碗沿点着照明。而大多数人家使用的则是一种鼓状、俗名“鼓儿灯”的陶釉油灯,苹果般大小,上部凹面正中有一隆起的小圆孔,用以添油、穿捻子。我小时候见过这两种灯具,个别人家还在使用。祖父说,这些灯具是驮队从南路运回来的。在交通和经济条件十分落后的年代,这样的灯具也不是所有人家都能买得起的,一些穷人家只能用破碗点灯。他们将半块破碗搁在窑帮钉进去很深的两根红柳木橛上,为了光亮能照得更远一些。至今,老家那些废弃了的旧庄院窑帮上还能清楚地看到被油烟熏过的痕迹。还有一些更穷的人家,没有清油时,就将磨细的油料面捏附在高粱秸秆上点着照明,老家人称之为“黑油棒子”。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的供销社有了煤油。煤油要比清油廉价。于是,煤油灯就代替了古老的清油灯。煤油灯制作简单,一个废墨水瓶,盖子钻个孔,将废旧的薄铁皮卷成的灯芯穿进去,再将棉花灯捻穿进灯芯,一个煤油灯就制作成了。但即使这样简单的煤油灯,它的制作材料也不容易找到。废旧的墨水瓶只有村学里或有念书娃娃的家里才有。
煤油灯的光亮较之清油灯要略微好些,但捻子拨得过亮,有呛人的油烟味,最关键的是煤油按票供应,并且每斤三角九分钱。这在那个年代也是不菲的价格。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老家生产队的劳动日值也不过四角钱。一个青壮年劳力,一天的劳动值几乎买不到一斤煤油。所以,人们对煤油的使用是十分节约的。我们家的煤油灯正常亮度只能照两三米,放在土炕与锅台中间的土栏杆上,窑掌两三米的地方都没光亮。祖父的煤油灯,更是昏暗,堪称一灯如豆,站在窑洞门外看去若隐若现,灯光只能照亮一米见方的地方。谁如果挑他的灯捻,会招来一声训斥:“那灯点的是煤油,不是水!”祖父有晚上看书的习惯,他的书就在煤油灯附近不超过十厘米的位置。
我至今记得,天快要冷了的时候,父亲在昏暗的灯光里为一家人编制过冬御寒的毛袜,母亲长年在昏暗的灯光里为我们缝补着破旧的衣服。
我还记得,为了节省灯油,夏天的山里人劳动归来后,是借着月光坐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的。现在想想,在月光流淌的夏夜里,一家人坐在凉风习习的院子里吃饭说话,那倒是很恬静惬意的乡村生活!
冬天是山村里人的农闲时节。天黑之前人们就吃完了晚饭,大多数人家也不掌灯,不串门,不闲坐,直接躺进热乎乎的土炕进入了梦乡。
马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市的一种照明灯盏,有玻璃罩可以挡风,夜晚在室外照明算是最先进的灯具了。二十世纪七十年前后,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修整水平田的热潮,乡亲们挑灯夜战,马灯功不可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城里人和机关学校已使用的罩子灯没能进入老家。对煤油使用十分节约的山里人不会奢侈到使用罩子灯的,只有我们家曾奢侈过。大约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将罩子灯买回了家,其明亮又环保的优点让村庄里的亲邻们羡慕不已!
1988年年末,环县杨旗至合道35千伏输变电工程竣工通电,沿线的川塬村队都用上了电灯照明,而老家人只能“望电兴叹”。过了一两年,乡亲们试图从外面买回废旧的高压线,拆解开来三根一束架在木杆上,从六七里地的赵塬村部将电“接”回了家。然而,让乡亲们大失所望的是,因线路太长,电压不足,晚上根本不能照明,乡亲们只能继续使用煤油灯。塬上人笑我们山沟里人“太洋气”,挂着电灯泡,点着煤油灯。
2007年,在乡镇工作的侄子树农,与县电力局多次沟通争取,终于将10千伏高压电引进了老家,乡亲们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从此,老家人迎来了光明的生活。记得那年除夕夜,老家的各个庄头灯火彻夜通明,烟花绚烂多彩,爆竹声此起彼伏,整个山村沸腾起来了!朴实的乡亲们辞旧迎新,告别旧时光,庆贺新生活,感谢党和政府的春风雨露。
2016年,老家人又率先享受了国家“户户通”的农网改造政策,乡亲们又一次沐浴了党的阳光雨露,深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给山里人带来的福祉。
从老家变迁的灯里,乡亲们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
——神奇的“阿拉丁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