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里的《红楼梦》
王悦阳

北宋汝窑青瓷盘盛放佛手。
作为“康雍乾盛世”的一曲“天鹅之歌”,曹雪芹溶毕生心血所著成的小说《红楼梦》是一段文字里的追忆逝水年华。小说里弥漫着作者对于往事的痴迷与回望,以及一声声对于盛极而衰、家族败落、命运无常的叹息,读之令人难忘。
尽管《红楼梦》是虚化朝代的,但明清时代的“物”在书中无所不在,曹雪芹特别用了许多具象之物,如荷包、饰品、佛手等,勾画人物各自的轮廓与性情,乃至作为象征、串连故事情节之物。透过文物看《红楼》,也成为一种解读“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方法与途径。
一部奇书《红楼梦》,字字句句离不开“情”,亲情、爱情、友情、主仆之情……“情”与“人”之间的互动,紧密絣织。而“人”又透过“物”的点缀,显得立体而有温度。“物”,让小说有了画面,成为看得见的《红楼梦》。近日,“看得见的红楼梦”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院对外展出,展览以《红楼梦》为题,通过大量文物的集中展示,以“物”来读小说,带领人们看见《红楼梦》的绝美与哀戚。
大雅可观
小说中的贾府,是诗礼簪缨之族,追求礼教、世代读诗习礼,曹雪芹就是生长于这样的贵族世家。祖父曹寅,善写诗,好校勘,奉敕编《御定全唐诗》。自曾祖父曹玺始,曹家三代四任袭替江宁织造——由皇帝亲信担任的要职,负责织造、买办皇家所需丝织及各类用品。如此特殊的生命经验,感染着曹雪芹,体现在《红楼梦》里优美的诗词曲赋、精致物品的细腻描述。

清乾隆年间金镶东珠猫睛石嫔妃朝冠顶。
元妃,本名贾元春,是贾宝玉的长姐。十三四岁时入宫,后晋封为贵妃,使贾府的荣耀达到鼎盛;所谓省亲,指的是宫里嫔妃获准返家,探望父母或其他尊亲,以尽孝道。贾府为了迎接元妃归来,特别修建了省亲别院——大观园。大观园,是元妃失去青春、与家人短暂相聚的乐园,也是贾宝玉与众金钗们,在其权力的庇护下,仿佛遗世独立的青春乐园,更是曹雪芹缅怀过去,繁华已逝的失乐园。此次展出的清代乾隆时期金镶东珠猫睛石嫔妃朝冠顶,长16厘米,座径4.8厘米,从中可以一窥清代嫔妃的服饰造型。所谓冠顶,依身份不同,层数、东珠、珍珠及宝石数量等,皆有相应规范。累丝金凤二层,以匀圆东珠相连及点缀,计有十一颗;凤首、腹及尾羽饰有不规则小珍珠;顶衔棕褐猫睛石一颗,由此可见应属嫔妃之朝冠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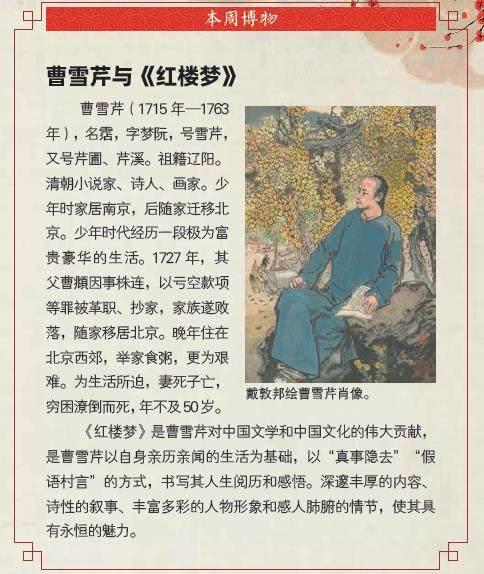
除了皇家之物,《红楼梦》对居家生活瓷器的描述,曾提到不少宋代名窑,像汝窑、定窑,也提到明代官窑,像宣窑、成窑等,装点着贾府、大观园的日常。曹雪芹将这份日常的奢华,包裹在精致讲究的古董瓷器里。特别是定窑,在书中宝玉生日开夜宴,就以40个定窑碟盛酒馔果菜。低调奢华,令人印象深刻。再如探春房中的紫檀架上,放着“大观窑的大盘”。这是小说仅此一次,以“大观窑”代称“汝窑”。暗示着探春掌权理家之后,明法守礼,革除弊害,是唯一具有“大观精神”的金钗。“大观窑的大盘”盛着“娇黄玲珑大佛手”。佛手,是清宫喜爱摆饰、取其清香的果品,也是书里慈悲的象征。老妪刘姥姥之孙板儿与最小金钗贾巧姐,在探春房中玩耍、传递佛手,暗示着姥姥将拯救抄家流离失所后的巧姐。
一番梦幻
“假作真时真亦假”是《红楼梦》里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暗示着书中所及,是真,也是假。曹雪芹透过虚幻的“补天未用”之石,通灵下凡,引领读者看见真实世界里的繁华与衰败,看见女性生命的美丽与哀愁,以及不同形式的悲剧。曹雪芹特别用了许多具象之物——
荷包是书中经常出现的小物件,这是一种满族随身佩戴之盛物小包。男性使用时,悬挂于腰带两侧成对使用。在《红楼梦》里,“泪光点点,娇喘微微”是宝玉初见黛玉时的描述。出身世代袭爵的黛玉,是贾母宠爱的外孙女,灵气脱俗,却总在生病与流泪。她身体孱弱,鲜少针线,“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林黛玉亲手做荷包给宝玉,更加凸显荷包的可贵,谁想到一回误以为荷包被宝玉转赠他人,生气回房。事实上,宝玉怕荷包被人拿去,一直戴在里面的衣襟上。如此珍重,如此贴近自己,通过对荷包的描绘,将二人之情感细节展现无遗。

清代红锻金银线绣荷包。
再如清代的玉锁形佩,外观即锁形,一面牡丹,一面“玉堂富贵”。以络子络上,得以随身佩戴。立即让人联想到有着“金玉良缘”之说的薛宝钗。宝钗身上总是佩戴着金锁,錾着“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与贾宝玉所佩通灵宝玉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成对。她生于皇商家庭,从小读书识字,品格高洁,素喜雅静。曹雪芹说她装扮朴素,“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屋子摆饰如“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这些描述与宝钗戴在脖子上的“金锁”皆暗示着宝钗最终的归宿与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