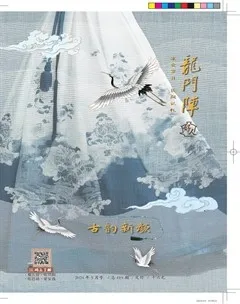成都,成都
欧阳帆
“成都多好的嗦,干啥子不回去嘛!”
仔细数数,我在成都待了一年零八个月。
研究生毕业签单位,也是缘分,我签到了成都一家出版社。来之前,出版社的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有没有听过‘少不入川,老不出蜀,你来可要想清楚!”我当时一定重重点了点头。总之,二十五岁,一无所有的我从北京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落脚成都了。
租的房子就在单位斜对面,上班过个马路就到。九点上班,经常八点才起,不急不忙吃点东西,偶尔会觉得这样太对不起留在北京每天不到七点就得出发上班的同学们,但很快就想明白了。虽然八点才起,不过成都比北京靠西,太阳应该晚一个钟头才升起吧。既然太阳都要晚点升起,为什么我不能晚起一会儿呢?
成都的闲当然不在这晚起的一个小时,住得远的同事还不是一样一大早就得出门。但成都的闲跟太阳可能真有关系。单位的楼有十几层高,我喜欢站在顶楼俯瞰,看出去,还是楼顶,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长方形。但成都的楼顶跟别的地方很不同,我以为如果要给成都做张名片,背景就要用这些楼顶。成都的楼顶上多长了野草,种了花果,有的楼顶上还长出瘦瘦小小的一棵构树来。
我租住的房间外面就有一棵构树,当然比起那些长在楼顶上的小构树,它当之无愧是棵壮硕的大树了。朱天心有篇小说里写到过构树,她写道:多少结红果子的构树还在,而从前谈心大笑的朋友已久不见面了。很不巧的是,我窗外的构树从不结那毛刺球一样的红果子。它只作为一群群无名小鸟的栖息之地,在早晨或者傍晚变身为一棵会唱歌的树,让我离开成都后都久久难忘。
回到说太阳,成都是太阳少,雨水多。也许是我起得太晚的缘故,常常感觉一觉起来就像到中午了,天色将明未明,昨夜的雨像落到一个迢远的梦里,睁开眼看天空,年年月月是这样暧昧不清的色彩,好像漫长人世也不过就是此时,好像片刻也经过了漫长的人世。可是,我知道,昨夜一定下过大雨,不是在梦中。空气里潮湿的味道,台阶下暗绿的青苔,还有院子里被风雨打落了一地的桃花花瓣……
大概,就是夜雨的浇灌,楼顶才变得如此葱葱郁郁。成都,或许是中国的阳台。天空之下,一座座楼,也不过是个花盆呢!想到社里老师说,成都“肥”在温江,温江嘛,插根筷子都能噌噌长出树来噢。听的人都笑了,意会的笑。天府之国,万物生长,不靠人力,是老天自有打算。到人情世故上来,也还是这样,打算也好似没有打算。成都的闲是像细雨润无声一样到骨子里去的。
街边麻将铺子、苍蝇馆子,可不就像那些楼顶上的植物一样,再自然不过地迸发出来的吗?刚到成都时,同事朋友不经意间会聊起地震的经历。路过一幢大楼,她指着大门前的柱子说:“你不知道,地震的时候,这柱子都开了裂,看得到里面的钢筋,吓死个人!”接着又说,“我那会儿在上班,十几层噢,吓得赶紧往楼下跑,不行,穿的高跟鞋,跑下楼来,累得去了半条命!”说完自己嘻嘻笑了。
说起地震时跑到公园搭帐篷避难,说地面起伏像波浪,都好像在说故事了。这一页翻过去了,像一梦醒来,黄粱未熟,像走过了奈何桥回望前世,也不过是“只好到公园去,无聊,只能打牌”。记不清牌打了好多轮,昏沉沉地危险也就过去了。
天意和人事交融沉淀,慢慢分不开也分不清了。四川省博物院里看画像砖,最中国的马车画像原来肇始于此。汉代文化的飘逸流动不靠想象,羽化成仙,是化天意而成人事,是有为而成无为。如今天意渐远,人事难亲,少不入川,是无可作为,还是无能为力?只有老街的榕树须髯垂垂,用茂盛的树冠遮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来。树荫深处,平行巷子,依依烟里,无尽的日常生活也不过是蚂蚁窝里一个太守梦。只是梦中千般好,梦醒皆索然。
且不管这些,吃茶去。太阳好的时候,是节日,老天爷放假,心情理应要比阳光更明媚。约朋友人民公园吃茶去。竹靠背椅,竹方桌,依花靠水紧挨着密密摆起。中午的时候,人也不算多,摆满了的椅子就是一种热闹。还有人在公园湖中划船,喝茶,看人,晒太阳。春夏秋冬,四时花不同,香不同。同去的朋友却偏偏不看花颜色,只念叨望江亭的竹子好,又说到蜀南竹海去了,兜兜转转,又说回来,说在川大读书时爱上望江亭喝茶,这时太阳不在头顶上了,要换个座位了,得跟着太阳挪座。
晴天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安好,还有一种集体的兴奋。英国人见面喜欢谈论天气,成都人大概很能理解这点。道一声“今天天气真好”,绝不是没话找话,碰上爽利的晴天,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欢喜。盆地地区的自足,固然因为地理区域上的相对独立,但面对太阳时的欣喜,这种情绪的集体经验也未尝不是自足的核心部分。如今蜀道难的艰辛已逝,而蜀犬吠日大概也不再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快乐了吧。选一个好天气,不去吃茶,那就去吃火锅吧。
南北方都吃火锅,但区别大了。在北京时,吃火锅无非就是吃羊肉牛肉之类。到成都,出版社的老师带我吃火锅,让我点。我当徒弟的不好意思,推说不会点,结果是真的不会。羊肉牛肉看不上眼,三样必点是鸭肠、黄喉和牛肚,还有猪脑花也可试试。鸭肠用筷子夹起,在滚锅里抖几下,千万别煮过,要吃的是一个脆爽。老师介绍起来滔滔不绝,这火锅味道之外更多了份隽永。火锅店生意都很好,腾腾热气驱散了夜的清冷。
夜里常常下雨。一年中的大部分雨都是夜里下的。有个朋友带我去锦里喝酒,黄酒,两层小酒楼,木桌条凳,我们坐下把手机放在桌上,感觉很像游侠把佩剑放下,自己就觉得潇洒。喝酒到夜里十点过,坐车回家。下车发现下过阵雨,特意绕远经过商业街,去感受雨湿梧桐的情境。夜晚一条无人的小街,梧桐叶子落在湿漉漉的地面上,一个个小脚印一样。后来我写打油诗,写“碾落梧桐成锈色,空枝尤待凤凰来”。
写打油诗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成都了。在成都的一年零八个月里,我往返于北京和成都间大概四五次。路途上,常常遇到去北京探望儿女的成都父母们,他们问我:“你是在成都出差?”
“我在成都工作,去北京办事。”
他们或者困惑于我为什么一个人在成都工作,或者感慨他们在北京生活的儿女:“成都多好的嗦,干啥子不回去嘛!”
而我,终于在来到成都的一年零八个月后,又重新收拾行李,离开成都返回北京了。和我那些当初就留在北京工作的同学一样,开始了早上七点就出门上班的生活。堵车、雾霾、生活压力……有闲岁月之后,好似只有无穷无尽的繁忙。不再栖身于构树之旁,游走于榕树之侧,匆匆将生命投入时间之流。这里,的确,太阳升起得更早。
不由叹一声: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