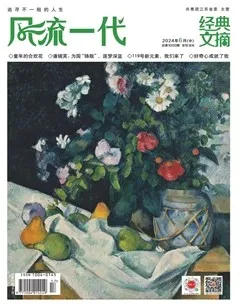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地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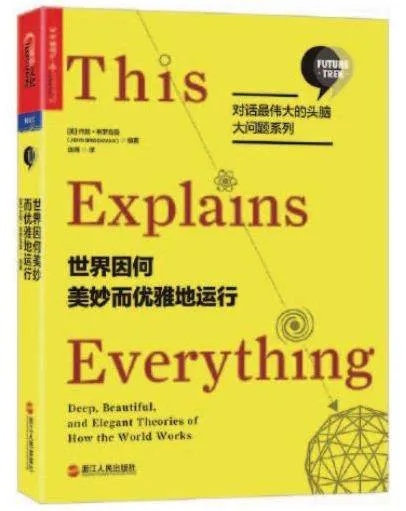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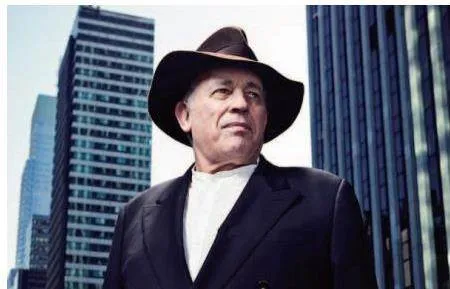
【内容简介】
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地运行?本书编者约翰·布罗克曼召集了146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回答这个“大问题”,并把他们的答案和论述集结成书。
这本书将带你认识这些“最伟大的头脑”,看他们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从而开启你的脑力激荡。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科学明星”,包括世界著名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互联网思想家凯文·凯利、社会网络学家克莱·舍基等。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晶体的优雅如何体现出普遍的数学法则?
是什么让摩尔定律成为可能?
鸟类是恐龙的直接后裔吗?
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地球在运动?
……
在这本书中,你会找到更多让世界美妙而优雅运行的奥秘!
生命是一组数字代码
马特·里德利(科普作家,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国际生命中心创始主席)
如果今天,再让我像1953年2月28日那天的清晨那样,认为生命是一个极具深奥玄妙的课题,已经非常难了。在那一天的午餐时分,人类对生命的认知蓦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顾在此巨变之前所有对“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你会发现,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类一直在苦苦追寻这个答案,却始终不得其解。生命是由具有特异性和复杂性(主要是蛋白质)的三维物体构建而成的,生命可以准确地进行自我复制。这是怎么实现的?你如何着手设置一个三维物体的复制?你怎么才能让这个复制品以一种可预测的模式,保持不断地生长和持续地发展?对这样一个严肃的科学性问题,我们绝不能凭空猜测答案。
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文·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曾经尝试过寻找这个答案,但他却求助于与此毫无关联的量子力学。千真万确,薛定谔运用了“非周期性晶体”(aperiodic crystal)这个术语,假如你见多识广,就能够把非周期性晶体视为一组线性代码,但我想要想做到这一点,光见多识广可能还不够。
虽然刚才讨论的问题让人迷惑不解,但谢天谢地,人类终于意识到DNA在生命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DNA是那样简洁明了。在1953年2月28日之前的所有那些对生命的胡乱解释,都与人类挥手作别。不过,这些解释倒是在原生质和生命力方面给予了人类洞察力。
接踵而来的是双螺旋结构,对此最直截了当的理解便是如弗朗西斯·克里克几周后给他儿子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双螺旋结构是某种类型的代码”,数字的、线性的、二维类型的,它们可以无穷组合并能瞬间自我复制,这便是你所需要的全部答案。
以下是克里克信函的部分节选,写于1953年3月17日:
我亲爱的迈克:
沃森和我可能得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发现……现在我们坚信DNA是一组代码,即基础或叫作字母的排列顺序使得一个基因有别于另一个基因,就像印刷的一页纸不同于另一页一样。你可以从中获知大自然是如何进行基因复制的。如果把一个拥有两组基因的链条分拆为两个单独的基因链条,并且每一个链条都可以和另一个链条聚合在一起,那么,因为腺嘌呤(A)与胸腺嘧啶(T)总是一对,鸟嘌呤(G)与胞嘧啶(C)也是一对,我们便能够获得之前两组基因的复制品了。换言之,我们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生命之所以能代代相承、生生不息的奥秘……你肯定能明白沃森和我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从没有过一个谜题,像生命的奥秘这样,在清晨时分还如此让人迷惑,而到了解开谜题的午后,又让人觉得答案如此显而易见。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帮助
塞利安·萨姆纳(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生物科学学院高级讲师)
我经常会和孩子们玩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是“猜猜我是谁”:想出一种动物或一个人,或一件物体,然后试着将它描述给另一个人,但不能直接告诉对方。对方需要猜测你描述的是谁或是什么。要玩好这个游戏,你不得不融入其中、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它是做什么的,你对它有什么感觉,你认为它怎么样和对它有什么期盼。
现在我们也来玩玩这个游戏。读读下面的人物场景,看看你是否能猜得出来他们是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这不公平!妈妈总是说我碍手碍脚、游手好闲,她再也没法忍受与我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我喜欢与家人同处一室,我压根儿不想离开。为什么要冒着离开家的风险呢?谁知道外面会有什么不测风云呢!妈妈说如果我非要赖着不走,我们需要某种“胶水”来保证我们不被分开。现在的情况是,胶水昂贵,妈妈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生产这样的胶水,因为她忙于生产后代。但我有个想法:让我负责生产这胶水,用一点点细胞壁(妈妈应该不会介意),再加上一些糖蛋白(这些糖蛋白有点黏,所以我答应妈妈完事后会洗手),就大功告成了!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舒适的细胞外基质!只要妈妈源源不断地给我带来更多的兄弟姐妹,我就会欣然地去做大部分的工作。昨天晚上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妈妈,你猜怎么着?她说好的!但她还说,如果我食言的话,她还是会把我轰出家门。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我”是谁?我是由一个单细胞渐变成的多细胞。如果“我”想要和自己的家人聚在一起,那么就有人会因此而付出代价,那就是细胞外基质。如果通过自己家人来复制自身的基因,我也能从中受益的话,我并不介意付出劳动。
可能这个故事确实挺难理解的,那就换一个:
我或许就是你说的那种喜欢做妈妈类型的人。我喜欢生一堆孩子,我今年可能已经生了不少,至少我的孩子们都这么说。但看起来我乐在其中。当然,我会给予每个孩子同样的爱。但真的是非常辛苦,尤其是他们的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如果我得不到身边人的帮助,我最小的孩子就无法保住。我的身边都是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压根儿没有时间打扫房间。所以我会在某天跟老大说:“怎么样啊,孩子?可不可以帮一下妈妈?在我帮你多生出几个弟弟妹妹的时候,你出去找些吃的。记住,孩子,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你的这些弟弟妹妹会在将来报答你的。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会像你老妈一样也成为母亲。想想看,即便以后你我都不在人世了,我们仍然可以从她那里获得好处。如此一来,你就不用再担心性生活、男人或精子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了。妈妈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喂饱了,然后把家里打扫干净。好孩子,你赶紧出发吧,记住别跟陌生人说话,尤其是男人!”
“我”是谁?“我”是搭建社群的一只昆虫。如果“我”独自筑巢,在“我”不得不外出觅食时,“我”只能留下幼小的、无还手之力的孩子在家中。如果一些大的孩子能够帮“我”,他们可以外出寻找食物,而我就能够留在家里保护幼小的孩子。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更多的孩子,孩子们也会喜欢,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更多的基因可以通过自己的弟弟妹妹们传递。不管怎么说,对现如今的年轻人而言,在外面的世界生活相当艰难,宅在家里则没有那么危险。
在上面的描述中对细节略做调整,“我”也同样能成为一个基因组的基因,或是成为真核细胞的原核生物。
在进化的游乐场里,我是同类基本物体中的一分子,我是通过互助与合作的进化而来,我是主要的变体,以此形成各种生物复杂性。我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要帮助那些与我类似的物质,我们统一分工协作,我们之间也会有争执,但我们会通过合作平衡彼此间的冲突,偶尔使用强硬的态度来让反对者遵从自己也并不会出差错。我会出手相助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我感觉良好,而是因为我能从帮助他人中受益。我的小秘诀是什么呢?我愿意出手帮助自己的亲人,因为通过我们共同分享的基因,他们最终也会拉我一把。我乐于接受从独来独往到分工协作这样的改变,这让我感觉甚好!
合作与互助行为的进化,是一种简洁而优雅的理论,它解答了大自然为何如此繁复多样与精彩奇妙。它不仅限于妖媚的猫鼬或是毛茸茸的大黄蜂。它是一个普遍现象,涵盖了大自然中的一切好坏与美丑,并生成生物的各个类别,从而形成了这个无奇不有的大自然。独立进行复制个体的群体,比如基因、原核细胞、单体细胞和多细胞生物,会基于它们自身的需求,重新聚合在一起,形成崭新的、更为繁复的个体。这种新的个体集合只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复制。如果分开每个部件,它们将无法正常运行或是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大千世界中简洁而又优雅的法则,阐释了这种复杂性演变的原因:威廉·汉密尔顿于1964年提出的“内含适应性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涵盖了自然选择理论的精髓。个体之间会协助合作的原因在于,这提升了他们彼此的适应性,即提高了将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几率。接受帮助的个体受益于自身繁殖机会的增加,此为直接适应性;提供帮助的个体则因自身基因通过自己所帮助的亲人,提高了传递共有基因的几率而受益,此为间接适应性。但依然存在孤军奋战的昆虫、单体细胞生物和原核生物,这是因为分工进化需要恰当的条件:产出必须大于投入,保持独立复制的个体所拥有的选择将影响最终的结果。生态和环境也同样发挥着作用。劳动分工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石,基因合并成为基因组,线粒体和原核生物的合并成为真核生物,单细胞体生物合并为多细胞生物,独居动物成为群居动物。如果没有帮助和分工的进化,那么世界上的真核细胞、多细胞生物和动物社群就不复存在了,最后,我们这个星球就会变得贫瘠荒芜、毫无生机。
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已经深知这个简单的概念。然而,只是在近期,我们才意识到,帮助的进化不仅可以解释昆虫转化为真社会性的原因(汉密尔顿最初提出该理论就源于此),还能解释生物复杂性发生的转变。在这其中,安德鲁·伯克(Andrew Bourke)就生物复杂性起源的统一框架,在其所著的《社会进化的原则》(Principles of Social Evolution)一书中,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综述。这个令人信服的简洁理论,使得世界的复杂性不再那么神秘莫测,但却依然精彩纷呈。
如果成年人经常与孩子们在一起嬉戏,或许我们也会偶得对于生命复杂性简单的阐释。
(灿烂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