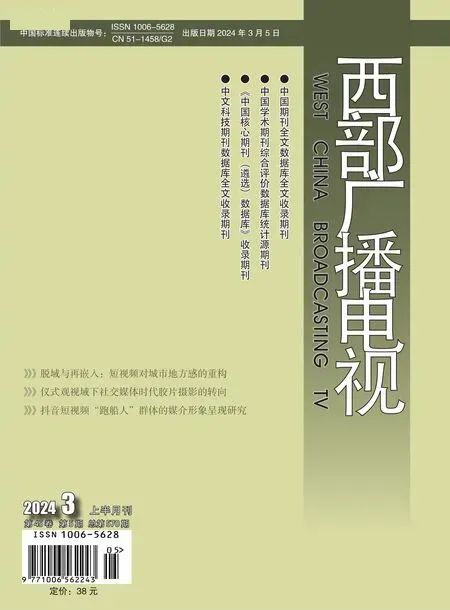欲望、冲突与双重束缚:精神分析视角下电影《河边的错误》的叙事策略研究
李 挺
(作者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电影作为一种年轻的艺术门类,其理论研究始终缺乏深厚且完整的根基,不得不从已有艺术门类和周边学科的成果中汲取经验。“从安德烈·巴赞的电影理论问世起,传统的电影理论开始向现代电影理论转折,克拉考尔和让·米特里的著作推动了这一转折,而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则标志着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改观。”[1]现代电影理论由于强调对电影文本和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相较于传统电影理论,其理论视域空前扩展。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周边学科相继被引入电影研究,电影精神分析学也正是在这一理论思想激烈碰撞的时期发展起来的。电影《河边的错误》致力于在病态逻辑和艺术想象之间达成一种“对接耦合”,看似迷乱模糊的精神症候视角实则潜藏着推动叙事的巨大动力。为了解析影片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心理与叙事结构,笔者以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工具,通过对无意识的欲望、冲突以及双重束缚等概念的运用,揭示出此类电影的内在叙事策略。
1 叙事始动:个体欲望与现实冲突
欲望总是对于某种缺失之物的欲望,并因而总是涉及一种持续的对于缺失对象的寻找。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中欲望的产生源自主体与大他者之间的断裂,经由这种断裂,一个缺口便被生成于主体的能指链条之上,这一缺口的运动最终涌现出了“对象a”即主体欲望的对象-原因[2]。大他者的欲望并非总是完全地指向主体,其欲望中超出或逃离主体的部分便构成了某种丧失,然而在主体看来其间仍具备某种对这种丧失或者说对大他者出逃的欲望的失而复得的可能性,而栖居于这种可能性之上的东西便被称为“对象a”。因此“对象a”并不是我们丧失的具体的某物,它是我们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某种恒定的感觉。因为我们作为主体总是在追寻知识、渴求财富和期盼爱情,而我们也并不会因为得到了财富而不去渴求更大的财富。早期成长经历在精神分析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童年是人的情感和意识尚未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欲望以及由欲望无法被满足而造成的伤痛极有可能演进为一种深重的童年创伤,而这种童年创伤在成年之后往往被压抑于个体的深层潜意识之中。
电影《河边的错误》的开头是4个孩童在玩抓人游戏,负责抓人的孩童谨慎地查看着每一间屋子,在查看过所有可以打开的屋子后,孩童推开的最后一扇门却险些令其跌落至废弃高楼外的施工场地中。在这里,电影完成了最初的叙事驱动,抓人的孩子没有抓到3个在逃的孩子,相反,最后一扇门所带给他的对于跌落的恐惧以及本不该存在于大楼内的外在世界的冲击,几乎注定了其关于“抓而不得”的欲望的丧失,此时的“抓而不得”也必然暗示主体(主人公)此后的童年创伤。马兰的冲突三角理论指出,冲突产生于主体内部某种被隐藏的感受,而这种被隐藏的感受通常就来源于主体的童年创伤或欲望,它出于种种原因不能被公开表达,久而久之就连意识主体都会将其忘却。同时,马兰也指出主体的焦虑产生于隐藏的感受被揭露,即当主体重新意识到自己的隐藏感受时就会焦虑,这是由于隐藏感受往往和个体的现实境况相悖。在电影的中段,马哲成功抓获疯子后他非但没有释然,反而变得与周围的同事格格不入,甚至不听从局长的劝告仍旧继续查案。而在查明“大波浪”的真相后,马哲则坐在家中打电话询问老王关于自己在云南立三等功的事情,却被老王一口否认。这些情节多次体现出马哲已经渐渐意识到了自身被隐藏起来的欲望,然而这一欲望却在不断的查案和询问老王后破灭。现实的处境无法满足主体的欲望,因此马哲与现实的冲突也就愈演愈烈,其自身的焦虑情绪也就愈发不可控制,内在欲望与外在现实的冲突也构成了马哲不断查案的动力。
电影的实质就是“第二次机会”。在电影的放映过程中涉及对所拍摄的现实的再演,与此同时德勒兹在《电影I:运动-影像》中把电影视为一种绵延的整体而非封闭的集合。电影通过剪辑达到向世界敞开的目的,从而可以被观众赋予更加多样化的意义,因此电影对于现实的再演更多时候其实超出了现实本身,可以认为其是一种扩大化后的再演,即所谓的“第二次机会”。被深埋于主体潜意识中的童年创伤在主体成年后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再次涌现。在电影《河边的错误》中,马哲所在的警队将电影院作为新的办公场地,同时马哲也被安排了一间新办公室,而当马哲上楼来到他的新办公室四处打量后,发现这里就是原本电影院的放映室。空白的幕布无疑是欲望最好的投射地,这一情节中马哲在新办公室透过电影放映窗口窥视的画面无疑暗示此刻的马哲已经取代了电影放映机的符号点位,即将朝空白的幕布上投射自己的欲望。在童年时期丧失的欲望往往会在成年之后以一种扩大化的姿态重新出现,而电影院这一情节也正预示着马哲的“第二次机会”的到来。同样的暗示在电影中还有多处体现,如片中多次出现的马哲用放映机查看证物照片的情节,又如许亮跳楼后马哲在电影院中所做的梦也是以电影放映的形式出现的。甚至在梦的结尾处,马哲为了挽救燃起熊熊大火的电影放映机,不顾众人的嘲笑,毅然决然地抱起电影放映机跳入河中。这些情节都显明了马哲与电影放映机之间的符号替代关系,两者都欲向外界投射自身的欲望,而此次案件所发生的小镇则成了马哲绝佳的欲望投射地。
2 隐性进程:双重束缚与替身人物
格雷戈里·贝特森所提出的“双重束缚”理论尽管脱胎于精神病理学中的精神分裂症,但与艺术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性。“双重束缚”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发出相互抵触的信息并期待对方必须作出某种回应时,尽管对方努力试图回应,但此时不论他如何回应都会受到否定或者拒绝,从而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精神分裂症就是对这种痛苦的显性表达。他者如迷的欲望给我们留下了两难的选择,这通常意味着:如果你不这么做,我会惩罚你;如果你这么做了,我也会惩罚你。以上就是“双重束缚”的典型形式。那么“双重束缚”理论又是如何与艺术产生关联的呢?贝特森认为“双重束缚”的困境虽然会为精神病患带来混沌,但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艺术家的创作增添意趣。在“双重束缚”的理论视域下,艺术家与精神分裂患者之间确实存在的共同点就是两者都采用了“双重视角”,如影视作品中的日出往往不会仅仅是日出那么简单,它通常隐含着对于某种“希望”的内在表述。同时,二者的区别也显而易见,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会混淆现实与幻想,把字面当作隐喻并最终将其客体化;而艺术家对其的运用则只限于艺术领域内部。
对电影《河边的错误》进行精神分析式解读的必要性在于其叙事理路已经远远超出了创作偏好或精湛技艺的范畴,其深刻性直接源自其所显明的病理性。在电影中表现出精神分裂症候的马哲也同样经历着“双重束缚”,如最初将疯子抓捕归案后案件已经告一段落,但马哲提出想继续调查时其内心就已经开始进行博弈。如果马哲同意结案,则会受到其自身想继续追寻真相的欲望的惩罚;如果继续调查,不仅可能会一无所获,而且会受到上级责难的惩罚。又如,马哲的孩子被检查出NT(颈项透明层)值偏高,但妻子执意将孩子生下来,此时马哲也受到“双重束缚”,如果将孩子生下来,则受到孩子有可能会发育不正常的惩罚;如果不将孩子生下来,则会受到让妻子失望的惩罚。电影将多个“双重束缚”叠加到马哲身上,并且随着影片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些束缚的强烈程度也随之增强,无法抵御其侵扰的马哲便最终走向了将现实和幻想混为一谈的精神分裂症候。
“双重束缚”理论不仅作用于人物的心理学层面,同时也在叙事的结构性层面上表现出其精神分裂症候,要阐明这一观点首先应当关注一个有趣的艺术现象,即“替身人物”。“替身”又称“双影人”,其源自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简单而言就是通过创作者的精心设计使得主人公与某一配角构成一种典型的镜像对称关系,此时的配角(替身)实际上就是主人公某些特质或者欲望的客体化映射。创作者往往采用为主人公打造替身人物的方式达成“自我”与“他我”之间的一致性与对峙性的杂糅[3]。替身人物作为主体部分特质或欲望的化身,其游离性使其获得某种“否定”的潜能,主人公往往会因为替身人物的否定性回归而使叙事获得一种“暗恐”的对峙张力。在笔者看来电影《河边的错误》中与主人公马哲所对应的替身人物有两位,一是疯子,二是片中反复出现的孩童形象,他们分别体现出与马哲的对峙性和一致性。
首先是孩童形象与马哲的一致性。电影的一开场便是由几个孩童的抓人游戏引入的,可以注意到的是负责抓人的孩童拿着手枪、戴着警帽,俨然一副刑警的形象。而后是当马哲询问发现凶案现场的孩童时,孩童的手上也同样拿着手枪并且离开时还向马哲提出自己特别想看看坏人的样子。最后是马哲在电影院睡着的梦中,马哲似乎变回了孩童时期并向疯子说道:“原来我早就见过你了。”正是童年与求而不得的欲望的相遇,才会使梦中的孩童早就见过疯子了,这也就解释了笔者为何在上文将孩童没有抓到人与马哲的童年创伤相对应的观点,片中的孩童其实正是马哲童年时期的替身人物。
其次是疯子与马哲的对峙性。马哲初次见到疯子时,便尝试主动去模仿疯子的行为——学着疯子将自己的外衣脱下放在河水中。而随着故事的继续发展,如果说疯子被捉拿归案象征着马哲短暂捕获了自身的欲望,那么当马哲想继续查案时,疯子的出逃则再一次象征着马哲欲望的丧失。而影片的最后,疯子与马哲在“疯狂”与“理性”上的换位也进一步说明了二者之间的替身关系。无论是“双重束缚”还是“替身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双重视角”,它提示我们在以主人公为主体的显性情节之外,对于其他人物所呈现的隐性进程的关注恰恰是我们应当重新加以审视之处。
3 再见时刻:实在界入侵与受众心理
在“双重束缚”的困境下人物心理的急剧压缩与聚合,会最终使其失去区分现实与幻象的能力。在拉康看来,当主体缺乏一个作为欲望所指的实在的对象时,主体就会以一种幻觉化的方式来满足自体情欲。因此,主体所拥有的那些最基本的幻想实际上就来自其原始欲望的升腾与消退。值得注意的是,幻象并不是欲望的对象,而是欲望的背景。如前文所述“对象a”是主体欲望的对象-原因,同时它也是逃脱了符号象征化过程的残留物,即“对象a”作为实在界的剩余物是无法被象征界捕捉并超越表象的东西。在通常的状况下,幻象作为一种防御支撑着现实以抵御实在界闯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在某些精神障碍患者身上由于其失去了辨别幻象与现实的能力,从而导致了其现实遭受到实在界的入侵。实在界作为一种与现实有别的“心理现实”,是无法被符号化的,也无法被客观“观看”[4],我们必须通过像电影这样的媒介从欲望出发对其进行“侧目”式的观看。
电影中的实在界入侵现象常常被表征为“亡者回归”,如《活死人之夜》,而电影《河边的错误》也同样使用了这一被大众文化所认可的影像表达。在电影院中睡着的马哲的梦境中,已经丧生的幺四婆婆和王宏重新以生者的姿态出现在马哲面前,并不断向马哲诉说着自身的欲望。按照齐泽克的说法,“不死的人”并非单纯地指向某种被驱力统御的象征杀戮与死亡的邪恶化身,相反他们是受害者的典型代表,死而复返是一种无奈的悲剧[5]。因为他们的死亡缺乏一种符号性的告别,这在马哲的欲望里则指代案件还没有真正告破,如此才导致了实在界的短暂入侵。实在界以亡者为媒介入侵马哲的日常生活,并不断对马哲施加着精神层面的折磨,而在这场折磨的尽头,等待着马哲的则是某种沟通回路的“爆炸”,也正是这种“爆炸”有力地宣告着再见时刻的到来。故事中的马哲只有抛弃寻获真相的结局才能意识到象征界虚假的一面,也只有当其面对另一种结局(抚养孩子)时,他才能避免直视实在界的入侵,从而被象征界的体系再次捕获。电影的结局是马哲与妻子一起给孩子洗澡的画面,从中可以推断的是马哲已经由追寻真相的欲望转向了抚养孩子的欲望,因此他也得以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沟通回路并从此前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从受众接受的层面而言,疯子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凶手?这一问题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重要,倒不如说做出这样的混淆可以视作是一个创作者能力的体现。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实际上两种立场均被写入了文本本身,最重要的是观众与批评家也都像故事的主人公马哲一样被卷入了这些立场。因此,创作者的叙事目的并不在于叙事文本意味着什么,而是它达到了一种效果,即观者的欲望与主人公的欲望一样被捕获进了一个意指的链条之中。观众因其效果短暂地转移了自己的欲望,从而变得同马哲一样渴求寻找到真正的犯人,在这一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创作者也正是通过这种混淆更好地实现了观者与电影人物之间的欲望的统一。
4 结语
电影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分析电影的方法专注于通过精神分析的手段对电影文本中的无意识欲望、童年创伤和压抑性特质等进行剖析。电影所营造的影像空间可以说都是虚构的,但同时也都是真实的。在齐泽克的理论中,我们所身处的现实并非真正的真实,而是充斥着符号与象征的“虚假”之物。相反,作为造梦机器的电影则为我们提供了刺破象征界的可能性,因而得以成为一种抵达实在界之真相的秘密通道,也因此通过对电影的精神分析考察,我们往往可以回溯式地发掘自我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