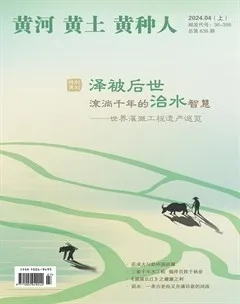淇水:一条古老而又充满诗意的河流
韩峰



“淇水滺滺,桧楫松舟”“淇水汤汤,渐车帷裳”“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此刻,我就站在从《诗经》中流过的淇水边,欣赏着这条古老而又年轻、充满诗意和文化内涵的河流。
历史悠久的淇水
淇水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方脑岭棋子山,流经山西陵川、壶关,河南辉县、林州、鹤壁、淇县,最后入浚县段的卫河,全长161千米,流域面积2248平方千米。她既没有长江的壮阔,也没有黄河的雄浑,当然也没有长江、黄河的名气大,可她的历史却不亚于长江、黄河。据国家地质部门实测,她的源头形成于下澳陶统,距今已有5亿年的历史。
在《诗经》中,“淇水汤汤”,水势浩大;在《山海经》《水经注》中,淇水“颓波漰注,冲激横山……倾澜漭荡,势同雷转,激水散氛,暧若雾合”,可见其“青春期”是多么的倔强、野性、桀骜不驯。也正因此,她无所畏惧,从峰峦叠嶂的太行山深处起程,在幽深峡谷中冲突,在乱石中游刃,在荆棘中穿行,在荒山上跋涉,在野岭上翻腾,五亿年风雨兼程,五亿年追求不停,五亿年执着地向着东方,迎接着一个又一个黎明,终于冲破禁锢、束缚,在没有路的地方,留下一个银光闪闪的梦,终于将自己融进大海,和大海的脉搏一起跳动。
“青春期”过后的淇水,性格变得有些温柔,母亲般地用纯净的乳汁哺育着两岸的儿女。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居住在淇水两岸。1932年和201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在碧波荡漾的河南淇县(朝歌)淇水北岸,发掘出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大赉店文化遗址,出土了各种石器、陶器、骨器、角器和蚌器,其中的陶器,不仅有仰韶文化的彩陶,还有龙山文化的黑陶和商代的灰陶。1932年至1933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和河南古迹研究会还在距浚县大赉店文化遗址不远的淇水上游岸边发掘出龙山文化晚期的辛村文化遗址,也是周平王时期西周卫国王室贵族的墓地,共发掘墓葬80余座,出土文物千余件,在国内外考古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些文物,后来被运往台湾,1960年,又运到美国展出,引起了文化部以及郭沫若、沈雁冰等540名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强烈抗议。1956年,在与两遗址隔河相望的朝歌石河岸村旁,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石河岸遗址,出土的钵、盆、鼎、罐、瓮、刀、凿、尖底瓶以及少量的猪骨、鹿骨,向人们展示了7000年前先民在悠悠淇水边的生产生活状况。时隔23年,1979年,在淇县花窝村淇河南岸,发现了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遗址——花窝遗址,以出土的铲、斧、凿、磨棒、陶器以及尖状器、刮削器等文物,填补了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的历史空白,为探索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翔实的宝贵资料和实物佐证,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7000多年前先民在汤汤淇水边刀耕火种的情景。
3000多年前,淇水边巍然耸起了商朝的都城——沬邑(朝歌)。《史记·殷本纪》记载:“沬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仍都焉。”《笺本竹书纪年疏正》也记载道:“武乙三年,自殷迁河北,至是复济河北徙朝歌,纣仍都之。盖武乙之时,其地名沬,至纣时,其地乃名朝歌。《水经注》曰:‘朝歌城本沬邑。”用纪年来说,公元前1250年,商王武丁始迁沬邑;公元前1147年,武乙继都沬邑;公元前1101年,帝乙即位后改沬邑为朝歌。公元前1075年,帝辛即位后仍袭朝歌为都。武丁、武乙、帝乙、帝辛4代帝王在此演绎着商朝的故事,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创造了宝贵的甲骨文,制造了惊世的青铜器,托起了商朝的文明,照亮了商朝的天空。
高村的淇水关,是商朝大将黄飞虎镇守的重要关隘,也是商纣王都朝歌的第一道城墙,今遗址依稀可辨。因濒临淇水,村中沟壑纵横,故小桥遍布,有几十座之多。村旁,有一架在淇水上的古石桥,原名太平桥,明代成化十三年(1477年),由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王越(浚县人)奉旨修建。桥全长360余米,宽5.15米,桥墩、桥面全由青石建成。桥面每块青石长1.75米,宽50厘米,厚30厘米,青石间全部用浇铸铁水的铁燕尾连成一体。500多年过去,不知经受了多少次洪水的冲击,不知经受了多少次载重车辆的碾轧,古石桥虽老态龙钟,但仍然顽强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淇水关是古代的一条国道,也是御道。当年慈禧与光绪途经这里,正是洪水未退的初冬,因水势较大,古石桥已成了漫水桥。轿夫们面面相觑,不敢前行,生怕有所闪失,吃罪不起。慈禧看到此景,也担心自己掉到河里喂鱼,于是叫来知县问策。知县一听,让老佛爷尽管放心,这淇水关有许多好水手,让他们为老佛爷护驾,肯定万无一失。知县精心挑选了28名好水手分列御驾两侧,安全护送到达淇水对岸。
朝代更替,卫武公在朝歌插上了卫国的大旗。卫武公继位后,效法先祖卫康叔的政令,卫国百姓一直过着和睦安定的生活。《史记》记载:“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卫武公四十二年(公元前771年),被废黜太子与母亲申后暗中逃奔申国的姬宜臼(后为周平王),与姥爷申侯联合缯国和西夷犬戎进攻周幽王,攻陷西周首都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周幽王及其与美人褒姒所生的太子伯服均被杀死,美人褒姒也被犬戎掳走。姬宜臼被拥立为周平王。犬戎尝到了甜头,又不断进犯镐京。在这关键时刻,卫武公表现出了自己的大智大勇,他没有袖手旁观,没有保存实力按兵不动,而是以81岁的高龄率领精兵强将长途跋涉奔赴战场,与周平王等一齐杀退了犬戎,并与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以武力护送周平王把国都东迁到洛邑(今洛阳)。因卫武公功劳卓著,周平王命名他为公。周代有五等封爵制,即公、侯、伯、子、男。可见公是周天子之下的最高头衔了。据《国语》记载,卫武公95岁高寿的时候,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向全国发布通告说,不要看我离100岁只差5岁了,不要想着哄我开心,有什么意见还是要不讲情面地大胆提出来。就是坐车出行、晚上睡觉前,他也礼贤下士,请身边的工作人员提意见,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典范啊!
卫武公修康叔之政,高风亮节,鞠躬尽瘁,在位55年,使卫国人和政通。《诗经·卫风·淇奥》中对他作了如此赞美:“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歌以淇水边修长茂盛的绿竹起兴,不仅让我们能想象到他颀长的身材和帅气,还能够联想到君子内在的虚心有节的品行。不仅如此,这位君子的学问、品德、修养,都像精琢细磨过的玉器、骨器那样光亮、高雅。《毛诗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卫武公去世后,衛国人为他修建了武公祠和有斐亭,历代文人骚客留下了不少赞誉他的诗词。
著名的卫懿公虽好鹤误国,但他醒悟后与将士一起拼杀疆场,以至被砍成肉泥,不能不说是一种为国捐躯的悲壮。而卫大夫弘演见卫懿公血肉模糊,尸体不全,只有一只肝尚完好,于是拔刀剖腹,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了卫懿公的棺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赤胆忠心,不能不说是一种大义。朝歌人荆轲恰如弘演,也怀着一颗赤胆忠心,也怀着一种大义,他蘸着淇水磨亮匕首,启程去了燕国,在易水边唱出了千古流传的“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之歌。
鬼谷子云游到云梦山,本想躲避战国的硝烟,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们却先后追寻到此,拜师学艺,隐居的水帘洞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军校。毕业的弟子们壮志满怀,跃跃欲试,由此冲向硝烟,纵横捭阖,叱咤着战国风云。
“药王”孙思邈背着采药的背篓来到淇水边,又爬上五岩山,寻找、品尝着济世的草药,《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也因此厚重了许多。
“禹贡名山”大伾山的八丈大佛则巍然静坐在七丈楼中,笑看着滚滚红尘,给融入卫水的淇水送上永恒的微笑……
充满诗意的淇水
这是一条荡漾着历代诗歌的河流。
在《诗经》中,《邶风》《鄘风》《卫风》均描述了淇水两岸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喜怒哀乐,其中有39首提到了淇水,如“淇水滺滺,桧楫松舟”“淇水汤汤,渐车帷裳”“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爱国女诗人的许穆夫人。她是卫懿公的妹妹,生长在淇水岸边,自幼在淇水戏水、垂钓、荡舟,与淇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她在少女时代就深为祖国的安危而担忧。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通婚联姻是一种政治行动,带有亲善和结盟的性质。当齐国和许国都派使者到卫国向她求婚时,她毅然选择了强大而又邻近的齐国。她想将来卫国如遭到外敌入侵,就可借助齐国的力量救援。而许国弱小又遥远,远水不解近渴。她这种深谋远虑、将祖国安危与自己的婚姻连在一起的远见卓识和拳拳爱国之情,却因卫国与齐国曾有隔阂,而遭到了卫懿公的坚决反对。最终,卫懿公坚持将她许配给了许穆公。
远在异国他乡,她将对故国的思念都倾注到了《竹竿》和《泉水》两首诗中。当听到狄人攻打卫国、朝歌失陷、懿公被杀的消息时,悲痛欲绝。在许穆公不援助的情况下,许穆夫人毅然驾车北上,赋《载驰》向各国求救,终于收复了失地,使卫国得以复兴。《左传》曾记载:“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漕。”以诗歌救国,在古今中外的诗歌史上,恐怕是屈指可数的吧。
载入《诗经》的《竹竿》《泉水》《载驰》,植根于自己的国家,植根于悠悠的淇水,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描绘了故国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充分表达了许穆夫人思念故土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作为商朝古都和周王朝卫国国都的朝歌的母亲河,作为在《诗经》中荡漾着周代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史河”“文化河”,自然也吸引了历代的文人雅士,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骆宾王、岑参、高适、陈子昂、苏轼等诗人,他们或慕名而来游览,或寻古探幽,或探亲访友,或在此居住,留下了数万首与淇水有关的诗篇。千百年过去,李白的“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杜甫的“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王维的“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苏轼的“惟有长身六君子,猗猗犹得似淇园”……仍然在淇水的碧波上闪光。
2014年9月,中国诗歌学会在河南省鹤壁市举行“中国诗河”命名大会暨首届“中国诗河”征文活动,正式命名淇河为“中国诗河”,这是中国首个以诗歌命名的河流。这是诗歌与淇水又一次最亲密的拥抱。
绿色环保的淇水
如今的淇水虽没有《诗经》里那么丰满,但在淇水儿女的精心梳妆下,却不失灵秀亮丽的身姿,依然用清澈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两岸的子子孙孙;依然流动着厚重的历史;依然舞动着传奇的浪花;依然吟咏着历代的诗文;依然一路歌唱着,追寻自己的梦。
被称为“北方漓江”的淇河,水质常年保持在国家Ⅱ类以上的标准。河水清且涟漪,可见鱼翔浅底优美的舞姿。更令我惊叹的是,在淇河上游的盘石头水库中,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桃花水母,悠然自得,上下漂荡,犹如江南烟雨蒙蒙中撑着油纸伞、踩着高跟鞋的妙龄女子,身着旗袍,轻盈款款地向我走来。对水环境和水质的要求都远远高于其他鱼类的桃花水母,能畅游于此,可见淇河生态是多么的优良。你看,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黑鹳、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白天鹅和灰鹤等飞禽,也悠闲地在河边或湿地啄食、嬉戏,时而你唱一句我唱一句,或来个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
淇水的两鬓,被鹤壁儿女插满了红的花、白的花、黄的花、紫的花,如再细分一下,还有粉红、乳白、浅黄、淡紫……裙裾上绣着墨绿或浅绿或嫩绿的乔木、灌木和杨柳、松柏,以及桃、梨、杏、枣等果树。倏地,花香果香欢跳着向我袭来,似一双双纤纤细手抚摸着我的肺腑,兴奋着我的神经。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曾经茂盛在《诗经》里的绿竹,虽经汉武帝堵塞黄河决口,虽经东汉初河内太守寇恂大量砍伐制作兵器,让百万支箭镞子弹般地飞;如今,绿竹仍然茂盛。那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里,都藏着淇河儿女的爱,都藏着淇河儿女爽朗的笑声。
润泽诗苑的淇水
在鹤壁新区附近的淇水岸边,我走进了淇水诗苑——一条落成于2011年、长达3千米的诗歌长廊。它与淇水相依相偎,手牵着手,是那么亲密,俨然一对儿恋人。
淇水诗苑由历代文人骚客的1500多首与淇水有关的诗词组成。这是从数万首诗词中精选出的,从殷商时期箕子的《麦秀歌》《箕子操》开始,直至当代,无不洋溢着诗人对淇水的爱,无不寄寓着诗人的思想情感。
1500多首诗词,经本土书法家真草隶篆的挥毫,又经石雕艺人的精雕细刻,洋洋洒洒地呈现在一块块石碑上。所用的石料,有河南的青石、雪花白,也有福建、内蒙古的花岗岩,还有湖南、北京的汉白玉。所用的石雕工匠,既有本地的,也有来自河北曲阳、山东嘉祥等地的。诗作的美,书法的美,雕刻的美,挽着古老而又年轻漂亮的淇河,融合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底蕴深厚的风景线。
李白雕像坐落在诗词广场中央,他那饱览多地名山秀水的目光,望着近在咫尺的淇水,望着一个个雕塑小品——淇水边从《诗经》里走来浣纱洗衣的母女,从《氓》中走来“抱布贸丝”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携儿育女的淇河母亲,曾在朝歌屠牛、卖炒面、垂钓的姜太公……李白如果从石雕中走出,不知做何感想。
淇水诗苑不仅“种植”诗词歌赋,也“种植”舒心快乐。徜徉淇水诗苑,胜似漫步江南园林,绿竹沙沙、垂柳轻抚,淇水鸣琴、鸟鸣虫唱,若是明月高悬,观赏一壶映月,再引发诗兴诗情,登咏诗台即兴吟诵,更是心旷神怡,别有一番惬意在心头。
淇水诗苑也“种植”着一座城的梦想。从昔日的煤城蝶变成如今的诗城、绿城、美城,这是鹤壁多年的憧憬。
“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秋词》中的诗句,岂不正是今日鹤壁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