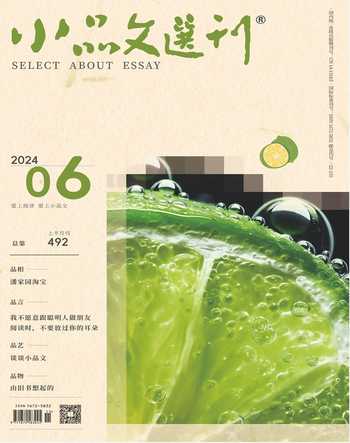登高
李汉荣
路渐渐陡起来,岩石上的苔藓愈来愈厚,由浅绿转入深蓝。向前一步,时间就退后一步,苔藓作证,腐殖土作证,合抱的古树作证我回到宋,回到唐,一座唐代的庙宇屹然于半山之上。檐上的鸟语平平仄仄,操着古时的方言,反复助诵的是谁的好诗?古碑有些倾斜,宇迹依然遒劲高古,棱角分明的笔画,让我读到了青铜的刀锋,和那紧握刻刀的手,那专注的近于虔诚和迷狂的眼神。他是把他的眼神刻在石头上面了,还有他的心跳和呼吸,以及那个黄昏的微风、树木的香气、落日缓慢移动的光线,都保存在这石头上了。那是千年前的黄昏啊。我抚摸这碑石,我是在抚摸一段石化的时间。一亿年前它是一块汉白玉石,一千年前它是一块汉白玉石,只是有了人的手迹,一千年甚或一万年后它仍是一块汉白玉石,我十分敬畏它了,我是石头面前的过客,我是文字面前的过客。
我看见云在高处向我招手,我看见云的马驰过来接我。不用了,我自己行走。云退回去,静静地卧于高处,卧成西天的净土,那么白,珲么坦荡,静穆中隐含着一种克制的激情,哦,白云生处,我梦中多次到达的地方。
汉白玉、花岗岩、玄武岩……石头、石头、石头,时间、时间、时间,我从浅山走入深山,我从低处走向高处,从今天走向古代,走两公元前,走向泥盆纪、震旦纪,走向壮丽的造山运动。石头围过来,时间围过来,我是时间中的时间。需要多少时间,才出现这个登临瞬间,让我在高处,浏览这么多的时间?
溪水越来越清澈,也越来越幼小,我来到那条大河的童年了,鱼都没有长大,听见我的声音就藏了,全是没有见过世面也不想见什么世面的孩子水之外的事物都与它们无关。水草更加茂密,灯芯草不准备点燃谁的灯盏,灵芝草也不懂得它有什么灵验,水仙花绝不知道自己就是水边的仙子——因为它们都没有名字,除了绿了又枯枯了又绿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它们没有别的建树,至于蜜蜂蜻蜓们的访问,它们一律欢迎,但绝不发出邀请。我坐在那潭水边,俯下身来,掬起一捧水,我不忍喝了它,这是那条大河的源头,我喝了它的源,那條河会不会降低流速减少流量呢?我看着清冽的水一点点从我的手指上漏出来,禁不住就想:我也是源头了,大河就在我手心里发源。
我继续攀援,苍岩更加苍老,或狰狞或慈祥或如飞狮或如卧虎,见多了沧海桑田高陵深谷的大世面,对我的到来一律平静得漠然,脚踩上去,青苔松软,让我体验到铁石心肠的时间,也有害羞的柔情。树木老得令人肃然起敬,想扑上去唤它几声祖父一一无奈它比祖父还要老上千年。有几颗老树在风中说话:唐朝的那些诗,宋朝的那些词,都是我看着写出来的,你嗅嗅那诗词里,是否有一种松香味、柏树味?不敢在树下呆下去,呆久了,我怕松树掩埋了我,我怕苔藓蔓上衣服,我怕松鼠们集体出动,把我抬走,藏进只有月光才能找见的地方。
路瘦得已容不下我很瘦的影子,影子就斜斜地印进深谷。我继续攀援,扶着远古的石头,抓一缕刚刚飘来的雾,擦擦汗湿的脸,正好几只鸟从头顶飞过,抛下几粒清朗的单词,循着它们的提示,抬起头来,我看见我此行的高点,我终于来到山巅:一些石头和一些石头,一些树和一些树,一些野花和更多的野花。蜜蜂先我而来,蝴蝶先我而来。天很蓝,水洗过的样子,女娲刚刚补好那么崭新的样子。极目远望,不知何处是终极,望久了,心也变得无际的宽广,心也渐渐蓝起来。天的蓝,心的蓝,蓝与蓝融为一体,心与天融为一体,不知有心,不知有天,天就是心,心就是天,也无心,也无天,只有无垠的澄明和宁静。
选自《与天地精神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