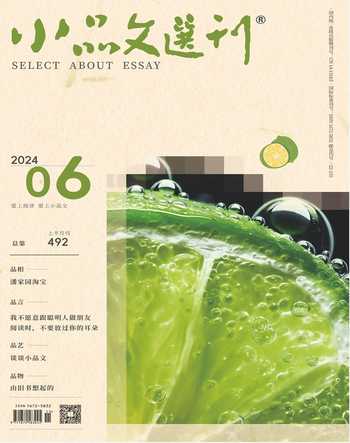阅读时,不要放过你的耳朵
毕飞宇
关于阅读,我至今是一个老派人物,还死硬。我坚持认为,坐下来,打开书,一手提笔、边读边记是最佳的阅读方式。阅读是容易产生快感的,快感来了,不管不顾,一口气冲到底,那个爽。我把这样的阅读叫作放纵式阅读,它的缺点是看得快、忘得更快。
如果手上有一支笔,它对阅读的速度就会有一个调整。笔的作用其实就是刹车的作用。你在书上划拉几下,再写上几个字,这样一来,阅读的速度就慢下来了,这样有助于理解,也有助于记忆。我和年轻人闲聊的时候时常发现这样一件事,当我们讨论到作品的某个细节时,他会这样说:“我没注意哎。”问题来了,这个细节你没有注意,那个细节你也没有注意,那你到底读到了什么呢?不客气地说,故事梗概而已。对待通俗小说,这样自然没有问题。但是,面对真正的文学,这里的遗漏就有点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恋爱了,一个月之后,你只知道女孩的身高和体重,那只能说,你不爱她。
前几天,我和余华一起做评委,我吃惊地发现,余华阅读的速度甚至比我还要慢,我高兴坏了。我一直以为,我读书慢是因为我的智商不够高,现在好了,我知道了,是我和余华有类似的好习惯。
事实上,我的阅读速度也算快,大部分时候,可以一目十行。但是,在阅读经典时,我甚至连一个词、一个字都不愿意放过。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知道字和词的意义,它们意义重大,它们是一个作家的终极,它们也许就是本质。在许多时候,把字和词错过了,就把整个作品错过了,甚至,把这个作家都错过了。
然而,我想说,无论我们是怎样好的读者,阅读都有它的局限。这个局限不是源自我们的能力,而是来自文字自身的属性。
文字的基本属性有两个:一个是“形”,这是供我们阅读用的,它作用于视力;文字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属性,那就是“音”,这是供我们说话用的,它取决于我们的听力。“形”和“音”并不构成彼此矛盾的关系,然而,出于生理的特征,我们在面对文字的时候很难兼顾。比方说,我们说话了,我们接受的是“音”,自然就会忽略文字的“形”;同样,在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自然专注于文字的“形”,很难体会文字的“音”。
举一个例子吧。在《雷雨》的第二幕里,有一段后母繁漪与长子周萍的对话。他们之间有不伦之恋。在剧本里,周萍说:“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繁漪说:“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
这一段文字我是上大学时读的,这两行“字”就那样从我的眼前滑过去了。但是,有一天,在剧场里,我的耳朵终于听到这两句台词的“音”了,我承认,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深为曹禺先生的才华所折服。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是周萍的狡诈。周萍想结束与后母的不伦之恋,他要用伦理与虚伪来压垮繁漪。
繁漪的声音充满愤懑之情,她想不到周萍会这样说。繁漪的声音也是对始乱终弃的控诉,是惊天的嘲讽与谩骂——你和你的老子是一路货,是彻底的绝望,是疯狂之前最后的克制,离泼妇骂街只有一步之遥——“你是你父亲的儿子”啊!
有一个问题是现实的,如果没有语言的“音”,我没有“听”,我真的能够“读懂”《雷雨》吗?我真的可以获得如此强烈的审美震撼吗?
事实上,在我们强调阅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做“自残”这样的傻事,我们不该放弃我们的耳朵。它不只是用来挂眼镜和戴口罩的。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该忽略文字的另一个属性。
阅读无比宝贵,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历史其实很短。在人类认知的历史长河中,“读”不是“听”的孪生兄弟,“读”是“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是重孙。在印刷术被发明之前,我们认知的历史是“口口相传”的历史,一句话,是“音”的历史,是“听”的历史。文学是这样,宗教是这样。西方的《荷马史诗》是这样,我们东方的“话本”也是这样——要不然,怎么会叫“话”本呢。
时代变了,但时代之变未必就是向前,有时候,它也向后。谁能想到科技的发展会如此这般?在我们使用视力即将抵达极限的时候,我们终于想起来了,我们还有耳朵呢。音频来了,“听”的时代訇然而至。人类的耳朵高兴坏了。它们骄傲,智慧在充血,耳朵在脑袋的两旁都翘起来了。
選自《北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