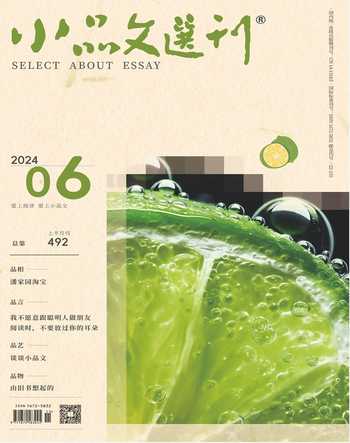阿背还乡
周伟
那天,我忽然接到湖南省作协的来电,说台湾作家代表团参加第七届两岸作家交流活动,赴湘西考察采风途经邵阳市洞口县,有一名台湾作家要趁此机会回乡祭祖。我赶忙安排女作家袁姣素约了专车在下高速的路口等候。车上下来的是台湾作家杨树清,一下车就念念有词:阿背,阿背,我们终于还乡了!听省作协的人介绍,这位叫杨树清的台湾作家,他的父亲叫杨国淇,“九·一八”事变后就从军了,征战了半生,后来去了台湾。
说起父亲,杨树清说个不停,他说父亲一生多舛,常常沉默寡言。退伍后的父亲后来成为老农,耕种番薯,闲暇时总爱坐在苦楝树下打盹,遥听来自对岸的广播,轻声唱着家乡的歌曲。楊树清最为难忘的是父亲的眼神,遥望对岸的家乡,父亲的眼神是那样的高远和悠长,一直越过海峡,很远很远。还在初中读书的杨树清,那年写父亲,写父亲的眼神,一篇《家在山那头》的作文发表于当时的《金门日报》。还记得性格内敛的父亲,从没提及家乡旧事。只是每逢过年或传统节日,父亲便带着他和哥哥朝着海的对岸磕头遥祭,对岸天地一色,一片模糊。
那时的金门、厦门两地隔绝往来,作为父亲那批的抗战老兵,思念家乡却又回不去的心路历程的苦,只有他们自己能懂。他们常常就着番薯酒,乡音呢喃,泪眼模糊。“泪已流尽,两岸无声。时间对老人越来越不利,让他们回家吧!”杨树清曾在他的作品《被遗忘的两岸边缘人》中这样写道。
后来,两岸开放,互通探亲。但由于父亲不识字,家乡口音浓重,家乡地址频繁变更,更是由于父亲离开大陆时,他的双亲、姐妹、弟弟已先后离世,就这样一直没有联系上。每次从大陆回来,杨树清看到父亲失望的眼神,他总是不忍面对。有一次,父亲嚅嚅地说:“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
。
”直到2000年,父亲在台湾去世,也终未踏上故土。杨树清跪倒在父亲的灵前,他向父亲起誓:一定要替父亲还乡,让阿背还乡。
甲午年的八月初一,杨树清回来了,他带着父亲回来了。父亲离开家乡83年的时光,时光如梭,父亲变成了他手中的一本书——《阿背》。父亲的小名叫阿背,杨树清的小说《阿背》写了父亲多舛的一生,也写尽了父亲的思乡情和乡愁曲。那天,我们一行仍然没有找到杨树清父亲的老家和他父亲的亲人。但杨树清认定是洞口县的高沙镇范围内的某一个村子。无奈之中,杨树清同我们驱车来到高沙镇的分界碑前,在那个标有“高沙镇”三个字的牌子下拜祭。没等大家愣过神来,杨树清扑通一声,长跪在地,口中念念有词。他点起香烛,倒满三杯金门高粱酒,摆上了父亲爱吃的番薯,焚烧起纸钱。
伴随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界碑附近的村庄更是显得出奇的安静,天上堆满了棉絮似的云朵。杨树清深深地跪在那里,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阿背》平铺开来,一页一页地撕开,每撕一页,就喊一声“阿背”。我就看到,一页一页的阿背,在火中飞舞,如梦如烟,如泣如诉。好久好久,我们几个人,陪在杨树清的旁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临走时,杨树清包了一小包父亲家乡的黄土,绝尘而去。烟尘已远,心还在这里。斯人已逝,魂魄终究回归故里。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记起杨树清那长跪在地、口中念叨“阿背阿背”的情景。于是,我在心里有了一个决断,一定要替阿背找到他的出生地和他的亲人。我们请杨树清从微信中发回他父亲的资料,把目光定在一个叫“曲塘”的地标,在整个邵阳市范围内查询,通过派出所的户籍室在网上查询。女作家袁姣素最为认真,又通过她的同学高沙镇三中的杨松军老师到高沙镇杨姓族谱里查找,半个多月,查阅了40多本族谱,终于理清了杨树清父亲的族谱脉络和关系,并且找到尚在人世的一些亲人,尽管他的直系亲属均已不在人世。
得到这些消息,我立即带了作协一行,热心的杨松军老师也带着高沙镇网站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起赴江口镇、高沙镇社山村、高沙镇洪茂村现场寻访,为杨树清父亲尚存在世的堂兄弟及表兄弟合影留念,并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的照片发到了杨树清的电子信箱。
在那个中秋月圆之夜,海峡那头的杨树清从微信上发来了一句话: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杨树清说,他将尽快成行,来探访父亲的故里。他说,他要再写一本《阿背还乡》,一本真正的阿背还乡!他还特约我和女作家袁姣素两人,联袂推出两岸三书,三乡之书。他说已联系好了出版社,并请有“诗魔”之称的大诗人洛夫为三本书题写书名。没有几天,就题好了,杨树清发回洛夫先生的毛笔题字。杨树清的长篇报告文学的书名是:阿背还乡;袁姣素的小说集的书名是:梦里水乡;我的散文集的书名是:大地无乡。
是啊,隔着水,隔着云,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遍拾乡愁,乡愁就是父亲的思念和宿愿。余光中先生的《乡愁》犹在耳边,好一曲深情而优美的恋歌。再读洛夫先生的《边界望乡》,还是那样的震撼:“鹧鸪以火发音/那冒烟的啼声/一句句/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
。”我在想,余光中、洛夫、郑愁予那一代乡愁诗人,是怀乡的一代,也是幸福的一代。他们用文字找到了乡愁的出口,找到了回家的路。而杨树清的父亲阿背,和杨树清父亲一样的抗战老兵“阿背”们呢?
选自《海口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