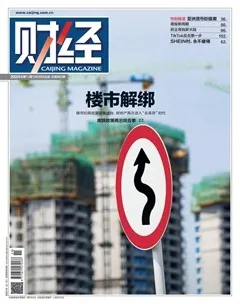宏观不稳定、应对危机与政策抉择
邓宇
现代经济和金融深度互嵌,全球经济互联,不稳定的经济常态随着周期演变而随时发生变化,地缘政治、科技革命以及气候变化加剧了这种不稳定,迫使危机从过去的间歇性爆发到逐渐走向“常态”,应对危机考验的政策抉择能力。
无论是美国“大萧条”还是上世纪70年代欧美“滞胀”危机,抑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20年全球新冠大流行,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频出,最终又演变为常态,危机时期的宏观政策退出颇为艰难,至今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正常化仍无法启动,而美国的超大幅度加息周期也难以尽快结束。似乎存在这样一个循环,应对危机时的宏观政策将为下一场危机的出现埋下风险隐患,由此形成了海曼·明斯基所描述的稳定与不稳定的经济。
可见,某种意义上拯救危机的过程也是制造危机的开始。《剧变》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提出,所谓的危机是必须做出重大抉择的紧要关头、转折点。危机的出现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化危为机、实现相对稳定。
但是,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料下一场危机的到来。而且危机早期,很难预测是超级火灾还是局部火灾。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在《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一书中发出灵魂拷问:我们有能力和信心应对下一场全球危机吗?本·伯南克等所著的《极速应对》在详细讨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过程时提出,鉴于危机演变的巨大不确定性,决策者应迅速采取行动,对冲不利的尾部风险。徐忠等新著《危机应对的道与术》一书重点聚焦危机处置与应对的核心问题,以美国“大萧条”等为例,从不同维度探讨危机时期的宏观政策选择,详细阐释财政危机、金融风险处置以及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存款保险公司的角色等。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的大规模“放水”以及激进加息何尝不是一场应对危机的试验,而日本央行应对危机的宏观政策则更加谨慎,也存在政策与市场博弈。
一、如何把握宏观层面的不稳定?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但是,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自身面临较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危机,处于逐渐衰退的趋势,大国博弈加剧,保守主义势力在欧美国家“沉渣泛起”,因而导致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思潮,经济、贸易、科技和金融等保护主义倾向日益突出,削弱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致使国际合作机制遭遇巨大阻力。
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一书中对未来国家竞争的图景做出了预测。康纳认为,全球化正在进入超级全球化阶段,传统上衡量一个国家的战略重要性的标准在于其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但数字时代的衡量标准已然不同以往,即在地理互联、经济互联、数字互联层面,是否深度参与全球资源、资本、数据、人才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流。
全球竞争格局已然发生新的变化。《多面全球化——国际发展的新格局》一书提出,全球化能让国家间联系更紧密,也能让国家间的矛盾更突出。如何把握宏观环境的不稳定?可见,全球化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全球政经格局的变迁出现新特征和新趋势,这就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更多不稳定性,以及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
究竟怎么应对这些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应对危机的宏观政策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虽然历史的叙事因国家和地区差异,以及国际环境的变迁而不尽相同,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作出的决策选择产生了巨大差异。贾雷德·戴蒙德在著作《剧变》中的案例分析和描述,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国际社会变迁的图景,有的国家成功化解了危机,有的则陷入了困境,遭遇失敗,其背后无不揭示出国家危机管理之道的重要性。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在其专著《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三角》中提出,面对深度衰退,最终贷款人必须迅速采取干预措施,并确保能够获得再融资来防止金融困难演变成一场能够引致“大萧条”的相互作用且不断累积的衰退。然而,这些干预也增加了成本,包括通胀的爆发,为防止出现“大萧条”而引发的不稳定也是其副作用。《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却对财政救助和公共债务提出质疑。在他看来,现在的政府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当时,可以说政府影响力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这就是为何如今的危机不仅是对市场缺陷的控诉,也是对政府作用的挑战。
二、财政与货币政策是否存在边界感?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体系框架的两大工具,对宏观经济运行,特别是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财政与货币的功能既有差异,也有互动,关键在于二者的定位。财政政策连接的一端是债务。美国人类学家、“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要参与者大卫·格雷伯在《债——5000年债务史》书中将债务置于货币的范畴。他提出,货币不仅使债务得以存在,而且货币和债务如影随形,一定同时出现,因此债务的历史就相当于货币的历史。调节财政的收支平衡所依赖的正是公共债务,而过高的公共债务显然无法持续。美国经济学者巴里·艾兴格林等联合出版的《全球公共债务:经验、危机与应对》,指出了公共债务的合法性问题。本书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妥善管理财政而让国家和后代背上无法偿还的债务,那么这个政府迟早会失去合法性。需要思考的是,财政刺激是否也有边界或限制,而不是无限地扩张。
通常意义上,中央银行被视为“最后贷款人”,这一特定角色意味着货币的权力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特殊职能,是其他金融部门所无法比拟的。但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也较多,显示出货币政策的复杂性。
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研究了1929年美国大萧条危机后认为,糟糕的货币政策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位学者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认为,上世纪20年代正是美联储扩张性的信用政策导致了大萧条的发生。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出版的《动荡时代》一书讨论了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变过程。白川方明认为,比起货币政策所关注的经济增长和通胀问题,金融稳定性也愈发重要,而货币政策本身的短期调节作用是难以取代长期政策的功能。应该看到,中央银行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而这意味着建设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应规范中央银行的职能,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同样也有边界。
三、究竟是随机应变还是长远谋划?
周期的观点具有深刻的启发性。知名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引言中归纳出三个重要历史周期: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美国橡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在《周期》一书通过总结自己50多年的投资经验,将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周期进行了系统性划分,给出了一个比较成体系的周期理论。那么,危机的爆发是否也具有周期性?例如经济周期、债务周期、科技产业周期等等,伴随其中的将是盛衰的循环。与其说是应对危机,不如说是通过宏观政策的抉择实现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
从乐观角度看,每逢重大危机,往往也是推动改革的机会窗口,这些不同类型的危机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过去国家财政或金融层面潜藏的风险隐患,或者监管的漏洞,危机的爆发则刺破了其中的“泡沫”;另一方面也倒逼财政体系重塑和货币政策框架更新,推动实现结构性改革。伯南克认为,消防员扑灭一场凶猛的火灾时通常会浪费大量的水,这是可以接受的。审慎和减少浪费的想法可能导致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使问题恶化。
历史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非具有前瞻性或高超的水平,即使在沃尔克时期也存在政策失误,而伯南克所引以为傲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并非完美无缺。亚当·图兹总结出的“多重危机”论认为,危机往往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交织所导致的。关于这一概念,马丁·沃尔夫持有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多重危机”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框架,来思考过去15年时间里发生了什么。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如果你以前曾成功地应对过几次不同类型的危机,那么你对解决新的危机会更有把握。读完本书,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应对危机的道和术究竟是什么?构建危机应对的常态机制需要长远谋划。“道”的角度或许更像是一种思维、理念和规律,“术”则倾向于方法和策略,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尊重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常识”的宏观政策虽然短期内颇为有效,却仍有可能催生出无法预知的严重后果,比如财政赤字货币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同样地,应对危机的宏观政策抉择既要相机行事,更要长远谋划,遵從制度规范,危机过后,更需要总结反思政策的有效性、局限性和持续性。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