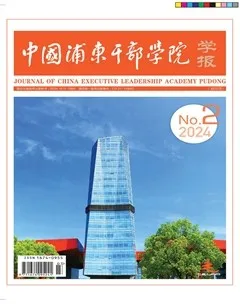反贫困视域下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比较研究
陈婷
摘 要:马克思与蒲鲁东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同时代人。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都是在回答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聚与贫困积累并存的问题中产生的。围绕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问题,马克思和蒲鲁东有着几十年的思想交往。但面对相同的时代课题,二人作出不同的理论解答。蒲鲁东早期对劳动者贫困现实的关注、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以及寻求解决现代贫困的努力,得到过马克思的肯定,但他们在对贫困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理解,所持的立场和方法论,以及对反贫困路径的选择等方面,存在根本的分歧。
关键词:马克思;蒲鲁东;现代贫困;反贫困;财产权;所有权;所有制;《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一生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有很多思想交集,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就是其中的一位。马克思与蒲鲁东分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创立者。社会主义首先是消除贫困的理论,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现象以及如何摆脱现代贫困,是他们所处时代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要面对的课题,因此认识上的一致、差异或对立都在所难免。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思想交往,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批判的思想交往和交往中的思想批判,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颇具代表性,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一、批判的思想交往和交往中的思想批判
19世纪40年代早期,马克思和蒲鲁东都对“物质利益”问题给予很大关注。此时的“物质利益”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普遍贫困化的问题。蒲鲁东出生于一个穷苦家庭,一直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他找到的反贫困的突破口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蒲鲁东的反贫困思想进入了正被“物质利益”问题所困扰的马克思的视野。
(一)马克思对《什么是所有权》的肯定性评价
马克思最早了解到蒲鲁东,是他在《莱茵报》工作时期。此时蒲鲁东主义已经是在工人群众中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学说之一。《莱茵报》作为一种自由报刊,是为适应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殊性质”而产生的。[1]363马克思通过亲身接触各种社会经济生活,毅然选择站在穷人一边。从他写作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为最底层的贫困群众发声。
从社会贫困的事实出发,蒲鲁东发起了对“贫困的根源”的追问,将贫困产生的原因归于私有财产,主张否定私有财产,鼓吹“特权的消灭、奴隶制的废止、权利的平等和法律主宰一切”。[2]40在1840年出版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提出了“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论断,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教条发起了挑战。虽然“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观点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由资产阶级活动家雅克·布里索提出,但蒲鲁东首次在理论上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论证。一直以来,国民经济学家在不作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就把私有财产视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确定不移的事实,“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3]256
1842年,马克思研读《什么是所有权》后,肯定蒲鲁东是“法国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什么是所有权》是一部“机智的著作”,同时认为对后者“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1]295该书也得到恩格斯的好评。1843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将《什么是所有权》称作“共产主义者用法文写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哲学意义的作品”,[4]583指出它在揭露私有制方面,在解剖资本主義政治经济方面,以及在揭露私有制导致贫困与道德沦丧方面,进行了较有分量的批判,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显示出了极大的智慧以及真正的科学研究精神,是把智慧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范例”。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也是“这本书中受到马克思赞扬的主要内容”。[5]105不过,马克思称赞蒲鲁东,主要是看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先锋作用,而这正是马克思本人将要从事的研究工作。
(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对蒲鲁东的“保护”
1844年4月,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总汇报》第5期发表埃德加尔·鲍威尔撰写的《蒲鲁东》一文,把蒲鲁东的理论解释成某种宗教信仰的东西而对之进行神学的批判。以此为契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展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保护蒲鲁东而反对《文学总汇报》的批判家,并提出自己的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来反对思辨”。[6]6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保留地表达了对蒲鲁东的欣赏,这主要是因为蒲鲁东对劳动群众利益的关注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想主义传统。
青年黑格尔派忽视法国社会主义的现实内容,单纯地将蒲鲁东理论的本质归结为各种教条式的抽象,认为蒲鲁东不懂得“自我意识”哲学,把公平的概念绝对化了。这种批判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真正触及蒲鲁东理论的最重要部分。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不能简单地把蒲鲁东的理论归结为抽象思辨的内容,青年黑格尔派不仅对其进行了错误的阐释,而且暴露了其“自我意识”哲学只是一种民主主义的平等原则的思辨式表达,并没有实际社会内容。和青年黑格尔派不同,蒲鲁东并不是天真地以为通过“纯粹理性的批判”就能够改造社会,而是关注社会的“物质利益”问题。蒲鲁东的“现实批判”相较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纯粹批判”来说,确实高明得多。
马克思同时也指明了蒲鲁东的缺陷和不足。马克思肯定了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有所贡献,但也指出了蒲鲁东对待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狭隘性。蒲鲁东批判私有制,但他的学说并没有摆脱私有制的影响,他的批判还受到政治经济学前提的支配。马克思这时已经认识到,要解决现实社会的贫穷困境,就要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首要任务就是揭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秘密。
(三)《哲学的贫困》的发表与“友谊的终结”
日本学者城塚登说:“马克思高度地评价了蒲鲁东的功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像世人常常误解的那样,把马克思的立场说成与蒲鲁东的立场完全相同。……虽然马克思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接受了种种宝贵的启发,但是,从根本的立场上说,他同他们始终存在分歧。”[7]104
1846年10月,蒲鲁东撰写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正式出版,并在法国和德国工人中散播。蒲鲁东理论的追随者还包括受马克思影响较深的俄国文学家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11月1日,安年柯夫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贫困的哲学》,认为这本书中有关经济学的部分写得还是很有分量的。其实,他写信的目的主要是想知道马克思对《贫困的哲学》的看法。12月28日,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回信中概述了自己对《贫困的哲学》的看法,并提出了原则性的批评意见,指出这本书是一本“很坏的书”。[8]4761847年,马克思用法文写成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并公开出版,对蒲鲁东学说进行了全面批判。不过,《哲学的贫困》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只印刷了800本,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在《哲学的贫困》面世之前,蒲鲁东就已经知道马克思在写作一部批判自己的著作,并“警告”马克思:“如果您要责打我,我是要报复的。”[9]151-152但当《哲学的贫困》于1847年7月出版后,蒲鲁东却保持了沉默。可能是马克思的批判击中了蒲鲁东的要害,所以蒲鲁东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批评作出实质性反驳。在这次公开论战后,马克思说道:“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10]31
(四)《资本论》写作阶段马克思视野中的蒲鲁东
在写作《资本论》时期,马克思继续关注蒲鲁东及蒲鲁东主义者的理论动向。例如,1857年1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蒲鲁东现在在巴黎出版一部‘经济学的圣经。我要破坏,我也要建设。如他所说的,第一部分他已在《贫困的哲学》中完成了。现在他要来为第二部分‘揭幕。……我这里有蒲鲁东的学生的一部新著作: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版。老一套。停止流通黄金和白银,或把一切商品像黄金和白银一样都变为交换工具。”[11]88-893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蒲鲁东的新的经济学著作①已经出了七版,我还没有看到。”[11]105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开篇,马克思主要针对蒲鲁东的经济范畴理论以及无息信贷理论,对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论银行改革》进行了批判,揭露了其想要通过银行改革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而保存这个制度本身的意图。意大利学者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批判“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整个蒲鲁东主义的论战”。[12]41
1859年6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问世,商品和货币理论在这里第一次得到详尽的论述。书中谈到蒲鲁东的地方共有七处,其中三处集中在第一篇的商品理论中。马克思主要批判了蒲鲁东对货币的错误理解,“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11]554这是继《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学所作的进一步深入批判。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对社会主义作了经济学的科学论证,也从根本上摧毁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865年1月19日,蒲鲁东去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施韦泽请求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一生作一个评价。马克思写了《论蒲鲁东》一文,对蒲鲁东的一生作了全面且客观的评价。
二、分析现代贫困的哲学方法论
马克思和蒲鲁东都承认,要正确地阐述現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需要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对此蒲鲁东与马克思存在交集,即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厘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路向。但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二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马克思没有采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而是用科学的方法论对现代贫困问题作出哲学阐释。
(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理解
1844—1845年间,马克思与蒲鲁东在巴黎相识,他把蒲鲁东看作法国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观点的差异,二人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论。对二人交往的这段历史,马克思曾在一封信中写道:“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10]30-31
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采用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发展公式。蒲鲁东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思想从一个观念前进到另一观念,通过一种更高级的观念而形成系列”。[13]629因此,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应当符合观念中的“系列”,因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只是适应观念顺序的一种发展。由此出发,他试图建立一种类似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系列辩证法”。对此,马克思曾评价道:“蒲鲁东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求实际上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因此,同黑格尔的密切关系在这里是实在的,而不是幻想的类似。所以,对于已经批评过黑格尔辩证法的人来说,要批评蒲鲁东的辩证法是不难的。”[14]627
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其辩证法,马克思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15]24马克思剥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和唯心主义外壳,把它改造成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唯物主义哲学,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是反映人类社会真实历史的辩证法。
(二)对现代贫困的哲学分析
蒲鲁东力图分析现代社会产生贫困的根源,然而,由于其哲学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他对现代贫困的分析仍然停留于理性层面。他用“系列辩证法”的逻辑,来阐释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蒲鲁东指出,把事物“有益的方面”和“有害的方面”并设之后,消灭有害的方面,保存有益的方面,通过矫正不符合系列秩序的阶段,使现实符合观念,便可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他用“系列辩证法”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剖析,由此建立起他的“经济矛盾体系”。在他眼里,现代贫困就是逻辑范畴各个环节的理性演绎。
在“经济矛盾体系”的演进中,最先出场的是分工,分工好的一面在于它使人与人之间地位和能力的平等得以实现,坏的一面在于它使一部分人陷于贫穷。为了从分工这一经济范畴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预先假设了现代工厂的存在,继而,“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16]241为了解决矛盾,分工的两个方面综合形成一个新的经济范畴即机器,于是坏的方面得以消除。机器好的方面在于它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增进了公众福利;机器坏的方面在于它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了失业。于是,又产生了竞争这一经济范畴,竞争从它的起源来看是“对公平的鼓励”,就其结果来看却又是不公平的。接着又产生了垄断,垄断既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又是制造贫困的主要原因。于是,蒲鲁东提出以国家和税收来规避垄断的坏处,并提到了“社会天才”。他写道:“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垄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者付给报酬。”[16]256然而,这样又会造成经济的倒退,破坏自由,最终瓦解社会。之后是贸易平衡、信贷、私有、共产主义、人口,以此类推……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这些范畴均不能解决贫困问题。
最后,为了自圆其说,蒲鲁东不得不求助于超个人的理性——神。在他看来,社会贫困不过是永恒不变的观念显现的历史。由此,蒲鲁东从先验的原则出发构建了一套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其实都是永恒理性派生出来的经济范畴,这些经济范畴是现实生活的动因。在蒲鲁东那里,不仅范畴是永恒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也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成为一种最合理的自然秩序。所以,自然而然,无产阶级贫困也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自然性的存在,现代贫困“完全出自天意”。可见,蒲鲁东表面上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其隐形逻辑前提却是在论证资本主义的超历史性。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用神学史观和天命论来解释现代贫困,这不过是用响亮的字眼、华丽的修辞来重述“事实”,并不能回答任何问题。马克思认为,对贫困的阐释应当从思辨的想象回到现实世界,从历史本身而不是在历史之外去寻找现代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社会历史和自然变迁不一样,不具有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形态,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同时也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的现代贫困也不会是永久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决然不是“普遍理性”的显现和安排,而是具有真实客观内容的历史发展,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秘钥在于理解人的实践。马克思以物质实践为出发点来阐释观念层面的东西,他不是把通过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那种关系看作由普遍理性从外部强加进来的东西,因为这些关系同桌子、麻布等物质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同样,现代贫困所反映的生产关系也是由人们生产出来的。因此,要使无产阶级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关键就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完全丧失”状态,“通过人的完全回复”[16]15来解放他们自己。
三、阐释现代贫困的政治经济根源
由于采取的哲学分析方法截然不同,二人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也截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马克思和蒲鲁东都认为,以“咒骂”的方式是不能回答贫困问题的,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作出分析和说明来回答。
(一)现代贫困的核心:所有权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本质和根源,只有在经济规律被认识之后才能被正确地揭示出来,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所有权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社会财富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虽然,蒲鲁东和马克思都把握到了分析资本主义的关键,但和蒲鲁东不同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批判范式是出于历史的缘由而不是逻辑的缘由。所以,不论是在出发点还是在观点内容上,二人都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17]42在他的成名作《什么是所有权》中,所有权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在《贫困的哲学》中,他将其作为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所有权“是一个特别的逻辑问题,它的解决关系到人类、社会和世界的命运。因为所有权问题是真确性问题的另一种形式,所有权就是人类,所有权就是上帝,所有权就是一切”。[13]652他指出,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困境在于,社会经济生活鼓励的自由交换,却在事实上造成了贫困以及不平等,“产生贫困、犯罪、叛乱和战争的原因是地位的不平等;而地位的不平等则是所有权的产物”。[2]265于是,被以往经济学家们看作最神圣的东西的所有权,在蒲鲁东这里却是最应该加以批判的。为此,蒲鲁东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所有制,实现“个人占有”的社会。在他的“占有理论”中,私有财产将由以平等的小占有形式出现的公有财产代替,在平等交换产品的条件下,社会财富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中,这样就可以消除私有制的祸害,消除社会贫困的根源。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蒲鲁东对于所有权的关注与讨论,尽管存在根本缺陷,但不可断言其毫无新意、毫无价值。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作出了批判性的考察,并抓住了所有权的核心。他察觉到了所谓的天然的财产所有权其实是反社会性的,是处于社会之外的一种东西,而这恰恰与社会性的劳动相矛盾,这正是属于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这是蒲鲁东的进步之处。但是,蒲鲁东对所有权的把握,始终停留在抽象法权的基础上,并未真正进入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关系。蒲鲁东其实并不是要取消私有财产,他仍然主张保留私有制的各种经济范畴,他反对的只是财产的绝对所有权形式,因为它使得个人权利同社会权利发生对立。他没有看到,整个私有制就是人类关系的物化,因而也是人的非人化的原因。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否定私有财产,他的“占有理论”只是想让社会所有成员都成为私有者,使一切人都成为资本家。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科尔纽说:“蒲鲁东本人没有从私有制去推求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根本没有把私有制看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祸害,因而也就沒有要求用激进的方法来废除私有制。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这就是蒲鲁东的学说的缺陷。”[18]355
马克思指出,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就要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产生的贫困的原因,从根本上需要到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去寻找。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过程是由劳动者来完成的,劳动产品是由劳动者创造的,而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却属于资本家。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他们虽然是财富的创造者,却成了社会上最贫困的人。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从这一事实出发,致力于发财致富的科学,却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一事实。马克思指出,在国民经济学家眼中天然合理的私有制,是必须要消灭的。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祛除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消灭建立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剥削基础上的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变成社会公共财产,充分释放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未来社会的所有权形式必将是社会所有制,社会化占有的所有权形式将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实现直接结合,劳动者可以普遍地、自由地、平等地支配生产资料,从而为摆脱贫困并实现自身发展创造条件。
(二)蒲鲁东对贫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蒲鲁东说,要治好贫穷这种“慢性病”,就必须彻底否定政治经济学这种制造贫困的理论。他说:“贫穷分成各种各类,形式繁多,构成一部完整的自然史,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已搜集到的一切事实中,可以得出一个不容置辩的结论,就是:只要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存在一天,贫穷就是社会的一种器质性慢性病,只有彻底否定政治经济学,才能结束这种对抗。”[19]155蒲鲁东以政治经济学这一棱镜透视现代贫困,以他构建的“经济矛盾体系”来描述现实经济生活,阐明不平等交换以及现代贫困的根源,并提出了构成价值理论。
蒲鲁东认为,社会是由鲁滨逊之类的隐逸之士组成的,人们所需要的绝大多数东西原本并不是自然界所供给的,而是通过工业生产出来的。按照蒲鲁东的说法,正是由于生产者“建议”另一个生产者的分工和交换,交换价值得以产生,正因为有了这种“建议”,交换世界得以形成,价值也就出现了。继而,蒲鲁东对价值的矛盾性进行了研究。他说,从性质上来讲,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互相排斥,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因为随着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价值会越来越低,反过来随着生产的产品的减少,价值会越来越高。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蒲鲁东将使用价值看作一种自然發生的现象即“众多”和“供给”,将交换价值看作“稀少”和“需求”。为了使这一矛盾性体现得更加明显,蒲鲁东说:“只要我是自由的买者,我就是我的需要的判断者,是物品是否合适的判断者,是对这件物品愿意出价多少的判断者;另一方面,只要你是自由的生产者,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资料的主人,你可以缩减你的成本。所以专断的意志必然要渗透到价值中去,并且使价值在效用与议价之间摇摆。”[19]81随即,蒲鲁东换了一种新的术语,即用效用来表示使用价值和供给,因为供给提供效用;用意见来表示交换价值和需求,因为意见提供对商品价值的意见。因此,形成了效用(使用价值、供给)与意见(交换价值、需求)的矛盾。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对立其实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的。在交换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自由的购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决定其愿意提供的价格,“自由的生产者”为了能达到产品价格与成本差额的最大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决定自己的生产费用,由于价格是自由的交换双方任意估定的,那么,双方的矛盾就产生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性就体现在这里。
价值二重性的矛盾该如何解决?按照“蒲鲁东式的三段论”发展公式,正题就是使用价值,反题就是交换价值,合题就是构成价值。所谓构成价值,指的就是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构成价值体现为“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20]102简单来说,这种比例性关系,即以同等的劳动小时交换同等的劳动小时,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劳动时数生产的产品购买到包含等量劳动的任何产品,这样的商品交换才是平等的。如果商品交换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那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自然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不公平交换现象就会消失,社会公平就可以实现。为此,蒲鲁东主张取消现存货币,设立“劳动货币”,把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变成货币一样的等价物,直接以劳动时间来表示货币,产品同产品都能互相交换,从而达到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消除商品生产的矛盾。
针对市场中出现的生产过剩现象,蒲鲁东把它说成是工人无法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对此蒲鲁东解释道:根本原因就在于生息资本的存在,借贷资本家通过借出自己的货币来获得利息,从而造成了物价上涨。“出售帽子的制帽业主……得到了帽子的价值,不多也不少。但借贷资本家……不仅一个不少地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他得到的,比这个资本,比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东西多;他除了这个资本还得到利息。”[21]584蒲鲁东指出,工人的工资加上资本的利息,形成了商品的价格,而这个价格是高于工人工资的,因此,工人想要买回他生产的产品,就成为一种不可能。也就是说,受资本利息的支配,工人虽然自食其力却仍然贫穷。可见,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在蒲鲁东这里,仅仅被看作放贷者对贷款人和劳动生产者的剥削。他认为,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等于它的成本价格,也就是等于它生产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加上工资,那么,商品就是按照价值出售了,剥削也就不存在了。对此,马克思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道:蒲鲁东只听到了“钟声响”,却不知道“钟声”到底从何处来。[22]412
(三)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与超越
1851年8月,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指出,从表面上看,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具有了一种比较有血有肉的形式”,[23]353但究其本质而言,在对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解释上,蒲鲁东事实上并未作出新的论证。蒲鲁东论证了构成价值是交换中的比例性关系,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比例性关系按照生产商品所用的劳动时间进行平等交换,从而达到供求平衡。马克思指出,这恰恰是把事情弄颠倒了。实际的情况是,当供给和需求处于平衡的状态时,商品中的必要劳动量正好决定了商品的相对价值,也就是说,这种相对价值恰好表现了蒲鲁东所企求的比例性关系。但蒲鲁东却把事情倒转过来,认为只要先将供需的比例性关系建立起来,先用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么生产和消费就会互相平衡。对于这种倒因为果的行为,马克思以一个比喻作出评价:“一般人都这样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大家出去散步。”[20]102-103而且,使用价值不能简单地与众多、供给画等号,交换价值也不能简单地与稀少、需求画等号,因为供给者同时也是需求者,需求者同时也是供给者。所以,蒲鲁东的做法仍只是停留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上,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实际上,蒲鲁东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价值”区分开来,他没有弄清楚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的劳动价值这两种衡量方法的差别,而是错误地用“劳动价值”①来衡量商品的价值,没有看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规定,而“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20]100如果按照蒲鲁东的说法,那么结论自然就是:生产工资需要的劳动量决定了工人能拿到多少工资,生产劳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了劳动作为一种商品的价值,这个劳动时间也就是维持劳动者及其后代的生命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工资的最低额度。所以,劳动者注定会“遭受现代奴役”,[20]95注定会陷入贫穷。这与现存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社会的不平等分配是相一致的。可见,蒲鲁东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站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马克思第一次严格地区分了劳动力和劳动。他指出:“谁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15]196在商品交换市场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劳动力。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和一般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不同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够生产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一般商品却只能创造等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从表面上来看,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且付给工人工资,这一交换行为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但是,事实上,在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多出的这一部分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出现,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于是剥削就产生了。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将剥削根源归结于生息资本的观点,全然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生息资本的性质和特点。借贷资本家把他的资本贷放给产业资本家时,所有权没有被出让,看起来既不表示买,也不表示卖。但实际上,这个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通过循环过程,又以增值了的货币形式回到了产业资本家手中。但因为资本支出时不是归他所有,所以流回时必须把它归还给贷出者。可见,生息资本的全部运动形式,不过是通过贷出一定时期的货币,然后将这个货币同货币的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蒲魯东当然没有发现这一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建立在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就尽可能地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使工人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构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15]707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既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贫困生产和积累的过程,剩余价值生产得越多,贫困程度也就越深。
四、消除贫困的“社会主义”方案
虽然蒲鲁东和马克思都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来阐释贫困问题与未来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的根本不同,二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消除贫困的“社会主义”方案。
(一)蒲鲁东消除现代贫困的方案
蒲鲁东说:“今天,在文明世界的一切事件中,贫穷是大家最为了解的。人们差不多已经明白它从何而来,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的,它的代价有多大;人们也已经计算出在不同文明程度下贫穷所占的比重如何;与此同时,人们也已经相信,截至目前,一切用以救治贫穷的灵丹妙药都了无成效。”[19]155于是,蒲鲁东提出了他自己的贫穷解决方案。他认为,从出发点来说,共产制和私有制的意图都是好的,然而,它们所造成的结果却是坏的。因为共产制违背了独立和相称的原则,私有制违背了平等和公正的原则。所以,蒲鲁东想要从共产制和私有制之间找出一个“合题”,建立一个既能实现独立性和相称性,也能实现平等性和公正性的社会。蒲鲁东把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形式叫作“自由”。所谓“自由”,就是不受任何行动影响的,因而能够接受任何好的或坏的、有益的或有害的决定的一种力量、机能或自发性,“自由”的完美程度取决于它符合理性规律的程度。
在新的社会形式下,国家与权威将会被充分保证个人自由的社会组织所取代,这样的社会组织是作为“人们的公仆”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人们的主人”而存在,从而达到自由和秩序的完美结合。蒲鲁东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发现并建立一个保证个体自由和独立的有秩序的平等国家,寻找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那么,怎样实现无政府社会呢?蒲鲁东坚决反对一切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因为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具备真实的政治能力。同时他也反对任何政党的领导。他非常崇拜自发性,认为“一切的革命……都是靠着人民的自发性完成的”。[24]229他把人民的自发性建立在神秘主义的基础之上,把被压迫群众的自发性说成是某种神秘的和出于天意的力量。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25]325可见,蒲鲁东的批判非常迎合资产阶级的口味,他所主张的东西,不过“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23]360
在未来社会的结构上,蒲鲁东主张依靠自然力的均衡维系,通过经济联合,把社会上被剥削的财富归还给社会,建立“自由社会”。“自由社会”是一个工商业自由发展,个人财产能够得到保护,由工人共同负责企业盈亏的社会,它建立在个人占有的互助制原则基础之上。蒲鲁东深信,社会是为生产而不是为政治而组织起来的,有一种以互相交换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存在,只要不受国家行为或垄断制度的干扰,这种自然经济就能保证利益得到平衡。蒲鲁东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以全体劳动者的名义所要求的,是相互原则、公平交换和信贷组织。”[26]206要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剥削和贫困问题,只能通过互助主义来解决,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将是被他称为“互助社系统”的模式。这是一种全人类性质的自由大同,其基础正是利他式、互助式的个人自由。新社会将采用会计核算方法,建立一个社会账簿,精确地确定盈亏状况,以便随时看出社会究竟有秩序还是无秩序,并报告衡量的结果。账簿中使用的术语不再是商品、资金等会计学术语,而是上帝、公有制、公民等哲学、法律、政治术语。蒲鲁东想通过建立为个人提供无息信贷的“人民银行”实现这一点。
(二)马克思对蒲鲁东理论实质的揭露
马克思指出:“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而他们自己愈是厉害地叫喊‘社会科学,就愈加陷入贫穷和愚昧的统治之下,他们简直太可笑了。”[27]224马克思把蒲鲁东称为“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者、经济学者”,[28]805把他的理论定性为“政治冷淡主义”,并写作《政治冷淡主义》一文对他所代表的政治冷淡主义进行全面清算。
马克思曾对小资产阶级作过一个概括:小资产者“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29]20这个特点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在政治、宗教、科学、艺术、道德上也是这样。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决定了它既迷恋资产阶级的奢华生活,又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既希望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又不想要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弊端;既想改善无产阶级的贫困生活,又惧怕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总之,小资产阶级从来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它或者同资产阶级联合,或者同无产阶级联合,它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法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即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一定的思想文化產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从蒲鲁东的出身及经历来看,他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者。他的理论无法超越小资产者的生活界限,而集中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和经济愿望。
对于蒲鲁东来说,无产阶级缺乏头脑和思想,是社会中的低能儿,而这正是无产阶级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所以蒲鲁东寄希望于小资产阶级,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和解。从本质上而言,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因为他认为一切政治运动不仅无效,而且非法。马克思则认为,无产阶级才是反贫困的主体,是变革现存社会、建立新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这个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只有消灭现代社会的一切反人性条件,才能捍卫自身。阶级斗争是每一个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筑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被压迫阶级想要将自己从贫困处境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使得现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再相容,就必须消灭现存的生产关系。而无产阶级作为最强大的生产力,就肩负着这一历史使命。
(三)马克思消除现代贫困的方案
马克思不仅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消除贫困方案的改良主义实质,彻底驳倒了蒲鲁东,而且实现了对蒲鲁东的全面超越,提出了科学的消除现代贫困的方案。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贫困并不是自然偶发意义上的贫困,而是由社会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导致的必然性问题。“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16]67因此,唯有变革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造,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彻底的决裂,建立一种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直接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现代贫困。
不可否认,在消灭国家这个社会主义的最后共同体形式上,马克思与蒲鲁东是有共通之处的。列宁曾说道:“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30]50二人都认为,国家是一切祸害的根源,是造成贫困的“帮凶”,所以,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消灭国家。不同的是,蒲鲁东想要破坏现有的国家形式,立即消灭国家;而马克思则强调,国家将在共产主义阶段自行消亡,在此之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非常必要的,而无产阶级之所以还需要国家,是为了镇压自己的阶级敌人,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不仅肩负着按照人民大众的利益改造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任务,而且还必须用好专政的职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阶段,接下来就是无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的阶段。国家将由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服从于社会的机关;公共机关将失去其政治性质,只具有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权力将真正地回归社会,为社会服务,为人民造福。
马克思指出,消灭贫困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实现自由劳动和共同富裕,自由劳动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与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相对应,而社会财富的创造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因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14]507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连消除贫困的可能性都没有。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飞速发展视为社会历史的一种进步,尽管这种进步伴随着血腥和残忍。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在几百年中创造的财富数倍于此前整个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和积累的财富,为消除贫困准备了必要物质基础。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再也容纳不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时,炸毁旧制度的物质条件就成熟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再受资本的束缚,社会分裂以及贫富矛盾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消失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将充分涌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31]222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全体人民可以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来共同分享发展成果,所有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真正成为自由且全面发展的人。
五、结 语
现代贫困问题是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共同关注点,二人都致力于思考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但就对现代贫困问题的研究而言,二人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均存在根本的不同。要真正找到消除现代贫困的现实道路,不仅需要科学的哲学方法论,还需要对贫困产生的政治经济根源作出科学合理的说明,并实现二者的科学结合。在理解现代贫困的哲学方法论上,二人都“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模拟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所谓的“系列辩证法”,将对现代贫困的理解放置到了一个唯心主义的天命框架之内。马克思则不同,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与改造,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将对现代贫困的理解放置到了唯物主义的现实框架之内。在阐释现代贫困的政治经济根源时,二人都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尽管蒲鲁东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认为想要改变社会的贫困现象,就必须消灭所有权,建立所谓的“个人占有”的相对所有权,并在价值矛盾性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构成价值理论。然而,他的理论存在根本的缺陷和矛盾。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改造,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出发,科学揭示了现代贫困以及剩余价值的产生根源。在消除现代贫困的路径上,二人提出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方案。蒲鲁东从其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建立一个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共产主义的“第三种社会形式”的调和主义学说。而马克思则从阶级对立的现实出发,立足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制度变革、生产实践以及价值目标上提出了消除贫困的科学方案。
通过比较二人在现代贫困问题上的哲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阐释以及“社会主义”方案,可以清楚地看到蒲鲁东贫困理论的局限性及其危害性,也可以更清晰地把握马克思贫困理论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在对蒲鲁东的揭示与批判中,马克思科学阐释了现代贫困问题的本质、根源以及消除贫困的路径和方向,实现了对蒲鲁东的根本性超越。总的来说,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与超越是涉及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全方位批判与超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M].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4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6]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M].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Selected Writings of Pierre-Josept Proudhon[M].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ewart Edwards,Translated by Elizabeth Fraser.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196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3][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M].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8][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M].王以铸,刘丕坤,杨静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19][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M].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4][法]加罗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M].刘若水,惊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2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M].何瑞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8]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0]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孙小帆]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rx and Proudhon from the Anti-Poverty Perspective
CHEN Ting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Police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Marx and Proudhon were contemporaries of capit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In a certain sense, both Marxism and Proudhonism emerged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wealth and poverty accumul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Marx and Proudhon had decades of idea exchanges around the issu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Faced with the same issue of the times, they came up with different theoretical answers. Proudhons early attention to the poverty reality among labors, his criticism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his efforts to seek solutions to modern poverty were recognized by Marx. However,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oots of poverty, their stances and methodologies, and their choices of anti-poverty path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Key Words: Marx; Proudhon; modern poverty; anti-poverty; property rights; ownership; system of ownership;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