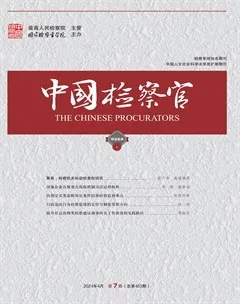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地方经验、困境与优化
张海燕 王明才 陈沫冰

摘 要:涉农检察公益诉讼存在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脱节的现象。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检察院的涉农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为制度研究提供了良好样本,其覆盖农村生态监督全程、突出农业生产监督重点与构建涉农类案监督机制的实践经验值得总结推广。与此同时,涉农检察公益诉讼暴露出案件线索来源渠道单一、案件办理资源供给不足与案件范圍扩展效果有限等现实困境,有必要运用系统化思维,通过多元主体参与、人才科技赋能与内外联动发力等途径实现制度优化。
关键词:涉农检察公益诉讼 “三农”问题 寿光经验
一、问题的提出
“三农”问题始终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近年来,涉农检察公益诉讼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涉农检察公益诉讼指检察机关以关涉农村地区公共利益的案件为对象,以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督促起诉、直接起诉等方式切实履行公益保护职责,最终形成的包括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在内的制度集合。
目前,涉农检察公益诉讼尚属新生事物,现有研究成果缺乏专门性研讨,对于具体检察实践的全面检视尤其罕见,进而造成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脱节。本文拟以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寿光市院”)的涉农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为例,凝练总结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全面把握阻碍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并尝试探索制度优化路径,以期为强化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效能提供智识贡献。
二、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寿光经验
寿光市院依托本地区农业农村治理模式,在拓展监督范围、锚定监督重点、打造监督机制等方面为全国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样板经验。
(一)因地制宜覆盖农村生态监督全程
寿光市院充分关注本地区农业发展的上、中、下游产业公益保护事项,以此为核心向周边领域探索推进,2020-2023年间办理涉农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情况如表所示。
一方面,推进涉农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适用多元化。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等方式为涉农公益提供全方位保障。另一方面,推进案件范围产业相关化。根据农业发展涉及到的前端产权保护、中端农业生产、后端销售三大环节,将监督对象充分覆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领域、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安全生产领域及其他相关领域。
(二)专项治理突出农业生产监督重点
如何在扩大公益保护范围的同时实现精准监督是涉农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面临的一大难题。寿光市院针对涉农公益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治理短板,以“小专项”为抓手,面向其中普遍性强、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重点问题开展专项行动。如上表所示,寿光市院重点关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020-2023年间,办理案件55件,有效助力乡村人居环境的常态化、规范化改善。
(三)协同联动构建涉农类案监督机制
我国涉农检察公益诉讼较强的职权主义能动性难以统合主观诉讼权利救济与客观诉讼秩序公益之间的差异性需求,需落实回应型检察公益诉讼思维[1],建构协同联动的类案监督机制。
寿光市院坚持以个案促类案,努力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如在办理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案件中,关注案件共性问题并批量制发检察建议,同时推动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出台《寿光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实施方案》,形成类案监督、源头治理的规模效应。
三、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现实困境
以寿光市院代表所开展的涉农检察公益诉讼在服务农业农村发展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案件线索来源、案件办理资源、案件扩展范围等方面仍面临现实困境。
(一)案件线索来源渠道单一
目前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线索收集方式主要有三类:基于刑事案件获取案件线索、基于自身开展的法律监督发现案件线索以及基于检举控告发现案件线索。首先,检察机关既是公共利益代表,也是“技术性当事人”,诉讼主体、权利主体处于分离状态[2],其距离公共利益受侵害事实较远,问题线索来源受限。其次,在开展法律监督工作中,受两法衔接平台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的现实掣肘,案件线索极为有限。最后,社会公众对涉农检察公益诉讼认知有限,基于检举控告而发现的案件线索较少。
(二)案件办理资源供给不足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检察监督的重点聚焦于刑事检察,对于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资源供给显著不足。
一方面,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高素质办案人员供给不足。其一,检察公益诉讼起步较晚,未能从业务人员能力提升层面实现同步供给。其二,涉农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多种类型,对办案人员提出了非法学领域的知识储备要求,专业知识的欠缺势必导致办案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办案经费供给不足。在开展涉农检察公益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需负担调查收集证据、鉴定评估等多项费用,办案成本高昂,客观上造成检察机关选择性办案的无奈局面。
(三)案件范围扩展效果有限
目前,涉农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存在单点集中的结构失衡困境,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及食品安全等传统类型案件为主,其他领域案件相对较少。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涉农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有限。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采“列举+等”式规定,受限于对“等”范围之理解,监督重点聚焦于有法律明文规定且难度相对较小的领域,“等”外领域受案范围探索力度有待提升。[3]其二,协调对接机制深化不足。检察公益诉讼既存在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制度性张力,又面临着法律监督刚性不足的问题,检察机关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与行政机关、相关组织和个人沟通衔接不畅的问题,案件范围扩展受阻。
四、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化路径
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化应当以困境破解为核心,秉持系统化思维,促进系统内部完善与外部交流。
(一)多元主体参与拓宽线索来源渠道
保护“三农”利益并非检察机关一家之事,涉及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相关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案件线索来源渠道的拓宽需要上述主体的广泛参与。
1.依靠群众增加案件来源。一方面,可考虑开展公益诉讼下乡活动,针对相关案件开展宣讲,提升群众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探索建立农村地区“网格员+公益诉讼”合作配合机制,聘任网格员担任公益监督员,激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
2.通过对相关行政机关的常态化监督发现案件来源。检察机关可以在农业农村相关行政机关常设派驻检察室、检察官联络室[4],推动建设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机制,拓宽监督线索来源,通过专题调研、实地走访等形式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二)人才科技赋能补足资源供给短板
针对办案资源供给不足之现象,既要重视专门性人才培养,又要运用数字技术为检察公益诉讼赋能。
1.完善“办案+培训+研究”的实战培训模式。组织人员定期对各项政策、法律法规等予以讲解,梳理办案过程中遇到的普遍困惑,对涉农疑难问题开展专题研讨;加强多元主体联动,深挖专业办案能手和业务专家,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与行政机关开展联合业务培训、双向交流活动,拓宽办案视野。
2.检察公益诉讼部门主动对接检察技术部门,建立协作机制。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资源供给不足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信息生产力”寻找替代性解决方案,为案件办理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在调查收集证据方面,运用无人机航拍取证等技术全面收集案件资料并及時固定证据。在检验鉴定方面,运用实验器材对涉案土壤、水体、污染物等进行鉴定,作为认定侵权事实的证据。在数据分析方面,以数据建模、模型应用为牵引,对调查取证内容进行数据化分析,实现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智能化、信息化。
(三)内外联动促进案件范围扩展
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扩展既要求内部案件受理范围的拓展延伸,又要求外部协调机制的持续深化,内外联动方能助力困境破解。
1.拓宽涉农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受理范围。除传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农业食品药品安全及农村安全生产等问题,“三农”领域还涉及占用破坏农用地、违法建设农田、侵占挪用涉农资金等问题,要求检察机关拓宽对涉农公共利益的理解范围,延伸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司法保护触角。
2.深化涉农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协同机制建设。诉前程序是各方主体进行直接沟通的机制,一定程度上具有司法命令和合同交融的性质。[5]检察机关应当继续以府检联动机制建设为切入点,完善健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线索移送、结果反馈等沟通协作机制,督促行政机关主动履职,增强涉农检察公益诉讼的权威性与制度刚性。
*山东大学交叉法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66237]
**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四级高级检察官[262700]
***山东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66237]
[1] 参见邓炜辉、于福涛:《回应型治理:检察公益诉讼治理模式的祛魅与重构》,《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8期。
[2] 参见李成、赵维刚:《困境与突破:行政公益诉讼线索发现机制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3] 参见杨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行政公益诉讼现状检视及路径优化——基于全国423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法律研究》集刊2023年第1卷。
[4] 参见张春明:《创新派驻检察监督机制》,《法治日报》2018年12月26日。
[5] 参见刘艺:《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检察公益诉讼》,《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