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
斯丽娟 辛雅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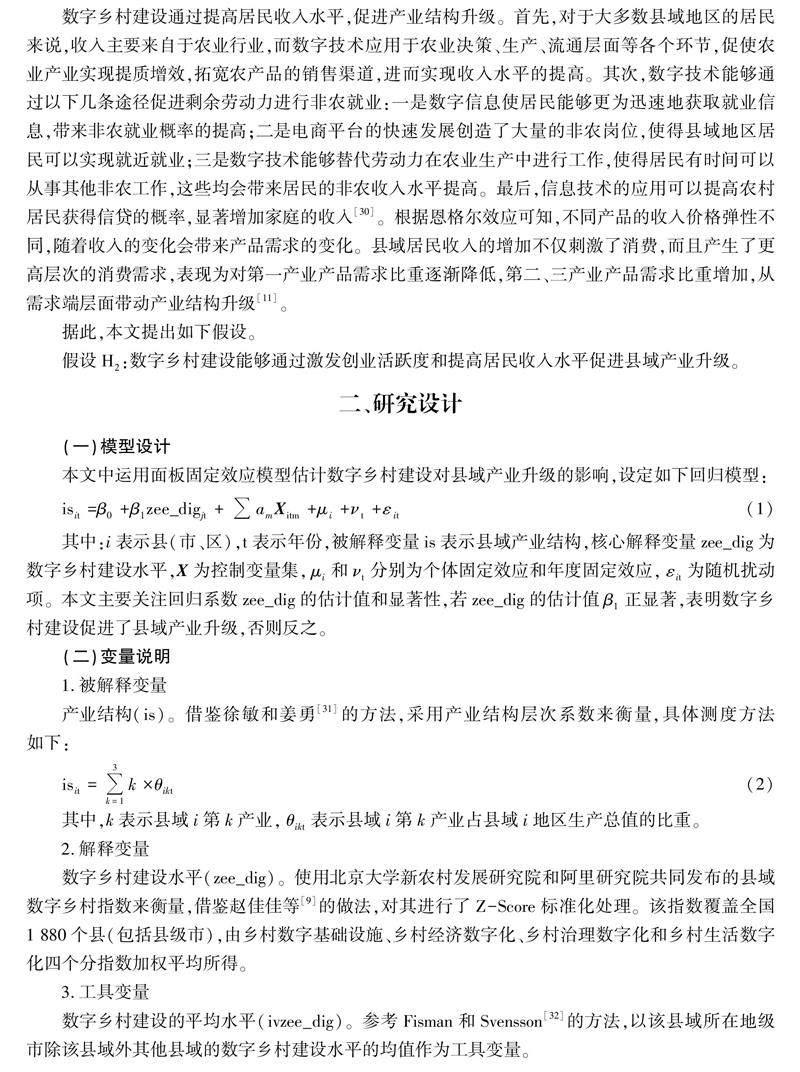


摘要: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功能完整、运行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在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下,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低的水平,存在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传统工业与农业、数字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等多重掣肘。县域产业升级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合理的技术应用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县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会影响县域产业升级,通过何种渠道来影响,这种影响效应又是否会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由于变量度量指标、样本观测期、理论基础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县级层面相关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2018—2020年涵盖中国1 09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总效应,并进一步开展了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效应讨论。实证结果表明: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在进行内生性问题、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和收入水平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东北、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综合以上结果,文章提出了继续推动县域地区数字建设水平和数字应用水平、加强县域居民数字素养的培养、激发数字乡村建设的就业促进效应、发挥数字技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等政策建议。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科学且直观地衡量县域数字建设水平,以县域这一更加细微的尺度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丰富现有研究,为政府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指导。
关键词:数字乡村建设;县域产业升级;创业活跃度;居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3.0;F49;F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24)02-0001-15
引言
作为我国经济功能完整、运行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县域主要由乡镇和农村组成,县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88%,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2.8%,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38.51%( 数据来源:《县域高质量发展年度指数报告(2022年)》。)。县域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輕重[1],其发展速度和质量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县域产业升级的结构红利能够使县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2],而合理的技术应用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3],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县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中的应用,2018年,中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标志着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开始。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2020—2021年,连续发布《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关于公布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等,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进一步推进。2022年,中央网信办等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以及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数字乡村建设政策体系基本上已较为完善。就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近几年来全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2021年已达到39.1%( 数据来源:《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数字乡村赋能县域产业结构处于即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蓄势阶段。因此,在充分把握数字乡村建设这一战略红利的导向下,进一步明晰数字乡村建设在县域产业升级的理论机理,有助于数字技术带来的技术红利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发挥,为推动县域数字化转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乡村建设即是通过推进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提高农民的信息素养,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的过程。数字乡村建设作为重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路径,是推动县域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对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测量,学术界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评价体系,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采用单一维度的指标来衡量,如农民手机拥有量、农村宽带接入用户量等[4]。二是构建多重维度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刘传明等构建了包含乡村环境、农村数字化、农业数字化和农民智慧化四个方面的数字乡村指标体系[5]。林育妙等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服务水平、数字资金投入四个方面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指标体系[6]。张鸿等分宏观环境、基础设施支持、信息环境、政务环境及应用环境等五大维度对数字乡村进行了测度[7]。Li和Wen从制度、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方面综合考虑,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指标体系[8]。但是上述指标构建均停留在省级层面,随着研究视角的细化,有学者采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测度的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进行衡量[9],具体包括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指数、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四个一级指标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到的数字乡村总指数。也有学者基于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维度来综合评估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应数字基础条件和数字乡村治理水平[10]。三是选取相关政策来进行评估,如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数字乡村试点县等政策实施作为表征数字乡村建设的代理变量[11-12]。
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最新研究主要从宏观经济层面和微观主体层面展开。其中,在宏观经济层面,林育妙等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得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和技术创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6];雷泽奎等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转移,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转变,进一步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13]。在微观主体方面,学者们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带来农民消费总量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4,14-15],并且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增收效应和信贷约束缓解效应[16]。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总体水平的提升意味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有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数字乡村带来了整体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17],进一步通过比较不同组别农户的增收效果,得出数字乡村的建设会扩大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结论[18]。而有学者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如潘锡泉基于浙江省山区26个县域,得出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结论[19];林海等以革命老区为研究样本,将数字乡村建设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维度,发现作为硬环境维度的数字基础条件会拉大革命老区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作为数字乡村建设软环境维度的数字乡村治理则缩小革命老区城乡间的收入差距[10]。也有学者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的福利效应,认为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增加收入、促进非农就业和加强乡村治理增进居民的幸福感[20]。此外,赵佳佳等基于2018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匹配数据发现,数字乡村通过促进信息利用、缓解信贷约束、增强风险承担意愿以及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影响农民创业决策,促使农民创业概率得到提升[9]。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会影响产业升级,已有文献关注较少。陶涛等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视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得出该政策的实施促使县域产业结构的转型,主要通过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和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实现[11]。Wang等基于2018—2021年16个省622个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不显著[12]。
虽然现有文献直接讨论了二者的关系,但仍存在以下的不足:第一,现有研究以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的实施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代理变量来探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电子商务仅仅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一部分内容,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数字乡村建设政策实施水平;第二,已有研究未能准确地推断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所使用数据差异、模型内生性等问题导致所得结果并不稳健,未能清晰地展示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且,从经济行为的角度来说,已有结论似乎与经济现实存在偏离。
据此,本文以2018—2020年中国县域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和县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运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更为科学、合理地对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进行衡量;第二,本文基于县级层面的数据,从更加细微的尺度了解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并采取工具变量的方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分别从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居民创业活跃度、县域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探讨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且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结构影响的区域异质性,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方向。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升级
伴随着数字乡村的建设,数字化技术和理念不断渗透到县域产业内,引发相关产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数字化改造。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第一,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创新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就生产方式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数据资源成为新的要素禀赋,重塑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结构,创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21],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县域经济的农村性这一特点使得农业成为县域产业发展的专攻方向,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能够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例如:遥感监测、精准作业、水肥药智能管理等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的应用,能够摆脱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困境,使得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22],带来农业产业的优化。就销售方式而言,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产品销售模式存在的环节多、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将供给方和需求方直接连接起来,降低流通和交易成本,加快产品的流通速度,同时产品的交易规模也有所扩大,从而推动传统产业的发展,使其产业竞争力增强。
第二,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产业融合实现产业升级。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要素资源配置边界不断拓展,在赋能县域农业产业化的同时推动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例如:数字技术带来的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不仅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率,而且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创新性和强渗透性的特点使其较为容易地与其他关联产业融合在一起,带来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形成,充分挖掘县域地区资源的潜在价值,进一步释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23],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出现诸如“云观赏”“云体验”“云购物”等智慧乡村旅游新模式以及休闲农业、共享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民宿经济等新业态[24]。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县域产业升级。
(二)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县域产业升级的机制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多数研究认为创业意愿的形成受到创业者个人特质和创业环境的影响[25]。基于个人特质视角,数字乡村建设会提高县域居民的现代化信息技能水平,他们能够通过数字信息平台进行创业知识技能的学习,了解创业的风险控制,进一步提高自身综合能力。另外,数字信息技术也会加强创业成功产生的示范效应,激发居民的创业思维。基于创业环境视角,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拓宽了县域地区居民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降低了信息搜索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使其可以更高效地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动向,进而确定创业的方向。并且,居民也能够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对创业决策进行评估,进而增加创业的成功率[26]。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和传统金融的结合,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和传统金融业务模式,增强了县域地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缓解了居民创业资金需求的约束,进而促進其创业想法的落实[27]。新创的企业往往具有高技术性和强创新倾向的特点,相较于市场中原有的企业存在明显的竞争优势,能够快速占领市场份额。新创企业的进入,对于较为落后的企业而言,可能会直接导致其退出市场,进而引致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逐渐流向新兴的部门,促使新产业发展壮大,进而推动产业升级[28];对于表现较好的企业而言,为了保持自身的市场占有度,会对自身进行升级改造,进而促进原有产业实现优化升级[29]。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首先,对于大多数县域地区的居民来说,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行业,而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决策、生产、流通层面等各个环节,促使农业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进而实现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次,数字技术能够通过以下几条途径促进剩余劳动力进行非农就业:一是数字信息使居民能够更为迅速地获取就业信息,带来非农就业概率的提高;二是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岗位,使得县域地区居民可以实现就近就业;三是数字技术能够替代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进行工作,使得居民有时间可以从事其他非农工作,这些均会带来居民的非农收入水平提高。最后,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农村居民获得信贷的概率,显著增加家庭的收入[30]。根据恩格尔效应可知,不同产品的收入价格弹性不同,随着收入的变化会带来产品需求的变化。县域居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刺激了消费,而且产生了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表现为对第一产业产品需求比重逐渐降低,第二、三产业产品需求比重增加,从需求端层面带动产业结构升级[11]。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县域产业升级。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本文中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i表示县(市、区),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is表示县域产业结构,核心解释变量zee_dig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X为控制变量集,μi和νt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主要关注回归系数zee_dig的估计值和显著性,若zee_dig的估计值β1正显著,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县域产业升级,否则反之。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is)。借鉴徐敏和姜勇[31]的方法,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衡量,具体测度方法如下:
其中,k表示县域i第k产业,θikt表示县域i第k产业占县域i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2.解释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zee_dig)。使用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来衡量,借鉴赵佳佳等[9]的做法,对其进行了Z-Score标准化处理。该指数覆盖全国1 880个县(包括县级市),由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分指数加权平均所得。
3.工具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的平均水平(ivzee_dig)。参考Fisman和Svensson[32]的方法,以该县域所在地级市除该县域外其他县域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4.机制变量
县域创业活跃度(entre)。借鉴谢绚丽等[33]的方法,采用县域地区当前企业注册数目和年末总人口比值的对数来衡量。
居民收入水平(income)。选取以2018年为基期平减后各县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对数来衡量。
5.控制变量
考虑到县域层面的其他因素可能对产业结构带来潜在影响,本文中也选取了一系列县域层面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2018年为基期平减后的人均GDP对数值表示。人口水平,采取年末总人口的对数来衡量。政府支出水平,采用县域公共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教育水平,采用普通中学在校生数量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借鉴林海等[10]的方法,采用县域公路总长度和县域面积的比值来衡量。由于目前缺少县域公路长度的数据,本文中将各县行政区域面积与所属地级市城区面积的比值作为权重,与地市级层面的公路总长度相结合得到县级层面的公路数据。
变量的定义见表1。
(三)样本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数字乡村指数数据来源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2020)》,产业结构和其他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本文中由于剔除掉了存在较多缺失值的县(市),最后获得了1 094个县(市)的样本数据。另外,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中对模型中的所有连续变量在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样本中产业结构最大值和最小值较为接近,说明数据的变化不太明显。从数字乡村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二者差距较为明显,表明不同地区间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差距较大,为异质性检验提供了证据。此外,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4.38,这一数值低于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在对式(1)进行回归之前,先进行了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相关结果见表3。
表3第(1)列与第(2)列为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情况下,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与第(4)列为同时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数字乡村建设的估计系数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验证了假设H1。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政府支出水平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为负向,这与储德银和建克成[34]的结论保持一致,可能是由于县域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非生产性支出占比过高,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
(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反向因果和测量误差等问题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可能会内生于某些不可观测的变量,进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会越多,进而反过来影响数字乡村建设进程。此外,数字乡村指数的数据可能存在测量误差,由于本文所使用指数的基础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阿里集团,存在一些县域地区因应用其他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导致数字乡村指数水平被低估,有偏于真实情况。
2.替换被解释变量
基于此,本文中采用数字乡村建设的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这一做法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同一地级市内各县域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都高度相关,符合相关性的设定;二是,同一地级市的其他县域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對该县域的产业升级并不会产生影响,符合外生性设定。表4报告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在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数字乡村建设会促进县域产业升级的事实,并且变量回归系数的值更大,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实际上更强。
本文通过改变产业结构的度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干春晖等[35]的研究,运用各县域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回归结果见表5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3.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考虑到数字乡村建设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中采取数字乡村建设滞后一期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的第(3)列和第(4)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当期的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促进下一期的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4.剔除特殊样本
考虑到在验证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结构影响效应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政策的干扰,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中对其他相似政策进行了控制。与数字乡村建设相类似的政策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实施,截至2018年,国家一共支持了1 010个示范县。据此,本文中剔除了属于电子商务示范县的样本,回归结果见表6的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说明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另外,由于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以及杭州市作为数字金融建设的先行者导致其数字化水平会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并且数字乡村的基础数据来源于阿里集团,可能会造成研究的偏差,因此,本文剔除了属于以上城市的样本,回归结果见表6的第(3)列和第(4)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与基准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保持一致,证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三)理论机制
前文提出,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通过提升县域居民创业活跃度和提高收入水平影响县域产业结构。因此,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对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县域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Mit=γ0+γ1zee_digjt+∑amxitm+μi+νt+εit(3)
其中,M为机制变量,衡量创业活跃度和收入水平。模型其他变量与参数说明同式(1)。
回归结果见表7所示。就创业活跃度而言,数字乡村建设与创业活跃度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且在10%的统计意义上显著,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升能够带来县域创业环境的改善和居民个人综合能力的提升,有效激发创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并且促使创业项目的落实,进而提高原来产业的竞争力度,淘汰产能落后的企业,使得闲置资源能够流入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就居民收入而言,可以看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改善了县域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促使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从需求端作用于不同产业的商品,倒逼产业升级转型。
(四)异质性分析
为了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差異,本文中将样本县域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分别对其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8所示。可以看出,东、中、西、东北地区这四组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1%、5%、1%的水平上显著且均为正,符合前文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分别为0.008 1、0.026 7、0.016 9和0.189 7,说明不同区域之间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其中,数字技术发挥的后发优势在东北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弱。究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本身具有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所产生边际效应相对于优化空间较大的中、西、东北地区来说要小得多。
四、结论与政策
(一)研究结论
产业的升级转型离不开新技术的应用,数字乡村建设给县域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8—2020年我国县级面板数据,在对数字乡村建设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其异质性。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在进行内生性问题、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政策的推进,通过将数据要素嵌入传统的要素结构,创新了原有产业生产、分配等方式,弱化了产业间的边界,加速了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赋能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收入水平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改善个人特质和创业环境,实现居民创业能力的提高以及创业想法的产生与落实,而创业企业的问世能够增强企业间的竞争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提升传统产业的价值、促进非农就业以及增加县域居民的收入来源,带来县域居民收入水平的改善,基于需求端倒逼县域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从异质性结果来看,数字乡村建设对东北部县域地区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中、西部次之,而对东部县域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小。主要可能是东部县域地区的产业发展较为合理且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引致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边际贡献相对于各方面落后的中、西、东北部地区来说较小。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应继续深入推动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不断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加快县域范围内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缩小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打造良好的数字技术发展环境。结合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区域各县域的实际情况,增强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外部资源的接纳能力,全面促成数字技术与县域产业的深入融合,不仅体现在改良传统产业发展模式上,更是能够推动产业形态创新,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激发县域产业的活力。
第二,政府应在县域地区加大数字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居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鼓励居民以数字技术作为支撑进行创业,提高创业成功率,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新元素,促进产业间的竞争,实现冗余资源的高效利用。此外,政府也应持续加强数字技术在县域地区的就业带动效应,增加非农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市场中劳动力的流动性,将一部分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解放出来流入第二、三产业,实现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从需求端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
第三,重视数字乡村建设赋能效果的差异,缩小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要发挥东部地区对中、西、东北地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通过与中、西、东北共建数字产业园区、共享数字信息平台等手段,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帮助中、西、东北地区进行数字化转型;同时,中、西、东北地区要加快补齐数字基础设施的短板,以便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后发优势,实现县域产业振兴。
参考文献:
[1] 黄祖辉,宋文豪,叶春辉,等.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22(1):24-43.
[2] 毛丰付,潘加顺.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J].中国工业经济,2012(10):32-44.
[3] PENEDER M.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3,14(4):427-448.
[4] 汪亚楠,王海成.数字乡村对农村居民网购的影响效应[J].中国流通经济,2021(7):9-18.
[5] 刘传明,马青山,孙淑惠.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J].区域经济评论,2023(5):26-35.
[6] 林育妙,程秋旺,许安心.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2012—2020年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3(4):101-111.
[7] 张鸿,杜凯文,靳兵艳.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评价研究[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1):51-60.
[8] LI Y L,WEN X.Regional uneven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A case study of China[J].PLoS One,2023,18(7):e0287672.
[9] 赵佳佳,魏娟,刘天军.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3(5):61-80.
[10] 林海,赵路犇,胡雅淇.数字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推动革命老区共同富裕[J].中国农村经济,2023(5):81-102.
[11] 陶涛,樊凯欣,朱子阳.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中国流通经济,2022(5):3-13.
[12] WANG P P,LI C Z,HUANG C H.The impa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Evidence from China[J].Agriculture,2023,13(10):1917.
[13] 雷泽奎,祁春节,王刘坤.数字乡村建设能驱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吗?[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54-66.
[14] 李宣蓉,范静.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2(18):50-52.
[15] 程伟.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7):12-16.
[16] 赵佳佳,孙晓琳,苏岚岚.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14-132.
[17] 齐文浩,李明杰,李景波.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收入增长: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农民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16-125,148.
[18] 尹含,孙伯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林业经济,2023(7):40-59.
[19] 潘锡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23(8):39-45.
[20] XIE Y Q,LIU H.The 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EB/OL].Preprints 2023, 2023052132. DOI:10.20944/preprints202305.2132.v1.
[21] 斯丽娟.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理论与改革,2023(2):73-85,150-151.
[22] 王胜,余娜,付锐.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J].改革,2021(4):45-59.
[23] 江晓军.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与路径[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68-75.
[24] 斯丽娟,曹昊煜.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65-174.
[25] SAMILA S,SORENSON O.Venture capital,entrepreneurship,and economic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1,93(1):338-349.
[26] 周广肃,樊纲.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创业选择: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J].经济评论,2018(5):134-147.
[27] 宋冬林,田广辉,徐英东.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38-51.
[28] 冯伟,李嘉佳.企业家精神与产业升级:基于经济增长原动力的视角[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6):29-42.
[29] 陈晓通,陈颖,李强.创业活跃度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我国省份数据的经验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1(18):176-178.
[30] MA W L,QIU H G,RAHUT D B.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Do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contribute to credit access and income growth in rural China?[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23,27(3):1421-1444.
[31] 徐敏,姜勇.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3):3-21.
[32] FISMAN R,SVENSSON J.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Firm level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3(1):63-75.
[33]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4):1557-1580.
[34] 储德银,建克成.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4(2):80-91.
[35]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31.
The impa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county-level industries
SI Lijuan, XIN Yaru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P. R. China)
Abstract: As the basic spatial unit of Chinas economy with complete economic functions and independent operation, count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Currently, most county-level economies in China are still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facing multiple constraints such as heavy reliance o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and inadequat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Upgrading county-level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unty-level development. In this background,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whether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will impact the upgrading of county-level industries, through which channels it will influence, and whether these effects will vary due to different levels of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hold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However,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county-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due to differences in variabl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sample observation period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We match the county-level digital rural index data jointly released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New Rural Development and Alibaba Research Institute with relevant data in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It ultimately obtains panel data covering 1094 counties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8 to 2020. By employing a panel fixed-effects model, it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level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ity effec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ire sample,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en after conducting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endogeneity issues, replacement of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excluding special samples, this result keeps the same as the baseline.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county-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enhancing resident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nd incom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northeast and central regions of China.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e article proposes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level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ounty-level areas,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county residents, stimulating the employment-promoting effects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c regions.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article lies in the use of the county-level digital rural index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scientifically and intuitively.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t a finer scale of counties, it enriches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counties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county-level industrial upgrad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resident income
(責任编辑 傅旭东)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低碳发展对中国西北地区经济格局的影响效应研究”(72373060)
作者简介:斯丽娟(通信作者),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silj@lzu.edu.cn;辛雅儒,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