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曲》作请柬的无限期

我耿耿于怀很久,你到底有没有听懂舒曼的《梦幻曲》。
对,就是那首,2 分钟而已,由水色的序曲、微凉的旋律以及虫鸣打断的间奏组成,在最后一道小节线后,我擅作主张地在这浪漫诗句里加了一个来不及晴朗的、比西瓜最甜那口还要迷人的结局。
所以宋曜闻,你听懂了吗?
1 /
那个时候,我正准备出国学小提琴,语言和签证都准备好了,却在申请手续上出了问题。我看着其他朋友相继离开,在琴房闷了一周后终于倦怠,几近崩溃。
于是回了我的老家,这个我爸从14 岁坐着老客车离开后,就只出现在我睡前故事里的乡下。
笼罩在夏夜山村里的月光像梦里的水,凉风剥落漫天星斗,吹成人间的萤火虫,带上了纤薄的草木露水的清香,经过连绵的西瓜地“沙沙”作响。

我挽着裤腿在西瓜地里学着逛超市时卖水果阿姨的动作,弯着手指挨个地敲,曾经被老师夸赞的、我引以为豪的绝对音准也成了眼下挑西瓜的天赋。可惜我同它们不熟,在瓜藤遍野里钻来钻去只分辨得出声音的差别,却并不知道究竟是落在高音域里的那个丰沛,还是低音域里的这个更甜。
然后你出现了,吓了我一跳。
你带着你家那条大狼狗,穿着个宽大的T恤短裤,既不大喊捉贼把我反手拿下,也不面露凶色逼我就地伏法,只站在瓜地旁边一动不动,像艺术展区角落里的雕像,让我感觉你仿佛正义凛然又尽职尽责地在替欲行不轨的我这种小偷行为放风。
后来我去看了《少年的你》,忽然觉得小北站在陈念前面的样子和你当时特别像。
别自恋,我不是说你们一样好看,只是他保护了陈念,而你从那刻,也拉住了我。
2 /
手电筒的光强烈,被你朝上卡在两块石头之间,如同地球作粉丝为宇宙应援,如同光束作鲜花送给璀璨星辰。
我借着光,吃你从自家地里挑出来的西瓜,在深夜十二点。
你坐在我旁边,摸着那条伸着舌头的大狼狗的头,问我为什么不睡觉。
我回,失眠,睡不着。
我对外一直宣称是申请手续出了问题,但其实收到的邮件却并非如此。确切地说,是我申请的那所奥地利音乐学府依旧在考虑我是否适合去深造。
我深爱着小提琴,也获过足够分量的奖状,可理想学院的犹豫让我敏感的神经在深夜里从最开始的难以置信到消磨信心后的自我怀疑,甚至开始贬低自己。看,我沈萱居然也要靠撒谎强撑面子了。
我咽下最后一口西瓜汁说,太晚了,你回去吧。
西瓜水分很高,月光亮堂堂的,它们都挤在我眼里。我指甲抠着绿白色的西瓜皮,强忍着不要像在琴房的每一个深夜一样哭个不停。
你没走,也没说话,从兜里摸出来一瓶花露水,把我的手拨开,涂在了我挠得红肿的蚊子包上。
我从来没觉得花露水这么好闻,像不加多余修饰音的和弦,纠缠着困意,让我安眠于这么多天来第一个好觉。
月色和雪色之间,有人是别人的第三种绝色。
而得失取舍里,你是带来平静自若的温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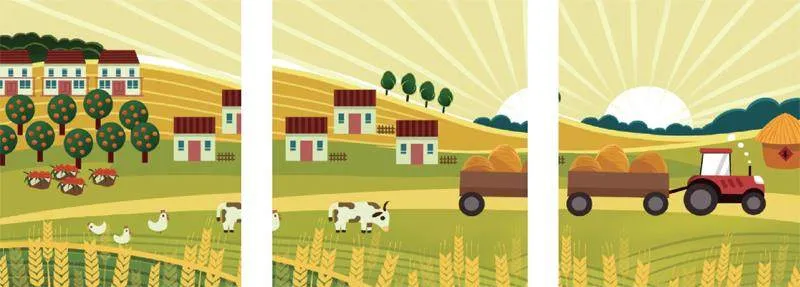
3 /
第二天一早你去上学,我问寄住的村民家里那个咬着包子的小孩儿你们学校在哪儿,他指给我不远处竖了旗杆的三层砖楼。简单漆色、空旷的操场里有斑驳的篮球架,校园的边际连接庄稼,要是想逃课,连栏杆也不用翻。
我蹑手蹑脚一层一层地摸索。中年英语老师一板一眼教带着口音的国民名句“Fine,thank you”,惨遭抽查的调皮男生即便有后排“狼狈为奸”的同伙也背不出《逍遥游》,写例题的粉笔在黑板上留下一半痕迹一半掉成了扑簌簌的粉末儿,板槽突然接住一截折断的粉笔头。
我很少能感受到这么磕磕绊绊又轻松自由的课堂,不由得在读书声里放慢了脚步,而刚踩上二楼最后一个台阶就被意外打破了这气氛,只听见从背后传来的中气十足的一声吼:“你是哪个班的?怎么不上课?”
时至夏日,没空调的乡间中学一间间教室都大敞着门,穿堂风跟着声音四通八达地传开。镜头好像突然被拉慢,后边是要来抓我的政教主任,窗户里是被惊动的众人目光。我在慌乱里张望,一眼撞进你抬起的眸色。
高三(1)班。
众目睽睽下我还有工夫记得这个。
4 /
最后,当然是你来救的我。
你站出来以哥哥的身份认领我,向那个政教主任用方言解释了一通,我听不懂,无聊地往你教室里打量,很巧地看见一个女生盯着你发呆,而在察觉了我的注视后低下头羞红了脸。
有趣。
你突然拉了拉我,说主任问我为什么不上学了。我猜你天生不会撒谎,不然随便一个理由也能搪塞过去。既然如此,我也变得诚实,我说我是学音乐的,还没开学。
停了两秒,我笑了笑说,不然等下课,我表演给你们听呀。
看热闹的同学这下也热闹起来,政教主任和老师维持了秩序,你回到座位坐好。我真的取了小提琴来,坐在小白楼正对着的主席台上。
铃声响起,我在你们学校几百人面前拉出绵长的定音,然后是欢快的变奏。
天光正好,蝉鸣在交替的节拍里起落,这首本该在琴房里被吸音板消融的百年前的《梦幻曲》现在被在窗子里挤作一团,探着脑袋的陌生朋友们听到。按错弦也没关系,随便改也没关系,我的感情不是舒曼,而是我自己,是此时此刻什么也不想的纯粹灵魂。
弓子离开时,我的头发被风吹得卷在琴弦里。有人鼓掌,有人好奇,但我都不在乎。这不是我在比赛时致分数、致名次,也不是我在晚会里致观众、致镜头,我致的是昨晚明亮的月光,致清甜的果汁。
致你,我的“哥哥”,你大概不知道,这是我从失眠的第一夜后,第一次重新把琴垫上肩。
5 /
夜凉如水,你带了一个在井里冰过的西瓜来找我。很多故事里的西瓜都是这样的,而我也终于亲口吃到文字里描述的“沁凉”味道。我翻起旧账,问你今天为什么没出来听。
你只大口地咬瓜瓤不说话,我也不急,捡起琴盒里的松香擦弓弦。
空白没有恶意,但你却坐立不安起来,半晌后吞吞吐吐地承认你在教室里听了。
我还在找你麻烦,笑着问你听出什么了。
这其实是没什么标准答案的问题,而且对你来说又太超纲,我本来没指望你给出什么答案,你却认真地看着我的小提琴语气颇郑重地说,好听,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
我问那你要不要试一试的时候,你的表现好像一幕喜剧,站起来就跑走,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向你表白。过了会儿,你又回来,我看着你宽大T恤上的水痕才知道大概是跑去洗手了。
我教你握弓的姿势,调整你下巴颏卡着琴身的角度,用西瓜藤拨你手指指导你按下去的位置。你屏息凝神,终于拉出了第一个音。
怎么说呢?我向打造这把小提琴的木头道歉,向这把小提琴演奏过的所有曲谱道歉,向各位小提琴手同行们道歉。
而你!锯子同学!需要向我的耳朵道歉!
6 /
在怎么教都无法按准音后,你每次来便都是观众身份,偶尔还领着那条只会垂涎于西瓜的狼狗一起陶冶情操。我有的时候练琴,有的时候用手机看音乐会。手机放在小石桌上,我怀里抱着半个井水西瓜,吃饱了就回屋睡觉。
直到那天,音乐学院的邮件跳出来,我当即心沉了一下,你看出我的紧张,什么也没问,只带着你的狗离开。
这应该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样子。邮件的开头写着“ 祝贺”,末尾写着“欢迎”。
在飞往奥地利的班机上我想,音乐到底是不是情感载体?那么多遍的《梦幻曲》,用掉了的两块松香,连舒曼都替我着急地想问问:你究竟听没听懂我的话呀?
飞机穿过云层,音符变成飘浮在万米高空的水蒸气,它们说其实不懂也没关系。
就像有一天晚上我在谢谢你的西瓜和花露水时,你对我说的那句话:
“想开或是放下,都是自己才能做的决定。别人能陪伴,能鼓励,但都帮不了你。”
所以懂不懂,怎么懂,是不是我想让你懂的那种懂,并不是我能决定的,而是你愿不愿意懂。
我留给你一封信,请寄宿婶婶在你高考完转交,信封里放着一张纸条,希望你收到。
7 /
“有一首《梦幻曲》,不辞作月光的请柬,请锯子同学确认后,无论多久都务必——”
“前来赴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