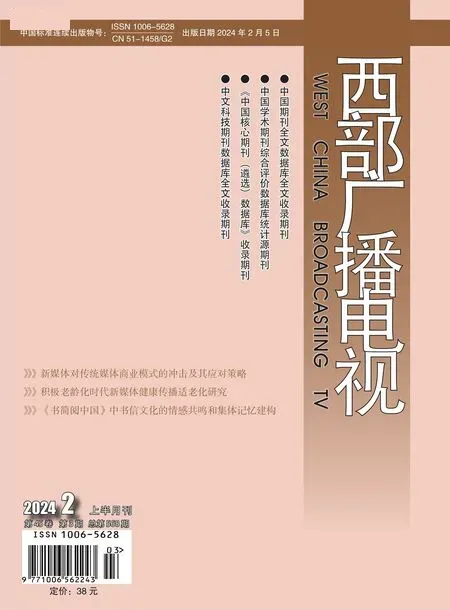电影对文学文本的影像重构
——以《河边的错误》为例
张松琪
(作者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影片《河边的错误》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从文本意义上来说,《河边的错误》作为先锋派小说本身故事为侦探悬疑题材,在文本结构中设置空白性和不确定性,让读者能沉浸到文本故事的解读中。电影同样也设置了许多的空白和召唤结构,给受众留下了想象和解读的空间。该影片的英文名称“Only River Flows”(只有河流继续流淌),与余华的观点“艺术家只能来自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相契合。
文本依赖的是大众的想象,大众通过想象填补作品中的空白从而生成自身的作品世界。而影像作品通过具体可感的画面和声音来构建影视空间,观众在具象化的屏幕空间中获得审美体验,所以经典文学改编为电影是导演与作者的较量,导演在改编时要注意原著与影像化的平衡。导演为突出《河边的错误》的画面质感和年代感,采用胶片的拍摄方式,为体现荒诞感和悬疑感,在这部类型片中融入谜题电影的风格和元电影元素,使得电影情节更加扑朔迷离。
1 重构:文学意向的转换
中国的故事片电影一直延续着以经典名著为蓝本的创作传统,改编过程中导演和编剧需要将文本空间转化为影像空间,使文本能够以可感的画面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个过程需要倾注导演和编剧大量的心血。作为余华先锋小说的《河边的错误》由文本改编为电影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将这部文学作品改为电影的过程中,导演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将文本中的文学隐喻转化为电影的视听语言,将文学意象转化为电影中具体可感的真实画面。
在文本中隐喻不单作为一个修辞手法使用,还可以传达深层次的意义,通过本体、喻体表达思想情感、激发读者的想象,增添文学作品的解读性,使读者可以通过某种事物解读文本中的含义。“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1]在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时,文本隐喻需要从文字描述转化为画面呈现,并通过符号化的视觉信息体现。在电影中马哲作为主人公穿着标志性的皮夹克,皮夹克在剧情中充当了重要的符号表征。电影开头,在满屋子穿着制服的同事之间,穿着皮夹克的马克显得格格不入;在和领导打球时,他不给领导让球;拍合照时穿着皮夹克站在一堆穿着制服的同事中间。这些情节呈现出他不善与人交际、性格上的孤僻。之后,马哲的穿着由皮夹克转换为便装,最后他眼神迷离地身着警察制服站在领奖台上,这隐喻着社会对个体的规训。当马哲精神崩溃走入河流后,疯子站在岸边穿上他的夹克,象征着二者身份上的互换。由此可见,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导演使用服化道、场景设置、人物刻画等多种手法将文本中的隐喻呈现在影像之中,从细节之处将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直观可感的画面声音,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能够仔细推敲导演设计画面的用意,从而使影像解读更添意味。
文学隐喻通过文字将隐喻编织到故事之中,而电影则通过画面中的符号、蒙太奇的组接进行隐喻。“艺术创作离不开想象,艺术家在进行艺术想象的同时,经常选取人们生活中熟知的事物来描述人们不太熟悉的事物,这一过程与隐喻不谋而合。”[2]在结构学领域电影中成组的镜头能够对现实世界进行影像化表征。《河边的错误》中导演通过梦境与现实交织相连,使用大量意象化的镜头,例如乒乓球从影院的屏幕中散落一地,暗喻马哲在一系列案情的发展下精神出现崩溃。在马哲喝醉酒射杀疯子的过程中,观众并没有看到疯子被枪射中的直观画面,却知道疯子被马哲连开三枪,因为电影通过不同机位角度的变化、画面的选择,完成了对情节的叙述。而该电影之所以让观众感觉扑朔迷离,是因为在影片中现实和梦境并没有隔绝开,观众以为这个段落中马哲已经犯下大错杀掉疯子,通过下一个段落的镜头,又发现那只是马哲的幻想。在很多电影作品中,导演为了让观众分清电影空间中的现实和梦境,会将二者进行区分,通过模糊的镜头、演员夸张的表演、意象化的音乐、怪异的色彩突出梦境。例如电影《八部半》中,男主人公圭多面临个人感情生活的混乱与电影拍摄的双重压力,梦境与幻觉不断侵入他的现实生活。在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影片《盗梦空间》中,剧情游走于梦境与现实之间,以旋转的陀螺作为区分现实与梦境的依据。但是在《河边的错误》中,导演用一种混淆视听的方式,将现实与梦境拼接起来,以一种平滑的叙事方式,让观众后知后觉。
此外,电影开头小男孩与朋友玩警察抓犯人的游戏,当他推开一扇“真相之门”后,看到的却是满目废墟。而这一段隐喻着马哲对于真相的追求,最终得到的是一片虚无。电影以影像化的叙事始终在突出文本中所体现的非理性的叙事话题,并且运用大量的意象化、夸张的手法,突出主人公在案情一步步进展的过程中,精神开始崩溃。文学化的语言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而可视化的影像同样可以用隐喻、象征、符号化的镜头来构成影片的召唤结构,使观众能够通过解读感受电影内部所表达的思想。
2 追溯:哲学命题的讨论
电影开篇引用了阿尔贝·加缪在作品《卡利古拉》中的一句话:“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阿尔贝·加缪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是“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在其作品中深刻揭露了人在社会中的异化、孤独、罪恶和死亡不可避免,但是他认为人们依然可以在荒诞的世界中追求真理和正义。导演在电影开篇用加缪的话带出了他对于文本深层次的哲学理解,使影片增添了荒诞主义的意味。
《河边的错误》在人物设置上呈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本我”是潜意识的表现,更接近兽性;而“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超我是人格中的道德成分,是由父母及其他社会权威的是 非观念和善恶标准内化而来的,其形成主要是由儿童的奖惩经验决定的”[3]。“超我既置自我于积威之下,乃临之以最严格的道德标准;可见我们的罪恶之感也即超我压迫自我的一种表示。”[4]“超我”和“自我”会通过道德来监管约束“本我”。而在影片中疯子就是“本我”的化身,是一种无序的存在,也是个体无意识的物化体现。影片中马哲之所以不能很快结案,是因为他是以正常的思维方式去分析疯子为什么把这儿几个人都杀了,想要找出其中的隐秘的关联或者是某种联系。而作为“本我”化身的疯子就是疯癫的、非理性的象征,他的想法是非理性的、无序的,所以就导致马哲在分析案件的同时自身陷入了精神陷阱。
在文本中马哲是作为“超我”存在的,4个被害者代表着“自我”,疯子则是“本我”的化身。马哲在不断寻找真相中,发现了被害者的秘密,即幺四婆婆的受虐癖、王宏的婚外情、理发师的异装癖,间接导致了他们的悲剧。随着案件的一步步推进,马哲精神崩溃,他在梦境和幻想中以“本我”的姿态将疯子绳之以法。这表明“非理性疯癫对于理性世界的威胁促使理性世界采取了暴力手段将疯癫从理性世界铲除,然而这种铲除却是以破坏理性世界秩序为代价的”[5]。现代社会更加注重事件的结果,而忽略掉过程的重要性。在这种错乱的非理性世界中,不论是小说作者还是电影导演都需要给受众一个结果,讽刺的是,马哲想要在非理性世界中找寻一个理性的结果,但是在探寻的过程中,自己也成为秩序的破坏者。
人类因为理性思维能力而区别于动物成为万物的灵长,但是世界本身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在这些不确定因素的面前人的这种理性思维就会陷入“不可知”的困境。从古至今,人类对于世界中“不可知”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研究。例如,中国的典籍《周易》中所展现的命、运、气以及王阳明的心学,都在探讨人们如何在不可知的世界中正确认知世界。《河边的错误》中折射着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命、运、气,正如马哲的汽车车牌是31415,即类似数学中的圆周率π,暗含无限和无序。马哲的孩子被诊断出可能存在智力障碍,电影结尾孩子与疯子做出了同样的玩耍动作,暗示马哲的孩子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疯子,呈现出荒诞的循环。导演为了呈现非理性将生活中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放大,使得整部片子都呈现了一种荒诞的宿命感。因为偶然性因素,诗人和理发师出现在案发当天的河边,之后诗人被疯子杀害,理发师被发现异装癖的秘密,从大楼上一跃而下。现实的不可知和这种荒诞的宿命感给影片蒙上一层悲剧的面纱,使马哲和观众陷入“理性的怪圈”。
3 再现:少数群体的呼唤
现实主义影片注重对于生活的再现。在电影创作中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旨在通过对现实生活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展现真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物,引发观众思考当下社会中的重要议题。现实主义电影作品作为“现实的渐近线”,要求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以求真的态度、虚拟的形象,打造接近真实的体验。《河边的错误》导演为贴合20世纪90年代的风格,在拍摄过程中使用16 mm的胶片拍摄,为突出年代感特意在胶片中加入划痕,制作后期专门设置了三间冲洗胶片的暗房。
案件发生在河边,南方潮湿的小镇不停地下雨,破坏了现场证据,这些微妙的设定与电影的叙事逻辑相契合,经得起观众推敲。这些细节的处理、细腻真实的还原都是现实主义作品惯用的创作方式。现实主义电影只有体现真实的场景,基于真实性创作,经得起观众推敲,才能立足于市场和大众。
现实主义的影片中需要塑造可信的典型人物形象。“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或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统一。”[6]典型形象要求艺术家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出发,对客观生活加以艺术概括,在生活中挖掘人物原型,创作出的具有较高典型性的艺术形象。例如,疯子的形象常常会出现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着强烈的隐喻性特征,导演选取身材高大的演员能够强化其作为连环杀人案凶手的躯体化呈现,“疯子”的形象象征着在约定俗成中的常规社会里不遵守规矩的异类。又如,《河边的错误》中,王宏的诗人形象是通过他戴着眼镜在诗歌大会中侃侃而谈,以及那封写给情人的诀别信等情景来塑造的。幺四婆婆是电影中最早出现的人物,但也是电影中最难刻画的一个形象,大银幕创作传播受到多种限制,所以电影通过马哲在房屋中看到鞭痕的镜头隐晦地表现出幺四婆婆的受虐倾向以及她和疯子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隐秘的事件和关系被放置在大众视野中,他们将面临倾泻而下的流言蜚语和同事、亲人、村民的审视,所以他们的死亡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对小人物的一次无意识“倾轧”。
导演将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隐藏在影片内部中,以“疯子”为媒介,呈现出一连串社会中异化、被异化和正在异化的人物,在这些异化的人物中探究人与集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本中人物形象最大的改编是将理发师的无意识行为转变为一种合理的行为,将他塑造为有着“异装癖”的人物形象,使他身着女装卷进凶杀案中,不论是否能够洗脱嫌疑,他身着女装头戴大波浪的形象和之前被判“流氓罪”都会被公之于众。理发师是马哲追求真相的头号受害者,而他跳楼砸在马哲车上也成为压倒马哲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电影选取社会中少数群体进行刻画,采用夸张的手法,将现实与影像之间的裂缝弥合,让观众感受到人物对于现实生活的困顿与迷茫以及他们在面对众多审视者的目光下所作出的反应。当观众将其与现实联系,进行深入思考,对于这个影片中谁是真正的凶手,或许就有了答案。
“元电影是回归电影最基本的概念来省思电影自身,在影片中展示电影制作过程,或电影再现形式的符号系统”[7],也是一种比较抽象和自我意识强烈的创作方式。魏书钧在其影片中多次表达出他对于“元电影”概念的自我认识,影片中警察在电影院办公,在舞台上领取“三等功”功勋奖励、电影院招牌被重重砸在地上、放映机被烧毁,通过这些夸张、颠覆传统逻辑的情节和画面,用电影的造梦功能让观众在真实与梦幻之间游离,感受从少数者那里带来的灵魂叩问和社会伦理。近年来,中国电影不断找寻新的突破口,魏书钧对于电影的创作基于他对于电影本身的理解和热爱。《河边的错误》将现实与梦境置于影片内容中,探究电影新的表现方式,将目光集中到社会上的少数人群身上,以导演独有的创作风格,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加入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