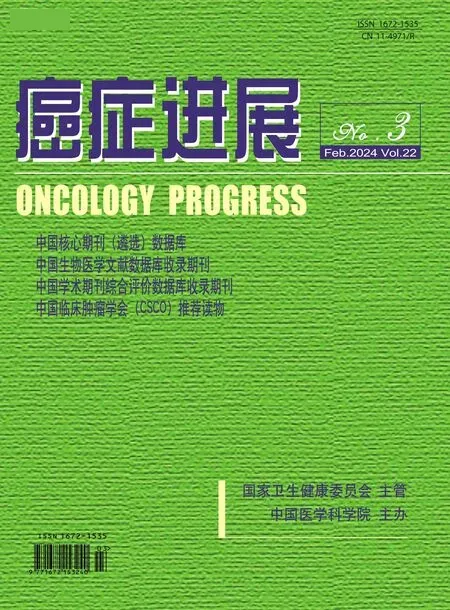免疫联合治疗在前列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王宇,于大鹏,杨彬
1济宁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山东济宁 272000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泌尿外科,3血管外科,山东济宁 2720000
前列腺癌是老年男性的常见恶性肿瘤,发病率居全球男性恶性肿瘤第二位[1],也是全球第五大死亡原因,2020 年前列腺癌全球新增病例估计超过140 万例[2]。同时,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呈明显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前列腺癌病死率比1990 年增加了388.91%,死亡率增加了124.55%[3]。GLOBOCAN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前列腺癌新发病例高达125 646 例,病死病例56 239 例[4]。临床对于器官局限性前列腺癌的治疗,多采用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近距离放射治疗和外照射放射治疗等[5],治疗效果良好,部分甚至能得到治愈;对于局部进展期和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治疗,则以雄激素剥夺治疗(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ADT)为主,因前列腺癌由雄激素驱动,治疗后睾酮水平降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患者会产生耐药性,继而进展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astration- 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CRPC)[6],其中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的5 年生存率甚至低于30%[7]。目前,在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mCRPC)的治疗中,免疫疗法进展迅速,研究出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肿瘤疫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CAR-T)疗法等多种方式,改善了mCRPC 患者的生存率。除多西他赛外,前列腺癌的治疗药物还包括阿比特龙、恩杂鲁胺、阿帕鲁胺、sipuleucel-T;其中sipuleucel-T 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作为第一类肿瘤疫苗[7-8]。尽管研究证实了免疫疗法治疗前列腺癌的良好前景,但由于免疫疗法恢复免疫平衡的目标与前列腺癌的“冷肿瘤”特性[9],前列腺癌的免疫治疗效果并不理想[10]。本文总结前列腺癌免疫抑制的机制,并对免疫疗法与其他疗法联合治疗前列腺癌的机制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前列腺癌免疫联合治疗提供参考。
1 前列腺癌免疫抑制的机制
与其他恶性肿瘤如肺癌相比,前列腺癌免疫治疗的效果不佳,针对前列腺癌免疫抑制的机制,各学者提出了各种解释。
有学者认为,前列腺癌免疫治疗的效果不佳可能与前列腺肿瘤的低肿瘤突变负荷有关。肿瘤突变负荷是肿瘤基因组每个编码区中基因的突变率,不同肿瘤的体细胞突变率不同。前列腺癌的突变率约是每兆碱基中含有1 个体细胞突变,而肺癌或黑色素瘤每兆碱基含有10 个或更高的体细胞突变[11]。同时,肿瘤新抗原的形成与各种形式的基因突变有关,有较高体细胞突变负荷的肿瘤形成的新抗原更多[12]。研究表明,部分前列腺癌患者参与DNA损伤修复基因的突变率较高[13],这些基因的突变导致该部分患者拥有较高的肿瘤突变负荷[14],最终导致免疫治疗的效果更佳[15]。由此可见,免疫治疗的疗效与肿瘤突变负荷有关,大部分前列腺癌患者的肿瘤突变负荷较低,导致前列腺癌免疫治疗的效果不佳;相反,高突变负荷的肿瘤如黑色素瘤和非小细胞肺癌,均具有较高的肿瘤突变负荷,导致其对免疫疗法的反应较高[16]。
还有学者认为,前列腺癌免疫治疗的效果不佳可能与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有关,即肿瘤细胞通过内在和外在机制建立了一个不适合免疫细胞浸润和不适合杀伤肿瘤细胞的环境,其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通过阻止效应T 细胞的功能,促进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和转移[17]。在免疫微环境中,垂死的肿瘤细胞会释放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通过识别DAMP而被激活,这些细胞会释放抗肿瘤细胞因子,并促进树突状细胞的成熟和抗原呈递[18-19]。前列腺癌的DAMP 产量较低,导致树突状细胞的激活受影响,免疫抑制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的产生减少,最终导致肿瘤周围T 细胞的缺失[20]。一项研究表明,与其他恶性肿瘤相比,接受阿比特龙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其原发性前列腺肿瘤中浸润的CD8+T 细胞数量会明显较少[21]。低T 淋巴细胞浸润、缺乏肿瘤抗原,均会导致树突状细胞活化受损、免疫抑制细胞数量增加,最终影响肿瘤细胞的识别和杀伤作用[19]。此外,肿瘤还可以促进免疫抑制细胞的生长,特别是调节性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其可表达细胞毒性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 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和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CD1,也称PD-1)等抑制分子,以此来抑制T 细胞功能,促进包括转化生长因子-β、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白细胞介素-10 在内的免疫抑制因子的表达,最终导致肿瘤细胞转移[22-23]。
由此可见,前列腺癌低肿瘤突变负荷的特性以及独特的TME,导致免疫疗法的治疗效果不佳。免疫治疗与ADT、放疗、化疗、多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联合在前列腺癌的治疗中能否发挥协同作用尚未明确。
2 免疫疗法与其他疗法联合治疗前列腺癌
2.1 免疫治疗联合ADT
ADT 是局部晚期和转移性前列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包括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或拮抗剂、双侧睾丸切除术或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拮抗剂。研究表明,ADT 具有促免疫作用,主要通过影响前列腺癌细胞的免疫浸润,使T 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增多[24],从而阻断CD8+T 细胞中的AR,增强T 细胞功能,防止T 细胞衰竭,刺激CD8+T 细胞中细胞因子的产生[25]。PD-1 是一种T 细胞表面受体,对T 细胞的活化有负向调节能力,PD-1 水平越高,肿瘤细胞越不易被细胞毒性T 细胞裂解,进而促进肿瘤细胞生长,而ADT 能提高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水平,增强抗PD-1 作用[25-26]。
一项研究对6 例前列腺癌患者ADT 治疗前后的病变部位进行活检和转录组学分析,结果显示,ADT 治疗显著增强了前列腺癌TME 中细胞毒性T 细胞的浸润和活性,这种由ADT 治疗引起的免疫激活在肿瘤的早期阶段更为明显,但当肿瘤进展到CRPC 阶段时则变得非常有限[27]。2013年的一项AR 拮抗剂氟他胺和第二代CAR-T 细胞疗法联合治疗前列腺癌的研究结果显示,二者联合治疗可明显减少肿瘤细胞计数[28]。由此可见,ADT 能够增强前列腺癌患者的免疫浸润,且与免疫治疗联合应用的效果更佳。但值得注意的是,雄激素对前列腺癌TME 和免疫细胞活性的作用较为复杂,ADT 与免疫疗法联合时,应慎重选择组合方案,包括不同的药物组合和不同的用药时机,因为这些均可能会导致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11]。
2.2 免疫治疗联合放疗
放疗是用放射线照射肿瘤靶区,通过对该区域肿瘤细胞DNA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来杀死肿瘤细胞[29]。有研究表明,放疗与免疫系统关系密切,放疗联合免疫治疗能增强抗肿瘤效果。接受放疗的患者存在照射部位与非照射部位肿瘤同时缩小的现象,这被称为远隔效应。这可能是因为肿瘤细胞被辐射后,可引起肿瘤细胞DNA 受损,产生了肿瘤相关抗原,进而被抗原呈递细胞吞噬,呈递给CD8+T 细胞,而CD8+T 细胞不仅会攻击原发性肿瘤,还会通过血液和淋巴循环到达并附着在其他部位并攻击该部位的肿瘤细胞,形成远隔效应[30-31]。但远隔效应相对罕见,无法广泛地用于治疗,存在的TME 也会抑制T 细胞的功能。与单一的放疗或免疫治疗相比,二者联合治疗能明显提高远隔效应的应答率。
研究表明,不同时间、剂量和组合,放疗和免疫治疗的效果不同。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SABR)是一种相对高精度的放疗形式[32],能够优化新抗原形成,诱导促炎因子分泌并促进肿瘤特异性效应T 细胞的迁移[29],特别是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协同治疗时,该效果显著提高。研究显示,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苯扎鲁胺或苯扎鲁胺单药治疗mCRPC 患者,均不能为患者带来满意的总生存期[33]。相反,一项Ⅱ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估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ligand 1,PDCD1LG1,也称PD-L1)抑制剂阿维鲁单抗联合SABR 治疗mCRPC 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疾病控制率为48%,31%的患者照射和非照射病灶均有客观反应[34]。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接受帕博利珠单抗联合SABR 治疗的患者中,70%(7/10)的患者有反应或病情稳定[26]。上述研究表明,放疗联合免疫治疗能有效提高前列腺癌的治疗效果。
此外,治疗过程中还要考虑所使用电离辐射的最佳剂量和分次,部分临床前研究表明,不同的辐射剂量对肿瘤细胞活性和免疫系统的刺激不同,特别是高剂量大分割的电离辐射,可增强前列腺癌患者的抗肿瘤免疫力[35]。但免疫治疗联合放疗治疗前列腺癌的效果尚需进一步验证,是未来需要研究的方向。
2.3 免疫治疗联合化疗
化疗是用化学药物杀死或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有研究表明,化疗与免疫治疗间也存在协同增效作用。首先,化疗能在诱导肿瘤细胞死亡的同时,促进肿瘤抗原的释放和呈递,刺激免疫效应分子的产生[36]。其次,化疗药物能选择性地抑制免疫抑制性细胞,如Treg 细胞和髓系来源的免疫抑制细胞,以此来提高抗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37]。最后,肿瘤体积的缩小能给免疫治疗更多的时间,还能降低免疫治疗耐药的可能性[36]。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在前列腺癌的治疗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rostate-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PSMA)在前列腺癌细胞表面表达,并可在肿瘤进展的全程表达,当其与CAR-T 细胞疗法相结合时,能形成一种针对前列腺癌的特殊免疫治疗方法,即PSMA-CAR-T 细胞疗法。多西紫杉醇是一种抗肿瘤药物,其通过抑制细胞有丝分裂治疗CRPC。一项研究建立人前列腺癌肝转移小鼠模型和人前列腺癌异种移植小鼠模型,结果显示,多西紫杉醇联合PSMA-CAR-T 细胞疗法具有协同增效作用,能同时下调包括PD-1、CTLA4、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ymphocyte-activation gene 3,LAG3)、T 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结构域分子3(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mucin domain protein-3,Tim-3)在内的免疫检查点分子的表达;此外,多西紫杉醇还通过促进CAR-T 细胞的浸润和减少髓源性抑制细胞来增强CAR-T 细胞疗法的疗效[38]。另一项研究证实了多西紫杉醇的免疫调节潜力,该研究采用多西紫杉醇预处理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结果显示,多西紫杉醇可诱导高迁移率族蛋白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HMGB1)水平升高,随后CXC趋化因子配体11(C-X-C chemokine ligand 11,CXCL11)水平和CD8+T 淋巴细胞也均升高[39]。
关于化疗与免疫疗法联合治疗前列腺癌的临床疗效,目前临床已有较多研究报道。一项前列腺癌异种移植瘤模型的临床前研究表明,与单纯化疗相比,PSMA 导向的CAR-T 细胞疗法与小剂量多西紫杉醇联合治疗明显抑制了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40]。硝羟喹啉是一种被FDA 批准用于治疗尿路感染的抗生素,有研究发现,硝羟喹啉对人前列腺癌也具有抗肿瘤活性[41]。一项硝羟喹啉联合PD-1 阻断剂治疗前列腺癌的临床前研究结果显示,硝羟喹啉联合PD-1 阻断剂协同治疗组的肿瘤重量、肿瘤大小、细胞增殖能力、微血管密度及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水平均明显低于单独治疗组[42]。
2.4 免疫治疗联合PARP 治疗
PARP 是一种DNA 修复酶,能修复细胞中损伤的DNA;相反,PARP 抑制剂通过抑制碱基切除修复途径干扰细胞DNA 损伤修复,诱导肿瘤细胞死亡[43]。研究表明,PARP 抑制剂可在诱导肿瘤细胞死亡的同时,增强免疫反应,特别是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有一定的协同作用。首先,PARP 抑制剂能导致肿瘤细胞DNA 损伤的积累,增加细胞质中DNA 的数量和新抗原的积累,最终增强肿瘤免疫反应[44-45]。其次,PARP 抑制剂能通过一系列的通路激活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TING)的表达,使PD-L1 水平升高,从而进一步增强肿瘤免疫[46-47]。其中Ⅰ型干扰素的激活与PD-L1 的上调均能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作用,是PARP 抑制剂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发挥协同作用的机制。
在前列腺癌患者中,约1/4 的mCRPC 患者存在同源重组修复(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HRR)改变,导致该部分患者表现出对PARP抑制剂较强的敏感性[48]。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DNA 损伤修复突变的肿瘤患者,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为PARP 抑制剂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治疗前列腺癌奠定了基础。一项临床研究采用奥拉帕尼联合度伐利尤单抗治疗17 例mCRPC 患者,结果显示,9例患者的PSA降低≥50%或影像学上有所改善,其中存在HRR改变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达到12 个月的比例为83.3%(95%CI:27.3%~94.5%),不存在HRR 改变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达到12 个月的比例仅为36.4%(95%CI:11.2%~62.7%)[49]。该研究表明,PARP 抑制剂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存在HRR 改变患者的效果更为显著。
3 小结与展望
免疫疗法作为一项新型治疗方法,为前列腺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众多临床试验也已证实,该方法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但前列腺癌拥有“冷肿瘤”特性,其免疫浸润水平相比于肺癌等肿瘤低,且单一采用免疫疗法很难抑制肿瘤的免疫逃逸。其他的常规治疗方法,如ADT、化疗、放疗及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如PARP 抑制剂,均显示出了一定的促免疫作用,为免疫疗法提供了联合治疗的新方向。现今,多项临床试验也在评估免疫疗法的组合策略,这些结果将为前列腺癌的免疫治疗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