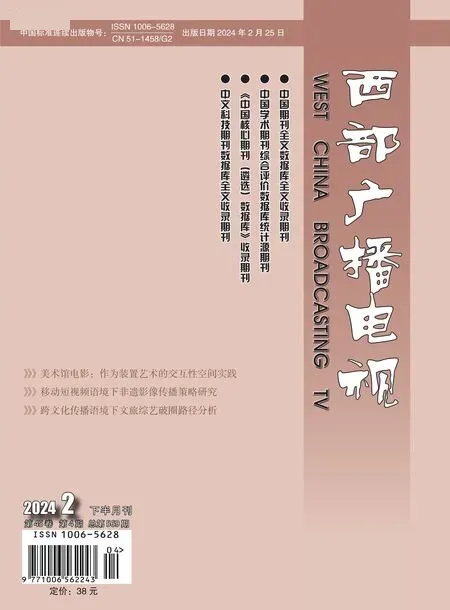性别的消解:国产影视剧表演中的“去性别化”探析
胡彧哲
(作者单位: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领域价值观念的持续重构,影视表演中女性的文本模式发生改变,当传统道德伦理被置于自由多元的思想氛围中时,其在公众中的地位与印象日渐模糊。与此同时,女性带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由个性的渴望与追求,以坚定的姿态步入公众视野,国产影视剧表演也逐渐显现角色的“去性别化”趋势。在此,“去性别化”主要指身处现代社会与文化中的女性,从内心深处摆脱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不再局限于以往男性的期待;同样,男性也从传统社会性别建构赋予他们的印象中脱离出来。无论男性或女性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社会性别框架,而在影视表演中不再以“男性”或“女性”为群体单位并作为观察对象。在优秀的影视剧作品中,角色创作也不再刻意强调角色的性别特点,而力求摆脱长久以来沉积形成的性别刻板印象,追求角色在影视剧表演中作为“人”(社会角色)所呈现出的人物属性和特点,以更加宽广的视角展现角色的多维特质。
1 国产影视剧中的性别文化
所谓性别文化,指的是基于男女两性社会特征、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而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知识经验、风俗习惯、制度规范等意识形态及其表现[1]。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影视剧中表演再现的性别文化,以对性别特征的外化表现为主,且常常以女性身体为载体呈现。女性的身体被置于男性凝视下,以满足男性的观看需求与视觉欲望。其中,基于男性视角产生的“美人文化”,不仅是两性关系之间单向度的文化规范,也是从外部观感对女性形象进行的一种控制。这种文化的传播使得女性形象在影视剧中的塑造很难摆脱陈规陋习的影响,更是对女性形象进行了物化和超现实化。随着传播媒介的更迭与普及,早期只是在男性凝视下被作为风景观赏的象征美丽的符号,逐渐成为被社会全体赏析评议的对象。时至今日,性别文化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影视作品中的观看主体与被观看者的身份随着经济消费主体的偏转发生对调,不知不觉男性也成为“美人文化”中的部分主体。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表明,人类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没有性别的,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文化[2]。社会角色与性别形象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影视剧中的性别形象能够体现社会角色,反之社会角色又影响着表演中的性别形象塑造。在中国早期电影中,出现了一类颠覆传统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与气势高涨的斗争意识,表现出此前女性少有的坚强豪迈的特征。其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模糊了性别特征,在台词、造型、行为方式以及叙事功能的处理上都完全剥离了女性的性别特征,被“男性化”塑造的女性通过在社会中“扮演”男性以得到与男性等同身份的资格。由于受到特定时期大众对军装和工装的推崇与热爱,当时男性和女性的外部形象上有统一的“去性别化”趋势。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影视剧作品,表面上看似宣扬男女一样的平等观念塑造区别传统的女性形象,其本质是基于淡化女性特征,无视女性性别特征的极端“去性别化”处理方式。在此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社会角色与影视剧中的性别形象,体现了我国性别文化发展与西方的不同。性别文化历来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20世纪90年代,角色的形象塑造成为我国影视媒介中性别文化的重要呈现要素。两性生存的文化环境与当下社会性别文化语境,借由影视剧表演中演员对角色的形象构建映现。
2 国产影视剧表演中的“去性别化”呈现
表演创作中角色的差异性塑造为创作者提供的独有体验,是大众文化与表演创作保持多样性的重要来源。演员在二度创作中淡化对角色性别社会化的创作理念,以追求更为和谐的表达方式。“去性别化”在影视剧表演中的呈现重心在于对人物角色个体生命体验的强调,角色的身份并不仅限于“她是女人”或“他是男人”,而侧重体现个体本身的个人特点及其他社会身份。相比在影视剧表演中刻意塑造一个怎样的男性形象或女性形象,表演创作消减了对角色的性别规范,重点聚焦于演员对剧本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与角色的融合,不再完全强调角色的性别特点,以塑造一个怎样的“人”为创作的最终目的。
2.1 角色与演员的魅力融合
国产影视剧表演中曾塑造了不少偏中性特征的人物形象,此类角色的塑造大多以牺牲角色原本的性别特质,如女性角色以模仿男性外在特征等表现方式,打破影视文化中的性别认知与二元对立框架。若是表面上模拟人物的外形和表现人物性格的一般特征[3],仿形却无心的表演,注定无法塑造出生动、真实且被大众认可的角色。表演创作以“去性别化”进行角色塑造,更能为受众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影视角色,展现出女性的强大与自信。
演员以身体作为角色再现的载体,在表演创作中,无论是台词、行动还是贴合角色的造型设计,同样能刺激演员对角色的创作,促使演员更快找到角色的感觉。电影《红海行动》中女演员蒋璐霞饰演蛟龙突击队中的佟莉。蒋璐霞塑造的佟莉不仅是女性,更是一名军人。这一角色与传统的战争片中以性感妩媚形象出现的女性角色截然不同。在表演中,蒋璐霞并未刻意模仿男性特征,保留了女性特有的身形和声音。作为小队的副机枪手,即火力手,这一角色通常由高大强壮的男性担任。然而,蒋璐霞成功地展现了女性同样可以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影片中,佟莉修长的身材、坚毅的神情和冷静的态度都让观众深入剧情,对她军人的身份深信不疑。演员在表演时,内部体验和外部感受都以角色的社会(职业)身份为主导,而非性别身份。蒋璐霞在塑造坚毅勇敢的军人角色时,并没有将角色变成无情的“铁人”,而是赋予她正常的女性情感。当她与战友并肩作战受伤时,面对有好感的队友递来安慰的糖,虽然没有表现太多言语和行动,但通过与对手的表演,观众能感受到这份朦胧的情感。影片并未过多渲染片中角色的个人情感,区别以往女性面对爱情和生死离别的态度表现,蒋璐霞扮演的佟莉以细腻点到为止的情绪触动人心,让观众为角色之间的感情动容。在部分角色塑造时,女性被看作男性的附属品,男性通常是站在救赎者的立场看待女性。而在佟莉一人独立对抗恐怖分子时,并未出现男性救援者助力她克服困难的剧情。相反,她彰显出我国特种兵所具备的绝对对抗能力和坚韧的心理素质,最终运用格斗技巧将敌人制服。在表演过程中,演员并未将该角色塑造为男性化的女性,特种兵身份不受性别影响,虽然身着与战友相同的作战服,但是其女性身份依然保留并展现。影片结尾,角色身着洁白海军服,裙装与她相得益彰,既显露出角色的女性知性美,又不失其为军人的身份特质。蒋璐霞的表演将佟莉这个角色塑造得生动、真实,向大众展现了一个能力极强的特种兵形象。
“去性别化”表演让人忽略演员性别身份而沉浸于演员对角色的诠释中,演员与角色融为一体,共同散发魅力征服大众,让角色变得完整、人物形象更丰满,而不只是强化角色的性别特征,以“男性”或“女性”对角色区分、概括。
2.2 性别角色的“物化”呈现
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影视剧表演中的人物形象被加速物化,角色的性别表征被弱化。影视剧表演中对角色的塑造重心被转移到角色的人格魅力与视觉的包装上。影视剧中的角色带给大众消费欲望的刺激,角色的性别不由演员决定,不由角色决定,而是影视剧作品的受众以他们在角色身上观察到的人物特征为依据,赋予角色性别。
女性主义学者奈奥米·沃尔夫指出,消费文化以下列事物为支柱:充斥着各式性克隆物的市场,想要物的男人和想被物化的女人,以及千变万化、用完即抛、由市场操控的欲求之物[4]。随着生活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影视剧观众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化浪潮卷入网络、影视等文化消费领域。2015年播出的电视剧《琅琊榜》引发广泛关注,剧中梅长苏与靖王是一对挚友,两人之间的胜似亲人的关系也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与传统的智勇双全角色不同,梅长苏被塑造成一位身患重疾的隐忍谋士,他言辞谨慎,情感内敛,面对靖王的误解和固执,常因为病痛而显得柔弱。这一形象,在播出时引发女性观众的同情和关注。剧中以友情刻画的角色关系,因一方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男性角色的性别个性特征,使两者的关系在女性视角下产生了更丰富的讨论空间。
在此类双男主模式的影视剧中,演员对角色的塑造都基于角色在剧中的身份进行详细表现,如《琅琊榜》中二人一个是谋士盟主,一个是王爷。通过剧中角色的人物特点,可以观察到演员结合剧本所赋予的角色身份与生活背景进行创作,将重点落在人物本身的形象塑造上,而非角色性别特征的呈现。演员对人物形象的建设还基于社会对男性固有的性格认知,结合不同情境带给角色的刺激与影响,进行细微深入的刻画。剧本对人物性格的设定使其中一方的男性气质在呈现时被削弱,演员深入揣摩人物后,呈现出细节表演,塑造出当下观众所喜爱的形象气质。基于对他人性别形象消费的文化心理,这类男性角色由观众依据角色特点与私人化标准将角色进行强弱划分,角色本身的性格特点与性别身份受到角色的人格魅力与视觉包装的影响,在电视剧中逐渐呈现出非典型性别气质倾向,使这类作品与角色在市场获得更为广泛的讨论与延续性的关注。
3 影视剧中“去性别化”表演的成因分析
在大众固有的观念中,社会性别是男性,就默认这一男性人物具备强健的体魄,能够担负起家庭经济重任;与之相反,若社会性别为女性,则该女性人物就应当出现在封闭的私领域中,生活中温柔细心,为家庭毫无怨言。在生产资料不断更新的今天,影视剧表演中两性常见的传统不可逾越的分工搭配早已得到更新,两者相互独立且区分明显的领域边界也逐渐变得朦胧直至相互融合。两性角色在公、私领域中达到步调一致的你进我退、错落组成。影视剧表演中“去性别化”的根本目的并非主张无视角色的性别存在,而是让影视剧表演创作从对角色的性别脸谱化塑造中脱离出来,推动社会意识的继续发展,强调表演中角色在社会环境中的关系,以及作为个体单位在故事情节中的构成。
艺术从根本上是个人化的而非性别化的[5]。表演作为在体验基础上的再体现的艺术,在影视剧中不同经历、背景、生活、思想情感差异下创造出个体所独有的生命体验,角色的独特性与差异性造就了表演创作的多样性。演员用心塑造的角色,首先应该作为有独立意识的人物呈现在观众面前。当演员进入规定情境中,依据角色的性格、情绪,根据故事情节发展而作出反应表现个人特质时,都是在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不是男性形象或者女性形象。影视剧表演的“去性别化”,让人物能够既阳刚、勇敢,又被允许害羞、犹豫。优秀品质的培养应当以人为单位,让每个角色都尽可能积极正面,但不该以“性别”为单位归类。优秀的作品中塑造的优秀的人物形象,往往对其评价“有血有肉”。伴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与矛盾冲突的出现,演员需深入体验人物内心世界,感受其在规定情境下的情感波动与心理变化,淡化性别,充分挖掘人物的独特性。经受过磨砺的成长型角色更具人物魅力,更吸引人,也更具积极的示范作用。因此,演员应凭借对角色的不同理解,诠释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通过“去性别化”跳出角色塑造刻板固化的陷阱,拒绝表演假大空的完美形象,摈弃理想化的想象与浪漫化的期待,基于现实刻画人物的生活、工作、感情,真实地再现典型人物。
4 结语
影视剧表演中的“去性别化”现象,不仅揭示了媒介传播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与性别文化的关联,也折射出社会文化与人们思想意识的演变。基于性别文化分析,影视作品中的性别观念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及历史文化的影响,既传播复制着现实生活中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也塑造了一些迎合消费市场需求的性别形象。“去性别化”现象反映了当前社会生活中两性关系及变化的趋势,使公众的审美判断超越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逐渐形成更为全面、包容的性别意识。
国产影视剧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在观看影视剧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人格塑造、审美取向、性别表达到行为方式,都无意识地借鉴或表达着对影视剧表演中性别呈现的认同。影视剧以社会真实生活为创作文本,经过表演创作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的性别角色,从侧面展现了性别意识在大众中的普及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在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影视剧表演中人物性别形象的塑造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人们应防范出现资本逐利的类型化模仿。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正努力摆脱性别刻板印象,构建新时代积极的社会性别认知,影视艺术更需致力于塑造具有积极正面精神特质的人物形象,无论其生理性别,以美和艺术的方式引导观众,助力他们“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