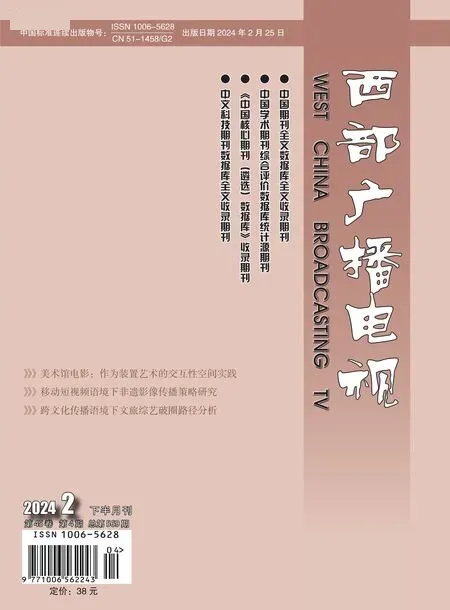旅行类综艺节目的困境与破局
——浅析《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的模式创新
李 丽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
旅行类综艺节目指的是以素人或明星为参与者,借助旅游的形式,采用纪实性镜头,真实地跟拍展现参与者在旅途中所经历的真人真事,并向受众客观地展现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从而实现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的节目[1]。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是我国旅行类综艺发展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节目主要是介绍祖国大好河山,顺带讲述节目中拍摄地点所蕴含的文化故事。主要代表作品有《正大综艺》《祖国各地》等[2]。2014年是我国旅行类真人秀爆发的关键节点,随后涌现了一大批旅行类综艺节目,但是也出现了同质化、泛娱乐化、重明星轻旅行的现象,国内旅行类综艺节目亟待创新节目模式。
1 我国旅行类综艺节目发展困境
1.1 泛娱乐化、低俗化
在技术加持和受众需求等因素的驱动下,我国旅行类综艺节目出现泛娱乐化的现象。“泛娱乐化”是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依托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的传播手段,将各领域的人物及事件进行娱乐化修饰,以“能否取乐、吸引大众”为追求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背景内容的严肃性[3]。在泛娱乐化的背景下,很多严肃的议题被解构,很多富有深度的内容变得浅显化。而泛娱乐化的问题也使得旅行类综艺节目中本应传达的地方风俗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法得到深度挖掘与传播,使得旅行类综艺节目成为当下社会的“快消文化产品”,将大众的文化审美引向低俗。
1.2 套路化、模板化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 a 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道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被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而文化工业的本质则是“标准化”与“同质化”[4]。首先,当下的旅行类综艺节目在文化工业的背景下陷入同质化的怪圈,一旦有“出圈”的旅行综艺,便会出现一哄而上、竞相模仿及抄袭的现象,这种复制及粘贴不仅包括人设的模仿,也包括情节走向的套路化和模板化。例如,《妻子的浪漫旅行》《青春环游记(第二季)》和《漫游记》中都有一位担任着适时抛“梗”,把控全局节奏的角色。而《花儿与少年(第一季)》中的郑佩佩与《花儿与少年(第二季)》的毛阿敏,都扮演者“知心大姐”的角色。其次,纵览近几年的旅行类综艺,制造矛盾与冲突仍然是大多数旅行类综艺的特征。例如,在《各位游客请注意》中,节目以陌生人组团旅行为主要模式,旅行中各位嘉宾互相不理解、“频道”不一致等问题不时出现,放大了旅行中由于想法不一致而产生的矛盾。而《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季)》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矛盾,节目中两位女嘉宾因为开销而意见不和,二人因此闹得不愉快。模式化的创作,同质化的旅游综艺节目频出,使得各节目缺乏自身特色,成为本雅明笔下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旅游综艺节目质量参差不齐,收视率进入低迷状态,口碑不尽如人意。
1.3 重明星,轻旅行
当下的旅行类综艺节目大多是以当红明星作为嘉宾,嘉宾自身的人气保障了该节目的基础流量与粉丝,但是,明星的加入也易使得旅行类综艺节目出现“重明星,轻旅行”的问题,喧宾夺主成为当下旅行类综艺节目的痛点。国内部分旅游类综艺节目打着“分享旅游体验”的旗号,但是中间穿插着明星之间的“钩心斗角”的情节,剧情化、模式化的误解、争吵、和好如初使得旅行类综艺节目逐渐偏离创作初心。例如,在《花儿与少年》中,嘉宾N和Z因选餐厅而不愉快的情节贯穿该节目始终,而节目本该宣传的旅游和体验在节目中则沦为陪衬。
2 《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的模式创新
2.1 嘉宾:熟人组合,兼具知识与流量的“青年领袖”
《跳进地理书的旅行》沿用《名侦探学院》《密室大逃脱大神版》《森林进化论》中的“熟人组合”,这不仅使得该档节目一经播出就具备了基础的粉丝群体和流量,也避免了嘉宾初识的尴尬。不同于以往的综艺节目,节目起初可能需要嘉宾之间进行简单介绍、了解与磨合。但是在该档节目,嘉宾无须花费时间去了解彼此,这一模式符合该节目短集数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节目本身的节奏,提升了观众的体验感。此外,该档节目的8位嘉宾分别是清华大学的火树、北京大学的郭文韬、南京大学的蒲熠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何运晨、中国传媒大学的齐思钧、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黄子弘凡、中央音乐学院的曹恩齐以及四川师范大学的石凯。8位嘉宾均在各自领域出类拔萃,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良好的青年意见领袖作用,既有实力,也有学识,同时也个性鲜明。“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最早由拉扎斯菲尔德提出,其指的是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在《跳进地理书的旅行》中,嘉宾的选择也与该档节目的目标群体不谋而合,即向青少年传达榜样的力量,利用青年意见领袖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2 “地理+综艺”,创新中的寓教于乐
不同于传统的旅行类综艺节目,《跳进地理书的旅行》节目组将当地人文、景观、历史、地理等知识融入节目当中,以地理书本为导引,巧妙地将看风景和学知识结合起来。该档节目摒弃了以往旅行类综艺节目的泛娱乐化、重明星轻旅行的问题,而是将教科书中抽象的地理知识通过视听符号展现在观众眼前,让观众在享受风景的同时,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到教科书里的地理知识,真正做到寓教于乐,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不再是二选一,而是兼容并包。为了保障节目的专业性,节目组与地理专家顾问详细沟通,确保基础知识点的正确,并且从民俗角度切入,寻找有意思的知识点。例如,节目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嘉宾通过房屋特征和地貌特征判断出葫芦娃是云南人。此外,节目组所选的地理知识贴近初高中生的教科书,并不会特意追求新奇特、以难点博流量,而是选择观众熟悉的有趣内容,扎实展现当地特色。该节目题材的创新使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纯娱乐类综艺节目,而是深挖节目的深层价值,通过斗智斗勇的奇趣欢乐,让观众在游戏中深入体验各种民俗文化。《跳进地理书的旅行》颠覆了以往的纯科普类节目的枯燥与说教,也摒弃了纯游戏综艺的过度娱乐化,而是将两者巧妙进行融合,在游戏过程中向观众科普地理知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在该节目第一季第一期中,观众在欣赏秀丽的风景之时,也需要跟随嘉宾完成旅行小测验,只有答对了题目,才能将旅行的吉祥物“南波小兔”养得更大,从而获得更多的旅行基金。此外,节目嘉宾每期都要通过写游学报告的形式,对本期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帮助网友进行“复盘”,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学习典范,对观众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2.3 以青少年群体为目标受众,个性化定制保障基础播放量
《跳进地理书的旅行》作为一档集数短的综艺节目,要想在短期内获得点击量和播放量,目标受众的清晰定位尤为重要。该节目以地理教科书为线索,将学生和对地理知识感兴趣的年轻人作为目标受众。清晰的受众定位易引发观众的文化认同。“认知是指人们获取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再加工的过程。”[5]该节目通过视听符号,以实地打卡的形式对抽象的地理知识进行重构与再现,满足了观众的求知欲望与需求。通过观看节目,观众能够在答题中获得体验感和认同感,不少网友表示,“文科生的DNA又动了”,答对题的喜悦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观众与该档节目的黏性。此外,节目组考虑到学生时间的特殊性,特地将该节目的播放时间选择在暑期,从7月2日首播,一个月内播完,特定时间段的“个性化定制”既保障了节目的收视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该节目的播出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
2.4 传播渠道相融,线上与线下联动的传播扩散
线上和线下传播渠道从“相加”走向“相融”,实现“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这也是当下国内综艺节目传播的必经之路。新媒体时代,一档综艺节目的传播与扩散离不开多渠道、多平台的联动。芒果TV利用其知名度为该档节目进行全媒体矩阵传播,有效提升节目影响力。截至7月31日,《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累计播放量1.16亿,豆瓣评分为9.2分。芒果TV利用其官方微博与“跳进地理书的旅行”官方微博进行同步宣传,与粉丝进行互动,扩大受众面。目前,“跳进地理书的旅行”官方微博粉丝量已超过15.1万,超话超1.4万,多次登上微博热搜榜单。“跳进地理书的旅行”官方微博也积极更新节目动态,通过答题和抽奖的方式跟粉丝群体进行互动。此外,著名主持人何炅在其主持的综艺节目——《不设限毕业礼》中利用自身的粉丝基础和影响力对该档节目进行推广,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该节目增加了知名度。再次,在抖音短视频平台,芒果TV利用其基础粉丝量为该档节目制作了宣传专辑,将节目中的高能场面剪辑成短视频,吸引观众观看节目。除了线上利用各大渠道与平台进行传播与扩散,该节目在线下还举办了点映会,节目中的嘉宾亲临现场与观众和粉丝进行近距离互动。
2.5 媒介漫游,赛博空间中的“城市漫游”
以往旅行类综艺节目往往会选择国外的名胜古迹进行拍摄,这种做法让许多观众有“距离感”[6]。《跳进地理书的旅行》选择大理作为拍摄剧情的场景,剧中的风土人情和秀丽壮美的风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云南大理之中,一起感受诗词里大理“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涟”的迷人景致,一同领略祖国山河之美。符号学奠基人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能指是形式,所指是内容和意义。在《跳进地理书的旅行》中,有很多这样的“符号”。比如,节目中的自然风景、建筑风格与美食作为视觉符号,建构起观众对于大理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而大理的民族音乐则作为语言符号,引起观众对大理民俗文化的好奇与近距离接触的满足。这几重符号共同打造了观众的感受空间,让受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也能够“云感受”快节奏时代的慢生活,“云品尝”大理的美食,“云体验”大理本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其独特的魅力与诗意。随着摄像机的视角切换,观众与8位嘉宾一同搭乘直升机前往巍巍玉龙雪山,以俯瞰的独特视角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直击地理变化带来的不同地貌,完成了一次赛博空间中的“Citywalk”(城市漫游)。
英国文化学者迈克·克朗指出,媒介在地方生产中扮演着加速器的角色。克朗表示,它加速了地方意象的生产,由媒介投射和创造的可想象的地方促使地理景观社会性转化,地方景观在媒介的参与下与彼时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传统社会中,地方通过地区约定俗成的行为,以“系物桩”的身份拴住和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有共同的经历[7]。而在以媒介为中介的社会中,媒介与地方合谋赋予了人类情感的在地性、物质性,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趋同化的数字行为弱化了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性,但是人们的情感却借由媒介塑造的地方意象得以表达,围绕地方产生了情感的聚合体,此时人们依然通过地方为自己定义[8]。由此来看,《跳进地理书的旅行》也充当着“媒介”的角色,向观众传递着丰富的信息。不仅如此,它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了一种组织松散、情感结构稳固的共同体。这一点从网上热追该节目的观众即可知。
3 结语
《跳进地理书的旅行》作为一档旅行类综艺节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的套路化、模版化、娱乐化的问题,在当下同质化的旅行综艺节目中突出重围。该节目将地理知识与旅行巧妙结合,以游戏的形式挖掘云南大理的文化内涵,以实地打卡的形式让观众身临其境地学习地理知识,以视听符号引领观众完成一场赛博空间中的青春之旅。《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的良好口碑与火爆“出圈”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旅行类综艺发展提供了“解题思路”和“破题之策”。品质优良的旅行类综艺节目需要寓教于乐,平衡趣味性和知识性,谨防掉进泛娱乐化的陷阱,不刻意制造冲突点和矛盾点、营造卖点,而是坚守初心,实实在在地传达正向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不断进行题材的创新、模式的突破,为观众提供具有深度的内容,旅行类综艺节目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