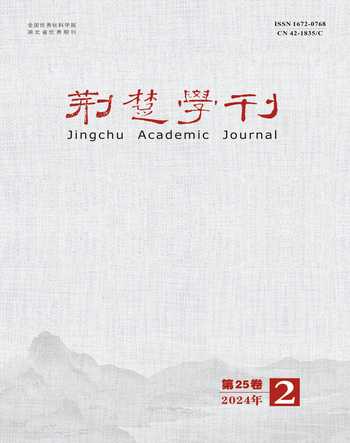“司命”形象及职能考
赵戈
摘要:早期司命以朴素天神形象出现。周王朝至战国时期,司命成为天子与诸侯共祭的神灵,分为公私之祭。金文、楚简与《周礼》中“司命神”神格和相应祭祀系统各有不同,皆不能简单视为同一;前人多遵郑玄注说,认为司命的多重形象是并列进行的,这在一定程度遮蔽了其在历史时序演变中的重要意义。汉代“司命”形象与职能的演化,从中可寻绎统治阶级与下层政治、文化和时代思潮互动的痕迹。
关键词:司命形象;祭祀;鬼神信仰;楚简
中图分类号:B933;K8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4)02-0037-08
“司命”一词,据出土文献,最早见于春秋早期( 1 )。魏晋以前多见于史书天官地理与祭祀部分(如《史记·天官书》《汉书·郊祀志》)。经汉代祭祀系统的整合,及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兴起,司命形象与职能发生较大变化。
诸家涉及“司命”相关的问题已多有创获。然关于“司命”形象时序上之演变与发展,以及背后凸显的时代背景,多仅是罗列史料后,简述其在文献中的形象,未作深入探查,遮蔽了司命在历史祭祀、民俗等文化史上的“活性”( 2 )。另外,学界多把《九歌》中《大司命》《少司命》中的司命与出土楚简和传世文献中的司命,简单化为同一。屈原《九歌》中的司命与楚简中的司命和孟姜壶铭文中的司命等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将双方简单联系起来并以所涉神祇对等研究的做法,尚存诸多困难。”[ 1 ]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探讨司命来源及自先秦至汉代以来其形象、职能发展演变的过程,审视其背后的时代文化意义。
一、秦汉以前的司命
秦汉以前,司命多以受祭神灵形象出现。周平王东迁后,统一尊奉的祷祀制度遭到破坏。战国时代,诸侯王好尚求仙长生,方士迎合造神,各国祭祀神祇升降纷繁。因此,面对各时段不同材料载录的司命形象,有必要进行司命源流考释。
(一)史料所见先秦司命源流考
司命何时产生并演变成祭祀对象,已稽古难征。战国时人认为司命是来自尧舜时代的远古神,能够延长人的寿命:“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辅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宝,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归之。”[ 2 ] 381-382(《隋巢子》佚文)传世文献中,司命首见于《周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载:“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 3 ] 645-646郑玄注引郑司农语,认为司命即“文昌宫星”,且是文昌第四星,贾公彦认为文中三礼“此祀天神之三礼,以尊卑先后为次,谓歆神始也。”[ 3 ] 646可见他认可司命为天神。《礼记·祭法》又称:“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 4 ]郑玄为《礼记》《周礼》作注,皆有“或曰”之措辞,贾公彦、孔颖达及后世学人疏解二礼时注意到了郑玄的困惑,是知至东汉时,司命的身份杂乱多混,郑玄已难明。今所见出土文献最早载“司命”的齐国齐侯壶铭文:“……齐侯拜嘉命,于上天子用璧、玉佩一司。于大无(巫)司折、于大司命用璧、两壶、八鼎。……”[ 5 ]铭文内容“上天子”“司折”“大司命”为祭祀典礼中的祭祀对象,祭祀规格和所用物品数量都有明确规定。春秋时期齐国的祭祀分为天神祭祀、地祇祭祀和祖先祭祀。周王室衰微,原本“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礼记·王制》)的礼制屡受挑战,诸侯王僭越祭天的情况并不少见,铭文中的“上天子”可认为就是天神祭祀[ 6 ]。
战国时期,司命出现频繁。一是见于诸子百家学说中。《管子·国蓄》:“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7 ]《庄子·至乐》:“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 8 ]《孙子·作战》:“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9 ]诸子学说中,司命由早期单一祭祀天神形象进入民间。粮食决定人民生死,帝王可御之于民,这是司命职能的具象化;司命能使骷髅复生肉身而活,是其职能的延伸,即掌管人類生死的天神神格下降至决定个人生死的人间鬼神;军队将领作为司命之“代言人”,更是司命神职的人格化体现( 3 )。
二是见于祭祀体系中。司命作为神灵祭祀中极为重要的一员,较为集中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楚地。楚地巫风盛行,神灵祭祀较为发达。仅就出土记载有“司命”之楚简列于下:
包山简(213):赛祷太备(佩)玉一环,侯土、司命、司祸各一少环。大水备(佩)玉一环,二天子各一少环,峗山一丑(钮)。
包山简(215):太、侯(后)土、司命、司祸、大水、二天子、峗山既皆成。
包山简(237):举祷太一膚,侯土、司命各一牂,举祷大水一膚,二天子各一牂,峗山一牯。
包山简(243):举祷太一膚,侯土、司命各一牂,举祷大水一膚,二天子各一牂,峗山一牯( 4 )。
望山简(54):举祷太佩玉一环,后土、司命各一小环,大水佩玉一环。归豹。
望山简(55):太一牂,后土、司命各一羯,大水一环,举祷二天子。
望山简(56):举祷于太一环,后土、司[命]……
望山简(128):……司命……
天星观简(7-02):司命、司禍、地主各一吉環(环)。
天星观简(13-02):择良日爨月,举禱(太)一牲,司命、司[祸]各一牲,……
天星观简(92):三月,赛祷化(太)一牲,司命、司祸。
天星观简(101)……司命、司祸各一……
秦家咀简(1):甲申之夕,赛祷宮幣(地)宝(主)一古(从豕),赛祷行一白犬,司命王父、王毋(母)……,酉(酒)飤祚之。
秦家咀简(11):赛祷于五碟(世)王父王母……,艳(地)宝(主)、司命、司巧(禍)各一肉(从歹),缨(理)之吉玉,北方一環(环)( 5 )。
河南省新蔡葛陵故城楚墓中发掘出葛陵楚简所记载“司命”更丰富:
葛陵楚简(甲一15):……于司命一(鹿),举祷于……
葛陵楚简(甲三4):睪(择)日于是兄(幾),态(赛)祷司命、司彔(禄)備(佩)玉掛,睪(择)日于……
葛陵楚简(乙一15):……公北、幣(地)宔(主)各一青義(牲);司命、司衍(祸)各一劾(鹿),举祷,曆(厭)之。或……
葛陵楚简(乙一22):又(有)敌(祟)見于司命、老褲(童)、祝獨(融)、空(穴)會(熊)。癸廠(酉)之日举祷……
葛陵楚简(乙二22)……[司]命一痒(牂),璎(缨)之以兆玉。
葛陵楚简(乙四97)……[地]宔(主)与司命,禮(就)祷璧玉兆……
葛陵楚简(零15)……[司]命一规( )……
葛陵楚简(零266)……[司]折、公北、司命、司衍(祸)……
葛陵楚简(零378)……[北]方、司命( 6 )……
齐侯壶铭文作“大司命”外,《楚辞》中再出现“大司命”“少司命”之称,观屈原《九歌》各篇所涉神祇,是为一组楚系神灵。就出土材料所在地,齐、秦、楚三国都有司命迹象,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司命已成为各国神灵祭祀的一员;齐侯壶铭文中祭祀与人的寿命有关,楚简中多司命、司祸共祭祀,也与人的寿夭有关,秦墓文中更有死生“尚命”之意( 7 ),说明早期司命与人的寿夭关系最为紧密,其职能即是司掌人的生死;楚简中“司命”与“太一”、“后土”和楚人祖先神一齐祭祀,神格当不会过低。但上述材料之“司命”,形象和职能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楚简所祀神之排列也各有不同,须作进一步辨析。
(二)先秦时期司命形象辨疑
周王室的衰微,祭祀权威随中央权力渐失效用。诸侯国不仅举行郊祀,还提升地方神祇的祭祀地位。战国时齐国祭祀地方“八神”,其中并无司命,且在春秋时已有祭祀“大司命”,故学者把楚国大、小司命视为楚国地方神祇的看法过于粗疏。司命形象的不同,可从司命相关的神祇神格分析、神祇排列顺序和神祇系统等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司命相关神祇神格、祭祀用品不同。齐侯壶壶铭文“大司命”前有“上天子”,楚简中出现“二天子”,学者认为“上”字即“二”字( 8 )。商周甲骨、金文中“上”与“二”形近,然前者上横稍短,后者则两行等长,齐侯壶铭文中“佩玉二司”之“二”与“上天子”之“上”明显不同。另,齐侯壶与楚简中祭祀顺序也不同,且祭祀规格及祭祀物有严格的区分。“上天子”用“璧”“玉備(佩)”,“大司命”用“璧,两壶、八鼎”,显然有等级之分。而楚简所见,如包山楚墓237号简和243号简,祭祀“司命”用“一牂”,祭祀“二天子”也是“一牂”;新蔡葛陵楚简“归備(佩)玉於二天子,各二璧”字样虽与齐侯壶相类,但物品数量明确,不能等视。楚简中“司命”祭祀用品有“牂”“少環”“羖”“鹿”等,与齐侯壶祭祀用品明显不同。因之,“二天子”与“上天子”不能等观,二者之“司命”也非一。
其次,神祇顺序与神祇系统也表明先秦祭祀神祇的复杂性。以《周礼》中“天、地、人”祭祀系统比观楚简所载祭祀系统,二者亦体现出不同特征。楚简中各楚墓主人或是王室,或是贵族,且时代有差[ 10 ];祭祀名类不同:“赛祷”“举祷”“就祷”等;楚简神祇组合有“太(一)-后土、司命-大水”“太(一)-司命、司祸-”“地主-司命-”“司命-(祖先神)-”等,学者普遍把“后土”“地主”解作地祇神,因“司命”多居其后与之共享祭品,则认为是一组地祇神( 9 )。事实上,这一结论并不能成为定说。楚简所记“太-后土、司命-”之例虽多,然是否符合《周礼》“天-地-人”祭祀系统,“太一”与“后土”的神格需要界定。先秦时期太一并未明确有天神之说,而要到汉武帝时。《史记·封禅书》: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11 ] 1666。
简中“太一”无法确定为天神,只能勉强视作至上神[ 12 ]。“天地人”顺序的祭祀系统便不成立,司命神格也就无法确定。再者,包山简及望山简所载“太-司命”组合后,尚有“大水-二天子”组合,祭祀规格相同。如包山简213、243,“太”和“大水”祭祀方式都为“赛祷”或“举祷”,祭祀物品也相同:“佩玉一环”或“一膚”,“司命”与“二天子”同为“一少环”或“一牂”,简文神祇排列及叙述方式明显存在把其分为两组不同神祇的意图。“太一”居前,说明楚人极为重视,然与“大水”祭祀规格等同,神格自然不会形成等差之分。可知楚人祭祀并未严格按照“天地人”系统,而是混杂有多种不同神祇组合的祭祀系統,因此李零先生把楚简神祇视为一般神祇和祖考两类。郭晨晖最新研究颇值得注意:“太、后土、司命为一组神灵;大水、二天子、佹山则为一组山川之神;楚之祖先神别为一组,……三祖神灵并没有严格高下之判,……并不是天神或者地示之属,而是一套职能神系统。……楚简中反映出来的神灵体系并不是依据天神、地示、人鬼三个层面进行划分,而是分为职能神、自然神、人鬼三类。”[ 13 ]近年来,学界对清华简《参不韦》《五纪》等简文的研究,又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特征( 10 )。
再者,屈原《九歌》中“大司命”“小司命”,也可为其在先秦至秦汉祭祀演变轨迹中提供一种说明。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注“司命”称:“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辅天行化,诛恶护善也。”[ 14 ] 82司命为星名之说始于二郑,洪氏依五臣之说,实未深究之。古今学者对大小司命的揭橥,喜以横向视角观之,泛言神格而各执己说,少有以历史动态眼光审读。故刘信芳先生提出包山楚简“司命”即《九歌》中的“大司命”和“少司命”之后,也不得不承认,传世文献记载的司命较为多义,二司命究竟是什么神无法确证[ 15 ]。大小司命神格和祭义,也能从历史所载中窥知一二:齐侯壶所述祭祀后,言“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气(乞)嘉命,用旂(祈)頁(眉)寿,邁(万)年無彊(疆),用御尔事。”孟姜祈求嘉命,是为天子与国家长寿万年,即公祭之义,结合铭文前半,天子命祭之礼中应有此祭义。依《祭法》,王七祀,有为群之祀和为己之祀,诸侯五祀,如王制。七祀和五祀皆祀“司命”,说明天子与诸侯公祭中,司命的祭义就是掌管天下群生之寿夭。《九歌·大司命》:“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 14 ] 69司命之分大小,概与天子和诸侯的公、私之祭有内在统一性( 11 )。
综上考论,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司命早期以受祭天神形象出现,使天子之民“不夭”。司命的出现,是先民“受命于天”与圣王崇拜的结果(参《随巢子》佚文)。商周文明的发展,统治阶层逐渐建立起早期政治制度形态,通过祭祀、礼乐等方面塑造自身权威,统御万民。司命神分管人民寿夭的神圣职能,恰是对早期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映射。
(2)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渐失国家祭祀话语权。各国出现越礼祭祀现象,又加入地方神祇而重新组合,齐侯壶铭文中“司命”与楚简中“司命”不可再等同视作天神,更不能简单对应《周礼》“天地人”祭祀系统。“司命”解释权的下移,神格与职能也相应发生变化。民间“司命史”、诸子学说中“司命”和楚简不同神系组合“司命”的出现,说明天神“司命”在春秋战国被纳入各国祭祀系统中进行改造。随着统治者在“天命”思想的神圣感中,开始渴求与“天”相接,追求成仙不死,故司命形象必然向着“人神”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以至于战国时期各方国的“造神运动”中,司命神格变得复杂难辨。
(3)《周礼》“天地人”祭祀系统中,司命属受祭天神,《礼记》中天子七祀、诸侯五祀皆祀司命,是知战国时各诸侯国祭祀之“司命”并非地方神祇(如齐国地方“八神”就无司命);《九歌》中大、小“司命”和汉高祖时晋巫、荆巫之“司命”,乃由周代七祀、五祀中公私之祭的“司命”演化而来。
二、汉代司命形象与职能的发展
汉代前期,战国文化传统尚浓厚。高祖初定天下,亟需确立统一的国家祭祀,作为先秦时国家祭祀天神的司命再度被确立下来:
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 11 ] 1658。
《周礼》卷二十“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句,郑玄谓:“兆日於东郊,兆月与风师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师於北郊。”贾公彦疏:“‘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阳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阳,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 3 ] 698-699南郊,即是天子祭天的最高礼,司中、司命是代表天子的阳,故享有天神的祭祀地位。武帝疾而医无效,游水发根上言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于是武帝下令安置在甘泉宫供祠:
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上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属,皆从之[ 16 ]。
神君,裴骃集解引:“韦昭曰:‘即病巫之神。”司命从属神君,可见原始司命神格已有所下降。《汉武故事》佚文载:“上祀太畤祭,常有光明照长安城如月光。上以问东方朔:‘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总鬼神者也。上曰:‘祠之能令益寿乎?对曰:‘皇者寿命悬于天,司命无能为也。”[ 2 ] 3919所载之事多不可信,然或反映出其时大致现实。武帝好祀鬼神、求长生,不可能于司命全然无知,东方朔之答,是知汉儒塑造君王“天命”的强大影响,司命由独立到从属的转变,也表明其神格有所降低。
又郑司农注《周礼》:“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郑玄言大祀又有宗庙,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岳,小祀又有司中、风师、雨师、山川、百物。作为国家最高祭祀(大祀)的司命神,汉以后形成稳定的祭祀神系格局,祭祀时间、场所进一步完善,趋向稳定,如“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新唐书·礼乐志》)而小祀的“司命”神格下降,也只是宫庙神灵祭祀的调整而已。国家祭典中的司命神在汉以后依统治者所需而微变,其“活性”之低,说明汉帝国制度文明的高度成熟与帝制稳定维系的绵长特质,也印证了皇权统治通过祭祀系统认定其统治合法性的多重考虑。汉制于后代的影响,于祭祀礼制可见一斑。
(一)司命与星名
司命与星名相联系,始见于汉代。《史记·天官书》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 11 ] 1544鄭玄注《周礼》,引郑司农言,“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而司马贞引《春秋元命苞》称:“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 11 ] 1544贾公彦作疏又引汉代星占材料,说明自西汉中后期至东汉,诸如《甘石星经》等一些天文星占、谶纬学说中,已经普遍把祭祀天神与星象相结合进行理论阐释,为帝王服务。
先秦史料中,尚未见司命与星名结合之说。然战国时楚人已有文昌信仰,又有司命信仰。两种信仰结合,很可能是经战国至汉代星占家与巫祝相关涉发展结合的[ 17 ]。因此可推知,天文星象家的这一工作,最迟在战国已经开始。至东汉,司命纳入星官的体系已趋完善,如陕西靖边杨桥畔东汉墓及渠树壕墓中所见壁画,有完整的星象神祇系统,司命对应的星辰与传世史料得以互相印证[ 18-19 ]。汉以后,司命之论以郑说为圭臬,以致司命为星名不知缘由。然亦有人对此质疑之,如元人苏天爵编撰的《元文类》中载有吴澄《书李伯时九歌图后》,其文:“司命亦天神也,《周礼》所祀有司中、司命,注以为星,非也。司命者,万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周礼》一为司中、一为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之命也。”[ 20 ]吴澄之说显然追溯至上古司命原始形象和职能,可见,古人并非把二者混为一谈,司命由天神形象进入星象家视野,有内在的承续关系。
(二)道教神仙洞府体系中的司命神
道教神仙体系吸收司命神,来自国家祭祀和求仙活动。道教徒认为,修行者可以通过服食仙芝灵草进行升仙。《云笈七签》卷114载:“食金阙燕胎玉芝者,位为司命。……子尽食之矣,寿齐天地,位为司命,授东岳上卿,统吴越之神仙,综江左之山源矣。”[ 21 ] 2537道人修成司命神后,由方诸青童统领,各神仙有等级之分,并有自己处理事务的府第。上清道教体系中,首先构筑了神仙洞府体系。《云笈七签》“洞经教部”载《大洞真经》云:“三元隐化,则成三宫。三宫中有九神,谓上、中、下三元君,太一、公子、白元、无英、司命、桃康,各有宫室。”[ 21 ] 227可见,太一与司命作为祭祀神祇之一,皆成为道教谱系神。《太平御览》载《道藏》中《黄庭内景经》曰:“霍山下有洞台,方二百里,司命君之府也。”[ 2 ] 189关于司命职权,《九天三茅司命仙灯仪》中称:爰有真君,实为司命。纠仙凡之功过,掌生死之权衡,纤细不遗,毫分无失。治赤城而册编九锡,佐青岳而职隶三峰[ 22 ] 573。早期的司命天神职能单一,而道教司命神不仅纠察仙、人两界功过,还要衡定生死。因为人由三元养育,天神地祇和三界共同备守,而司命神“守人心中定算,则注其年寿也。”[ 22 ] 430人的年寿既通过司命定算,那么司命则可通过赏善惩恶增减:“人有恶言,司杀白之于司命,司命记之,罪满即杀。”[ 21 ] 724众生如果放纵身心、杀生犯罪而不信奉仙君神祇,就会“罪殃深重,为十直之神司命司录写其罪犯,上奏天府,历劫缠结,无由解脱。”[ 22 ] 505
武帝时儒学定为一尊,道家一派的“天命”理论逐渐被排挤出中央,于是转而潜入基层传播教义。故道教神仙体系中的司命仙君也被塑造转向监察人间的善恶,记录凡人的罪业,或定算命籍,有时行使杀伐权,但更多地是向上级报告,即“上奏天府”。道教徒构建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神仙官府体系,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借鉴自国家官僚体制,又用以吸收和管理信徒,正如魏斌先生所言:“说起来,司命就是仙界的官吏。就像民众通过官吏才能与朝廷接触一样,司命扮演的正是一个权力媒介的角色。”[ 23 ]
除了神仙官府体系中的司命真君外,道教进一步延伸了“司命”的形象及职权范围。《太平经》中有时也把“司命”看作“身体神”[ 24 ] 14-15,如卷114载:“乃为人寿从中出,不在他人。故言司命,近在胸心,不离人远,司人是非,有过辄退,何有失时,辄减人年命。”[ 25 ]余英时先生指出,司命有时泛指“掌人命”而非特定的司命神。“因此人体内亦有称作‘司命的神,它切近地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并决定人寿。”[ 24 ] 71-72可知,在道家的神鬼体系中,“司命”不仅管理人在阴间的命籍,还管理阳间的人以及人的“精魂”。司命将人的寿夭与个体行为连接起来,将人的生死赋予了某种宗教性质的伦理价值评判[ 26 ]。
(三)民间司命及灶神
文化阐释权的下移,使得“司命”形象也常常活跃于民间风俗中。应邵《风俗通义》“司命”条下载:“槱者,积薪燔柴也。今民间独祀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檐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汝南余郡亦多有,皆祠以月者,率以春秋之月。”[ 27 ]“司命”形象在民间的变化,反映出其越来越具现世世俗性,以及其更加具有“人性”。王充《论衡·解除》:“国期有远近,人命有长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则王者可竭天下之财,以兴延期之祀;富家翁妪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寿。”[ 28 ]汉代的这种祭祀风尚,是自上而下浸淫的。不同的是,底层民间,“祭祀有很强的功利性(即趋吉避凶),在汉代信仰的众多神灵中普通百姓更加关注与自己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小神,如社神、灶神、门神、司命等,对他们的崇拜信奉构成了汉代民间神灵崇拜的主体。”[ 29 ]《列仙传·木羽》载:木羽者,钜鹿南和人也。母贫贱,常助产妇。儿生,自下唼母,母大怖。暮梦见大冠赤帻者守儿,言“此儿司命君也。当报汝恩,使汝子与木羽俱仙。”母阴信识之[ 30 ]。从“母贫贱”到“报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这样的叙述,可想见民间“司命”祭祀必然会盛行。
此外,“司命”与灶神结合,也始自东汉。王国维《东山杂记》中有详细论述:
南方人家敬事鬼神,谓之东厨司命,此实合古代五祀中之司命与灶为一也。……汉时司命之祀极盛,与今日祀灶无异也,不知何时始与灶合而为一神。按俗传《太上感应篇》,此书之作当在唐宋间,而其中已云司命灶君之神。……北宋时确已谓灶神为司命。然原其混合之始,当在汉晋之交。……郑注又言今时祠司命,行神、山神,门户、灶在旁,则汉时已并五祀而一之,习久相忘,遂反配为主也[ 31 ]。
王氏认为灶神与司命在民间信仰中混合,可能早在汉晋之交。晋时“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葛洪《抱朴子·内篇》),与汉代民间道教司命职能何其相似。灶神司命不仅监察人间善恶,享受人间祭祀的同时,也有奖惩和护佑百姓的职责。很明显,无论是道教的司命真君,还是灶神,其形象都有浓厚的世俗统治官僚色彩。西汉末,王莽擅权,司命就出现于新政的官僚体系,李贤注“司命府”言:“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纠察。”[ 32 ]以“司命”名作官僚组织,至明清依然可寻迹。
综上所论,对于司命在秦汉时的变化有以下几点认识:
(1)汉初天下初定,高祖重新整合战国文化遗产,建立新的汉王朝礼乐制度,司命作为先秦国家祭祀中的天神得到继续尊奉,后世继之。
(2)西汉时期,司命在星象家、谶纬家、儒生、方士、神仙家和道家等学说中被引入,甚至被延纳入中央官僚体系中,发生多重变体。这些群体皆以帝王所需为目的,旨在宣扬其思想受帝王青睐,因此东汉以前,各家改造的司命具有浓厚的政治性意味。星象家对司命等神祇的改造,自战国时代已开始,至东汉形成完整的体系;而武帝朝儒生、方士活跃,经学谶纬兴盛,加之“天命”学说达到巅峰,故会出现东方朔与武帝问答言司命地位之变化。相应地,这一时期君权的无限高涨,司命职能尽管仍是司掌“阴阳化生万物之命”,但帝王之命寿直承于至高天,司命已无法干预。
(3)东汉儒学渐微,中央对地方的文化控制逐渐削弱。被排挤出中央的道教极力发展自身学说,司命成为道教神鬼体系中的重要神,职能随之扩张,不仅司管神仙和凡人生死,还要纠察凡人过错。道教沉入民间,又使民间道教信仰异常活泛,加之底层现实生活越加艰苦,其生死观(诸如东汉养生风气、死后生活等信仰的流行)中,“司命”形象出现身体神、渐与灶神结合和独祀的现象,自是情理之中。
三、结语
司命由早期巫祝为帝王天命创造的天神体系中,被纳入方国祭祀的神灵体系重新组合,地位有所下降,神格也渐模糊。楚简中“司命”神格历来难决,诸家说法相抵牾,故不可片面视之。汉帝国一统后,司命作为国家祭祀天神的身份再度受尊崇。由于汉代帝王长生思想的需要,方士、星象家、道家和儒生等群体又对其进行不同程度加工。星象家把司命纳入天官星象体系经战国到东汉;神仙家、谶纬家、儒生和方士对司命的改造盛在西汉;而道教及民间司命信仰也始自西汉、兴于东汉及后世。司命形象及职能的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可寻。另外,天官星象系统、道教神仙洞府体系中“纠察过错,籍录善恶”的司命神、始于王莽新政的“司命府”,都與汉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和对民间控制紧密相关。从司命职能的变化来看,汉代星象家言管命籍、神仙家言助成仙、谶纬家讲“通命运期度”( 12 )和民间讲福佑等,都不离人的生死之命。东汉及以后民间司命信仰的流行,寄寓着庶民阶层对于“永受嘉福”更深切的俗世愿景。
注释:
(1)见齐侯壶壶壁铭文。关于齐侯壶(又作洹子孟姜壶、孟姜壶)年代问题,众家说法不一。笔者梳理后,概括有三:一是孙诒让、郭沫若和杨树达等先生持春秋晚期说;二是李学勤先生根据器型与内容,提出春秋早期的商榷意见;三是孙刚、张振谦先生又有春秋早期后段说。若再考虑《周礼》《礼记》记载问题,可推测“司命”至迟在春秋早期,已成为神灵祭祀中的形象大量出现。
(2)如刘信芳、晏昌贵与杨华诸先生的相关研究中,对出土楚简与传世文献中“司命”,皆模糊指认为同一类形象,未作辩证分析。参见刘信芳《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祇》(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杨华《楚简中的诸“司”及其经学意义》(载《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1期)、晏昌贵《楚简所见诸司神考》(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9期)。
(3)此论断还可据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1出土简文加以说明,秦简记载一位名叫丹的人死而复生之事,有“与司命史公孙强北出赵氏之北”字样,学界多认为“公孙强”称“司命史”,就是代行司命神掌管人生死的职能。参考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载《文物》1989年第2期)。
(4)本文所录包山简文,参考自陈伟《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不复赘述。
(5)本文所录望山简、天星观与秦家咀简简文,除参考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外,兼吸取晏昌贵、杨华、郭成磊等人研究成果,不另具注。
(6)本文所录新蔡葛陵楚简,参考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载《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7)墓文载:“……三年,丹而复生。丹所以得复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论(与)其舍人尚(掌)命者,以丹未當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狐穴,屈(掘)出。……”见孙占宇《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8)杨华先生以字形、祭祀规格对比,认为二者应为同一,李学勤先生与此同。见杨华《楚简中的诸“司”及其经学意义》(载《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1期)。张振谦先生认为,“上天子”“二天子”与“司命”祭祀顺序不同,故二者不能视为同一。徐义华先生从张氏之说,认为齐侯壶的“大司命”就是楚辞中的“大司命”,是天神,赞同古人把《周礼》《礼记》《庄子》等先秦时期司命作天神。见张振谦《洹子孟姜壶初考》(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徐义华《洹子孟姜壶新释》(载《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9)陈伟先生认为:“简书中的神祇排列大致以类相从。太为天神,后土为地祇。司命列于后土之后,似不致又是天神。”见陈伟《湖北荆门包山卜筮楚简所见神祇系统与享祭制度》(载《考古》1999年第4期)。史培争、李立认为,楚简中司命位于“太”“后土”之后,祭品的规格低于“太”,表明与后土共享祭品的司命,也应该与后土相同,属于地祇。参史培争、李立《论包山楚简“司命”与〈九歌〉“二司命”的联系》(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2期)。汤漳平先生通过对比《史记·封禅书》《九歌》和楚简三组神祇,认为具有惊人的完整性和对应性,三组神祇同者多异者少,祭祀顺序相同,分别是天神、地祇和人鬼,司命归于地祇之列。见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
(10)如贾连翔先生认为《参不韦》所涉神祇系统、《五纪》所涉神祇系统与《周礼》“天地人”系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一新结论正可佐证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多样的祭祀系统。贾连翔《清华简〈参不韦〉的祷祀及有关思想问题》(载《文物》2022年第9期)。
(11)此说以曹胜高先生之论最有力,即“天子、诸侯专祀司命,用于护佑其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天子、诸侯所公祀者,护佑群姓百姓,祀为大司命;天子、诸侯所私祀者,护佑于己,祀为小司命。”曹胜高《七祀与〈大司命〉〈少司命〉的祭义》(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曹说以前,汤漳平已提出类似论断:《封禅书》所载各巫祭祀对象皆不同,唯晋巫和荆巫同有司命,且不分大小,实即《九歌》中大小司命。关联二者所论,或若合符节。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
(12)纬书《春秋佐助期》称:“司命,神,名为灭党,长八尺,小鼻,望羊,多髭,臞瘦,通于命运期度。”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页)。
参考文献:
[1]史培争,李立.论包山楚简“司命”与《九歌》“二司命”的联系[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2):36-41.
[2]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周礼注疏[M].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礼记正义[M].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799.
[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8)[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212.
[6]何凤鸣.春秋齐国祭祀礼俗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20.
[7]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1259.
[8]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619。
[9]郭化若.孙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96.
[10]郭成磊.楚国神灵信仰与祭祀若干问题考论[D].西安:西北大学,2016.
[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2]田天.西汉太一祭祀研究[J].史学月刊,2014(4):39-51.
[13]郭晨晖.楚简“太一”性质考[J].中国史研究,2020(2):14-29.
[14]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刘信芳.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祇[J].文学遗产,1993(5):11-16.
[16]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220.
[17]吴成国,潘贝.关于湖北文昌信仰历史与现状的调研报告[J].文化发展论丛,2015(2):207-225.
[18]邱雅暄.陜西靖边杨桥畔东汉壁画墓司命、司禄考[J].文博,2020(4):60-69.
[19]段毅.渠树壕壁画中的星象与神话[J].考古与文物,2020(2):69-79.
[20]元文类[M].苏天爵,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515.
[21]云笈七笺[M].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22]上海书店出版社.道藏:第三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23]魏斌.“山中的”六朝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06.
[24]余英时.东汉生死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5]太平经合校[M].王明,编.北京:中华书局,1960.
[26]程乐松.身体、不死与神秘主义:道教信仰的观念史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96.
[27]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384.
[28]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1043.
[29]张影,邬晓东.两汉祭祀文化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7:55.
[30]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107.
[31]王国维.王国维学术随笔[M].赵利栋,辑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
[32]范晔.后汉书[M].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73:828.
[责任编辑:王妍]
———楚简制作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