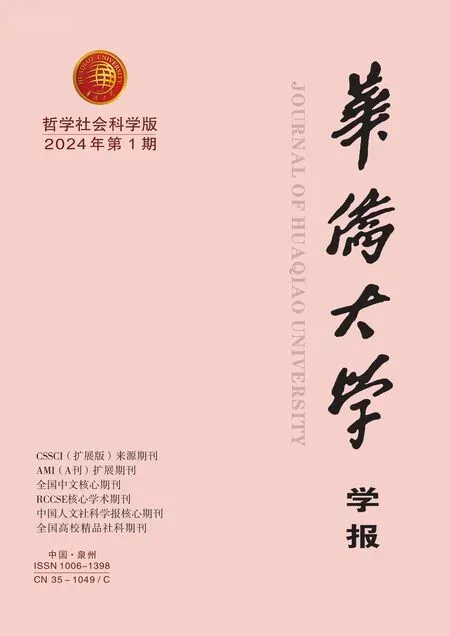公共风险谣言的行政治理
——以实质法治为视角
○黄 城
一 问题的提出
新冠疫情期间,各类相关谣言纷至沓来。“戴多层口罩才能防住病毒”“病毒会通过宠物进行传播”“湖北产的大米上可能有病毒,不能吃”等不实信息在网络上不时被捧上热搜。据统计,从2020年1月20日到2月5日晚上十点,仅十余天时间,网络上出现的此次新冠疫情谣言数量就超过了16万条。(1)元元学姐:《16万条疫情谣言!新传学子该如何思考?》,知乎,(2020-02-08)[2022-01-11],https://zhuanlan.zhihu.com/p/105682503.为何有关谣言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传播量级?主要原因在于与新冠疫情及环保、股灾、金融危机等类似公共事件有关的谣言是一种公共风险谣言,其与针对个人的谣言相比,跟社会问题联系得更为紧密,与人们日常生活更息息相关;且因公共风险事件往往突发,有关谣言的传播范围、社会影响、复杂程度都会显得更甚;这种“突发”过程往往还伴随着人们认知能力的不足——不仅普通民众,政府和专家可能也存在这种问题。社会性、突发性、认知性不足这三个公共风险谣言的基本特征,恰好对其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
如果细究更为实质的部分,公权力部门处理公共风险谣言的态度其实隐含着两种相左利益的平衡——一边是言论自由的权利,一边是政府行政规制过程中促进的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2)[美]欧文·M.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刘擎、殷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页。这不同于与个人相关的谣言中一方自由表达权和另一方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公共风险谣言不是私权与私权的冲突,而是私权与公权的权衡。前者受私法调整,而后者受公法调整。谣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言论自由权的行使——法的本质以“自由”为最高的价值追求。而对公共风险谣言的法律规制则是为了公共秩序的维护,又体现了“秩序”的价值。法的其余价值以法的秩序价值为先决和基本条件。法的秩序价值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3)柳亮、刘景臣:《自由、秩序与法治》,《求索》2009年第9期,第30页。为了避免在扼制公共风险谣言的过程中也抹杀了适宜言论,公权力应该对言论自由、监督权与公共利益实行权衡。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我国《宪法》第35条都确认了人人有发表意见的言论自由,由此足见对言论自由权的珍视已经成为国际共识。言论自由可以促进个体自我成就,维持社会稳定和变革之间的平衡,(4)Thomas I.Emerson,“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First Amendment”,72 (5)Yale Law Review(1963),pp.877-956.还可以为真谛的发现和彰显提供必要的社会土壤。(5)[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鲍容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7页。社会大众的思想虽然有时会出现错误,但如果借此禁止公民发表言论,那么人类社会就不能建立起良好运行的民主制度。禁止公民发表言论所导致的寒蝉效应会对真相的发现与挖掘造成一定的阻碍。这种风险使得有识之士通常会建议政府给市面上流传的谬误留下一定的空间,哪怕这些谬误可能产生恶劣的影响。(6)[美]卡斯·R·桑斯坦:《谣言》,张楠迪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0、12页。言论自由权作为一种经过宪法认可的权利、甚至是“一切权利之母”,法律对其限制必须采取一种谦抑的态度。(7)王松苗:《防治网络谣言:法律的张力与效度》,《检察日报》2012年3月11日,第5版。
在疫情这类公共风险事件期间,言论自由权发挥着更为显著的发现真相的作用,且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监督面向。部分公共风险谣言实际上起到了倒逼公权力机关回应诉求、及时决策的作用,表达了一定的公众意愿。当善意的言论通过互联网等传播渠道辐射式向外散播,引发社会舆论的大量关注,从而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事件与责任方产生一定的舆论压力时,会充分表现为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功能,以保障个人及社会的合法权益与诉求。(8)周裕琼:《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66—267页。民众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件进行监督检举,也可共同关注不同类型的案件,结合媒体的声音力量和影响力,引发从线上到线下影响现实案件进程的强大力量,其正面影响不容小觑。(9)谢燕:《在自由与责任之间:网络谣言的法律制裁与反思》,载谭世贵主编《法之思:浙江省首届法科生大学生征文比赛获奖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9页。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一部分所谓的“公共风险谣言”并不存在言论自由权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张力,其本质上反而是互补的。这就要求仔细划分公共风险谣言与言论自由权之间的界限。
在行政主体如何依法治理谣言这个问题上,目前学界主流观点可以分为两派。一部分学者认为保护言论自由权应优先于对谣言的行政管制。王颖吉认为,依法治谣和保护言论自由之间需要遵循“保护”优先于“限制”的原则。在保护表达自由时,保护是常态,限制或禁止是例外。(10)王颖吉、王鑫:《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治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张振亮进一步提出,在一些情况下,谣言起到了一定监督公权力部门的正向作用,对于这类言论必要时应予专门保护。谣言的公共治理更应该关注的是疏导和防范,而不是管制和惩罚。(11)张振亮:《网络谣言多维共治法治化的路径》,《新闻爱好者》2018年第2期,第26页。李若建则认为,把事件简单归因为坏人造谣,然后惩罚造谣者,是平息谣言最简单可行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无法真正杜绝谣言。(12)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6页。张书琴从反面提出,规范言论自由的法律手段也会产生“寒蝉效应”,伤害言论自由,可能会影响那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对事实的揭露。法律对谣言的规制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13)张书琴:《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反思》,《学海》2014年第2期,第167页。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治理谣言需要的是加强行政管制。王勇认为,应对谣言需要依法严惩造谣传谣者,加强信息内容管理。(14)王勇:《别让网络谣言成为突发事件的“次生灾害”》,《人民论坛》2013年第20期,第59页。湛中乐、高俊杰认为,应完善相关立法,加大对造谣传谣者的惩罚力度。(15)湛中乐、高俊杰:《论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第154页。范卫国进一步细化,提出造谣者产生的损失或获得的利益通常高于行政处罚的力度,依靠现有行政处罚难以给造谣者以足够威慑。(16)范卫国:《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英国经验与中国路径》,《学术交流》2015年第2期,第98页。谢永江、黄方则从执法角度认为政府事后对造谣者惩处不力,过半的造谣者未受到法律制裁,导致不足以震慑造谣者。(17)谢永江、黄方:《论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87页。
其实这两派学者的争论本质上还是围绕在行政主体对公共风险谣言的依法治理究竟是应该更侧重于言论自由权还是公共秩序的问题,也就是这二者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定:应该给予言论自由权更为宽泛的空间,还是更关注于公共秩序?在秩序与权利之间,实现公共风险谣言的有效治理与规范治理的平衡,需要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性和强制力,确认每个社会成员的言论表达范围,排除来自非法力量的强制和侵害。(18)卢博:《网络谣言的甄别与行政规制》,《理论月刊》2021年第1期,第136页。行政主体在进行公共风险谣言治理的过程中,应当秉持法治理念,依照已有法律规范进行执法,防止为了单纯地追求治理效果而超越法律框架、以行政取代司法的情况出现。(19)王海军:《论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中州学刊》2014年第7期,第71页。在此,依法行政不仅应是一种形式上的法治,还应该是一种实质上的法治。这就要求行政主体在治理公共风险谣言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合法”,还要“合理”。实质依法行政要求行政主体不能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权力被滥用或者运用得不合理,这种行为就应该被指责为非法行为。公权力的行使应正当且合理,与行政法的规定和精神相符合。(20)[英]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2、56页。
行政法自诞生以来就以权利为价值基准,而不以权力为价值基准。行政法控制权力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21)孙笑侠:《论法律对行政的综合化控制——从传统法治理论到当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期,第384—385页。行政法的存在就是为了控制权力以规制政府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差错,因此行政法常常将精力专注在保障相对人正当权益方面。国家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不得任意渗透到社会,滥用权力从而侵犯个人自由和财产。(22)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75、221页。具体到疫情这类公共风险谣言的治理之上:如果行政活动仅仅以公共秩序为导向,而不受法律的实质控制,就只可能有行政技术,而没有行政法治;只有赋予在公共利益反面的私人利益以法律权利,并保障这种权利,行政法才有产生的基石。(23)[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4页。因此,实质依法行政其实是从行政法的权利本位思维衍生出来的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合法又合理的要求,本文的实质法治语境也在于此。在执法环节上,应当把保障民主与权利作为首要目的,这主要就是要求执法者具备“权利本位”意识,讲究办事民主、公正、效率(或称便民)。(24)孙笑侠:《“权利本位说”的基点、方法与理念——兼评“法本位”论战三方观点与方法》,《中国法学》1991年第4期,第53页。而在过往的公共风险谣言的行政治理过程中,有关公权力机关往往运用的是形式法治路径,即只注意到了形式上对有关行政法律法规的遵循,而没有关注到行政法的这种实质内核。这不仅与我国行政法的基本精神不符,从现实角度而言也不利于公共风险谣言的行政治理。因而,本文就是意在从行政法的基本精神与实际情况出发,以实质法治为坐标,结合依法行政和执政为民,给予公民权利以更大的空间,以新冠疫情谣言为例,探求公共风险谣言的行政治理方向与举措,以期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二 政府公信力与公共风险谣言治理中的实质法治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出于“先见之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建立在先定义后理解基础上的。也就是人们会率先识别自身经历和环境已有定义的事物,并按照已有的刻板印象去认知。(25)[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7页。具体到谣言问题上,桑斯坦认为,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之前既有的想法。这就是说,谣言的传播与否,部分取决于这则谣言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们已有的知识。这被称之为“前见理论”。人们的很多信念都来自于自身已有知识产生的希望、目标和欲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信念是有主观偏好的。某种说法可能会使人们感觉舒服,而其他说法会令他们感到痛苦。因而,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一些群体有强烈的动机接受某些谣言,而其他群体会以同样强烈的动机拒绝。在一些群体中被广泛相信的谣言,却会被另一些群体嘲讽讥笑。大量研究证明,人们会去否定那些与他们最深的信念相冲突的论断,以此来减少认知不和谐。而对于那些身在谣言中的人,回音室效应强化了对已经被接受的谣言的相信程度。这说明,既有知识在抵制和助长谣言上同样奏效。(26)[美]卡斯·R·桑斯坦:《谣言》,第26—28页。因而,在谣言的行政治理问题上,行政主体治谣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们对其行政行为的前见。因此,最重要的是防止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公众产生对政府的不良前见,从而导致治谣失灵。“凡是政府说是就不是,凡是政府说不是就是”是这一现象的鲜明表现。谣言中其实蕴含着民意,谣言的泛滥从某种意义上正是源于政府在民主法治这一环上的缺失。毕竟谣言能否在人群中泛滥开来,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煽动人群情绪的水平决定。(27)[美]卡斯·R·桑斯坦:《谣言》,第97页。解决谣言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惩治谣言的制造者,而是要尽其所能消除谣言产生的土壤,使谣言没有存活的条件。(28)蒋德海:《法政治学要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4页。这就要求政府在治理谣言的过程中树立一个良好的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即政府忠实执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公务权力,从而赢得社会大众肯定和认同的能力。其通常表现为政府行为的公正性、透明度和声誉度,以及政府对公众的感召力、向心力和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赖、拥戴感。政府公信力的提高有助于社会大众对政府工作的拥护,政府的执行力在公众的配合中也会提升。反之,如果政府的公信力不高,社会大众对政府工作的配合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弱化政府的执行力。(29)江必新:《贯彻十九大精神加快行政法治建设》,《求索》2018年第1期,第9页。“法治国”要求政府行为合法,这是一切“政府承诺”的前提条件,更是塑造和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基础和最为重要的部分,这关系到社会公义层面的普遍“公信”(30)张贵峰:《守法是最根本的政府公信力》,《法制日报》2012年8月10日,第7版。。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参照过往经历而形成的有条件的内心预期,信任某人意为对某人了解或自以为对某人了解,尤其是了解其目的与动机,期待其可以和自己的隐含利益统一或大致统一,而不是依靠这类信任关系反过来侵害他人的利益,这是信任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反映到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如果政府依法行政,人民可以凭借法律的稳定性获得一种平稳的预期,从而会更加信任和拥护政府;反之,人民就会对政府产生怀疑。政府应合法且合理地使用权力,这是政府公信力的应有之义,因为违法的政府自然无法与诚信挂钩。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诚信,以“公共利益”为幌子,实则竞逐自己的私利,变“法治”为“人治”,对政府公信力有极强的破坏作用。(31)姜明安:《推进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新要求》,《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1期,第17页。作为一个以民为本的现代政府,依法行政,从微观层面看,是政府本身的义务所在;从宏观层面看,是一种塑造和改善政府形象的重要方式。如果对一些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以一种放任不管的态度,任其野蛮生长,久而久之,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威严、大众的公共德性都会遭到破坏。
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可见依法行政对于政府公信力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树立政府公信力就要求政府以一种实质法治的方式来进行谣言的治理,而不仅仅是形式上遵从法律。这很鲜明地表现为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应该既“合法”又“合理”,即行政机关不应该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应以公民权利为限。因为,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意愿与能力,直接影响到政府公信力的高低。政府公务员应掌握权利思维和方法,即尊重和保障人权,善于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32)孙笑侠:《法律思维方法的“器”与治国理政的“道”》,《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第7页。面对谣言,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首先要做的不应该是定性,而是意识到这是大众的自由表达权:引导而不是处罚,疏导而不是堵塞民意,才是治理谣言最为有效的方式。过于强调管理的行政权力而忽视公民的权益保障,会导致治理手段与权益保障的不平衡,也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反映到治理公共风险谣言的问题上来,如果政府在治理公共风险谣言的过程中总是忽视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保护,动辄以公共秩序为名滥用一些行政措施来损害公民的个人权益,首先会让民众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漠视。而政府对公众权利的迎合程度又会影响着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与满意度。另外,由于在公共风险事件中,政府也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如果断然对谣言进行定性,事后发现定性错误,“谣言”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会更加挫伤政府的公信力,人们将不再信任政府的辟谣行为,从而导致后续政府治谣的失灵。一些民众之所以更倾向于相信谣言,正是因为有关部门对一些公众关注的重大事件采取一味处罚兼瞒报、谎报的措施,对于信息公开一再拖延,让他们产生了较差的心理感受,给谣言提供了生存空间。这就要求政府在治理公共风险谣言的过程中要更偏向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做更多的限缩性解释,这也符合现代“民权本位”的法治观念。由此,实质法治要求公共风险谣言的行政治理采取一种更为柔和的方式。
三 实质法治治理路径一:审慎认定与处罚公共风险谣言行为
在当下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公共风险谣言往往借助网络平台传播,呈现出了不受时空局限、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信息发布成本低的特点。并且由于自媒体的发展,每个人在网络上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33)[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205页。谣言由过去的“点—点”或“点—面”传播转变为“点—面—面”的多重传播。互联网存在的沟通瞬时性特点又使得群体意见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加强个人对一定信息的看法,(34)[美]卡斯·R·桑斯坦:《谣言》,第57页。这被称为“群体极化”现象。但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政府抛弃法治化行政方式的理由,在公共风险事件期间也要遵循行政法的相关原则、规范执法,使行政行为具备合法性、正当性。如前文所述,所谓的“谣言”有时候也有正面价值,可以起到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倒逼公共风险事件的真相。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言论,理应得到最为强力的宪法保护。(35)Cass R.Sunstein,“Pornography and the First Amendment”,35(4)Duke Law Journal(1986),pp.589-603.在此,对公共风险谣言的惩戒应该采取一种事后治理的方式,而不是预先治理,这也符合现代法治行为导向的要求。此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6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第3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在对公共风险谣言进行认定与处罚的过程中,应尽量采用柔性策略,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以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梳理目前有关的法律规定,《宪法》第51条规定了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社会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明晰了公民个人权利在社会利益前的边界。《邮政法》第37条、《电信条例》第56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14条、《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第37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条、《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第17条、《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第9条、《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第6条、《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5条、《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第38条都对“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做出了禁止性规定。但这些规定都过于原则性,缺乏具体的行为规制条款,发挥的更多是一种劝导性作用。目前,有关法律法规中最具实际执行价值的还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一)项。基于行政法实质法治的精神——合法又合理,应首先对该条文进行教义学上的限制解释,使其局限于条文的核心含义。毕竟与公权力的违法行为比较,普通公众违法行为的罪恶要轻得多。(36)Olmstead v.United States,277 U.S.438 (1928).进而,在对其进行限制性解释的基础上,再来谈相关的合理性问题。这是一切法学研究的前提要求与应有之义。由于公共风险谣言的有关行为不属于直接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所以不应该受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的规制,不需要快速、从重处罚。在此,从我国《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二款规定的公正原则和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第一款规定的比例原则出发,以公共风险谣言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四个角度对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一)项进行分析,以做到过罚相当。
(一)公共风险谣言的主体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该项并没有对公共风险谣言的主体作出特别的规定,即只要求行为的主体达到责任年龄且具有责任能力。但是其中有一些内容依然值得阐明,在此会适当围绕其他三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
公共风险谣言的主体可以分为三类:谣言制造者、谣言发布者和谣言传播者。谣言的产生必须经过造谣和传谣这两个过程,只有造谣而无传谣是不能被称为谣言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只对传谣行为做出规定,对造谣行为并没有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谣言制造者只是制造了谣言,却没有对外散布,他就不应受到行政处罚。在谣言发布者和谣言传播者之间也要进行区分,前者对外发布了谣言,而后者虽然不是谣言的源发者,却对谣言进行了转发。如果前者的行为并没有达到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就不应该受到行政处罚,而如果后者的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行政主体对公共风险谣言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主要应通过哪个主体对外造成了实质负面影响来判断。此外,有些传播者可能不仅仅只是提供信息,还会融入自身情感与观点,利用自身想法对谣言再次阐释和建构,从而使得谣言发生“变异”(37)吴贵森:《网络谣言认定及治理制度立体化之初探》,《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68页。。这种发生了实质性改动的谣言如果扰乱了公共秩序,最初的谣言发布者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变异”是由谣言传播者产生的,与谣言的源发者无关——谣言传播者在此相当于重新捏造了一个谣言并进行传播。
另外,考虑到公共人物往往都是社会地位较高和财力较雄厚的人群,对于谣言的辨认能力是要高于一般民众的,(38)黄城:《微博侵权责任的可预见性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60页。应当对公共人物适当采取更高的要求,而对普通公众适当采取更低的要求。当然,这里对于公共人物和普通公众是不能简单二分的,而存在一个程度问题——这个程度可以通过诸如网络自媒体的粉丝数量、民众中的知名度等来综合判断。反之,对专业领域人士就较强科学性专业事务的判断则应该采取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这也是基于“行业自治”的理念。比如,对于医护人员针对传染病发出的预警,更多时候应该采取一种宽容、尊重的态度,在没有其他专业人士配合调查的情况下,尽量不轻易认定为谣言。
(二)公共风险谣言的主观方面
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二款的规定,缺乏主观过错可以使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而在此,对公共风险谣言的主观过错要求应更进一步,即只包括故意,且此处的“故意”要结合行为目的来判断。基于条文中“故意”置于“扰乱公共秩序”前的语序安排,行为人传谣应是出于扰乱公共秩序的动机,如果其主观上不是出于此,则不构成传播公共风险谣言的行为。如对道听途说信以为真或者由于认识判断上的失误而出于责任心的行为,不能视为传播公共风险谣言。(39)安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60页。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二)项的规定本质上也是体现这一精神。大众深信过去的事情意味着对未来的最佳指引,而这也并非不理智的。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会导致过度忧虑或过度忽略。(40)[美]凯斯·R·桑斯坦:《最差的情形》,刘坤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页。当公民面对一种先前从未出现过的潜在巨大灾难时,忽略问题就会变得极其严重。(41)Max H.Bazerman and Michael D.Watkins,Predictable Surprises,Cambridge: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4,pp.91-93.比如,在疫情这类公共风险事件中,民众一开始可能会低估风险。但随着疫情的加剧,且逐渐有案例发生在自己周围,恐慌心理会导致民众高估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谣言很有可能会因为忽略概率的原因而滋生蔓延,因此产生的谣言就是由于人们客观认知能力的局限。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和美国纽约西区联邦地方法院也在相关判例法中表明过类似的观点:除非人们确认且明悉谣言为虚假的,否则他们无需为传播谣言的行为负责。(42)John H.HATROCK,Jr.and Beverly J.Hatrock,husband and wife v.EDWARD D.JONES &CO.,and Jack Daugherty,750 F.2d 767 (9th Cir.1984);Halina E.RUSZKOWSKI,as Executrix of the Estate of Jerzy T.Ruszkowski v.HUGH JOHNSON &CO.,Inc.,Reynolds &Co.,Inc.and Reynolds &Co.,302 F.Supp.1371 (W.D.N.Y.1969).对谣言的质疑、推测也不能算作谣言传播行为,这只能算作一种理性探讨,其意图在于确认信息的真假,系信息不透明的结果,主观推测不乏合理性基础。美国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有关判例法中就认为谣言的转发者在没办法认证谣言来源事实真假与否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为造谣。(43)Raab v.General Physics Corp.,4 F.3d 286,288 (4th Cir.1993).公共风险谣言的企图在于蛊惑不明就里的人们,引发恶劣结果,紊乱公共秩序,从而达到某种别有用心的图谋。而利他者以维护他人与公共利益为目的,当他人权益受到侵害,公共秩序处于危机之中,或者公共行政出现瑕疵时,他们常挺身而出维护其所相信的信念与价值观。因此,也不能把利他主义者的言论视为谣言。
(三)公共风险谣言的客体
公共风险谣言的行为客体为公共秩序,这是其与针对私人的谣言最大的区别。结合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此要区分有害谣言和无害谣言:行政主体只应对有害谣言进行管制,如果某种行为根本没有对公共秩序造成危害,或虽有一定危害,但情节轻微危害不大,行为人系初次公开散布此谣言,且还及时改正的,不宜轻言追究。无害谣言按照鲍威尔大法官的说法,更适合于同其他观念在观点市场中自由竞争,从而达致真理。(44)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 (1964).当然,如果已经发生了危害,对公共秩序造成了影响,但谣言有关行为者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该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一)项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在此,行政处罚的力度应当与有关谣言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相称。
危害还要区分线上与线下,如果只是在网络上转载或跟帖很多,就不应算作公共秩序混乱,公共秩序还是要以现实中实际发生的行为和结果作为标准。(45)谢燕:《在自由与责任之间:网络谣言的法律制裁与反思》,载谭世贵主编《法之思:浙江省首届法科生大学生征文比赛获奖论文集》,第495页。比如,有人在网络上散布某地发生杀人案的言论,这种言论至多只会引起网上舆情,而不会造成现实的公共秩序混乱。此外,这种扰乱公共秩序的现实结果可以归类为二种:抽象危险和具体侵害。前者是指扰乱公共秩序的后果虽然没有发生,但是这种抽象危险非常迫切。在此可以运用霍姆斯大法官在1919年确立的“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其认为,就算给予言论自由权最为宽泛的范围,也不会允许在戏院内谎称失火而造成骚乱的言论。(46)Schenck v.United States,249 U.S.47 (1919).后续,他把这个原则进一步细化,增添了两个重要的限定条件:“迫在眉睫”与“刻不容缓”(47)Abrams v.United States,250 U.S.616 (1919).。布兰代斯大法官进一步完善了该原则:只有某种言论引发的危险极度逼近,而且来不及对该言论进行充分的磋商,该损害马上可能产生的情形下,该言论所导致的危险才能称之为明显且即刻的危险。且该危险必须是一旦发生其损害非常严重。(48)Whitney v.California,274 U.S.357 (1927).即使公共风险谣言还没有出现实际危害,但如果继续允许其进一步发展,这种实际危害即刻就会降临,以至于等不及进行充分商榷,并且这种实际危害最终会破坏公共秩序,就说明公共风险谣言造成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构成了抽象上的扰乱公共秩序。而后者具体侵害则是指造成了具体的损害结果,即已经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由于抽象危险比具体侵害更难以判断,在确定抽象危险的过程中要更为尊重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与抗辩权。行政主体不仅应该主动告知获取的证据和证明的事实,还应当认真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抗辩,并作出相应的分析处理意见,说明采纳或不采纳意见的理由。如果一个公共风险谣言行为可以满足上述二者之一的要求,那就可以说这种行为已经侵犯了公共秩序这个客体。
(四)公共风险谣言的客观方面
在客观方面,所谓“散布谣言”是指捏造并散布没有事实根据的谎言用以迷惑不明真相的群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是指编造火灾、水灾、地质灾害以及其他危险情况和传染病传播的情况以及有违法犯罪行为发生或者明知是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的情形。(49)安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第60页。这里的重点在于“散布”和“谎报”,说明公共风险谣言要求公开散布虚假事实。公开散布要求的是一种强传播关系,而不是弱传播关系。从造成的社会危害上看,只有在大众范围内流转的不实内容,才可能扰乱公共秩序,如果不实内容仅在家人、朋友等小范围内流转,因信息传输对象较少,很难扰乱公共秩序。比如微信内的信息传播就不同于微博上的信息传播。前者是一种小范围的传播,仅限于私人之间的非开放圈子,应该认定为弱传播关系;而后者是一种大范围的传播,具有开放性,应该认定为强传播关系。
此外,“散布”一词具有消极内涵,往往指向不实信息,而“谎报”一词更是仅能指向不实信息。因而,谣言必须明确限定为欠缺事实依据的不实信息,并不包括真实信息或真伪不明的信息。从实际实践来看,人们探求真相有一个进程,从朦胧走向明晰。因此,尚未明晰的、模糊不清的、内容相左的信息将始终存在于社会之中,所谓的“谣言”常常处于人们的认知进程。把真伪不明的信息都认定为谣言并予以处罚,就会对人们探求真相的过程造成影响。目前政府经常面临的“谣言往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尴尬,其原因就在于官方轻易地将某个虚假未定型的传言判定为是一个谣言,从而导致自己陷于一个不能回旋的困局当中。(50)周安平:《公私两域谣言责任之厘定》,《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第149页。在公共风险事件期间,由于政府本身和民众一样也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对于很多传言也无法确认真假。因此,政府对其的定性也应该更为审慎。而且因为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完全真实和完全虚假的观点都是不存在的。言论只能做到部分的真实,也即和事实大致相符。对事实理解存在偏差不构成造谣。如果网民公开散布的信息符合基本事实,即使某些细节之处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也不能认定为造谣。(51)湛中乐、高俊杰:《论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第157页。比如,在疫情期间,散播的信息对确诊人数存在细微的偏差,把4个确诊病例说成8个,这并不能构成对基本事实的实质改动。谣言必须是对客观事实的实质性虚构,或者对关键点进行的捏造与修改。
还应注意的是,虚假事实只包括事实,而不包括观点,这也符合国际惯例。对于言论的保护,世界各国宪法制度均确立了保护意见表达而非事实传播的原则。因此,对于谣言,法律打击的重点在于虚假的事实性信息而非意见。(52)罗斌、宋素红:《谣言传播违法与犯罪的成立条件——基于行政法与刑法相关制度比较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5期,第22页。鲍威尔大法官曾在判决中对此论述道: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不可能存在虚假思想这类东西,无论一个观点看起来多么具有危害性,要纠正它不能依靠强制力而应是观念的自由竞争。但是,有关事实的不实散布不会受到这个修正案的保护。(53)Gertz v.Robert Welch,Inc.,418 U.S.323 (1974).德国宪法法院也在“吕特案”判决中将言论自由分为表达见解和陈述事实两类,采取不同的保护标准:表达见解是个人的主观意志,无所谓正确与否,因而不受任何限制;但故意和明显失实的事实陈述不受德国基本法的保护。(54)王颖吉、王鑫:《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治理》,第179—180页。此外,有些言论往往并非是单纯的事实或观点,而可能是二者的杂糅。这时候主要应该考虑的就是这个言论中的主要内容和核心内容是事实还是观点。如果其主要内容和核心内容是事实的话,认定其是否是公共风险谣言,则应考虑其事实部分是否是虚假的,而不需要考虑有关的观点部分;如果其主要内容和核心内容是观点的话,则自不必言,其肯定不是公共风险谣言。
综上所述,一个公共风险谣言必须同时符合以上四个要件,那才应受到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制。这种审慎认定与处罚公共风险谣言的态度可以尽量避免“谣言”事后又被证明是真实的情况,从而降低政府公信力,导致后续治谣的失灵。而且,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的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之前应该根据上述四个要件说明事实、理由及依据,且行政相对人应当有权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这也是自然公正原则最基本的程序规则要求之一。(55)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此外,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44条第一款和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应该由行政主体承担以上四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而不是由行政相对人来承担。这些也是基于实质法治的要求。
四 实质法治治理路径二:加大政府信息公开以消解公共风险谣言
实质法治还要求政府基于人民主权及其衍生的公民知情权的要求,强化政府信息公开以提升公信力。这种政府信息公开也是建立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教义学解释基础上的合法且合理要求。根据我国《宪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政府的公权力源于人民,又归属于人民。而公民知情权是人民主权的重要体现与必然要求,这是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根据社会契约理论,人民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将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组建国家,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和提供者及国家权力的真正行使者。其中,人民是授权人、委托人或权利人,政府则是受托人、代理人或义务人。反映在政府信息问题上表现为:政府只是替人民保管信息,公民有机会充分了解政府信息是民主的应有之义。而且,这也是民主的前提条件。(56)[美]罗伯特·A·达尔、[美]伊恩·夏皮罗:《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5页。要使公民主权、民主主义充分发挥机能,就必须保障自由的、丰富的情报流通,必须使公民经常的、充分的受到启发。保障公民对国政情报自由接触的程度,可以说是检验公民主权实质机能状态的标准。(57)郝庆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宣贯手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51页。在现代民主观念中,除去政府的构成,公众的参与及监督也显得越发重要,甚至已经成为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尺,而公众参与及监督的前提在于人民的知情,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亦是保障其参与权与监督权,实现其话语权,有利于民主的实现。因此,公民知情权是人民行使一切民主权利的重要前提,是遏止政府滥用权力的一道必不可少的重要防线。如果人民主权失去了公民知情权的支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对此,James Wilson指出:“人民有权知道他们的代理人正在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58)James Madison,Notes of Debates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5,p.434.代表人民的政府掌控了国家公共权力之后,往往就转变成了社会最大的信息所有者和控制者,人民却成了信息的缺失者和不知情者,政治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便由此而生。为了降低此种信息不对称,使委托人——人民能够更好地了解和知晓政府所从事的公共管理活动,政府就必须依法负责任地向人民及时公布公共信息。列宁也曾说过:“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59)[苏]列宁:《列宁全集(第六卷)》,中共中央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因此,政府掌握及拥有的公共信息当然应当向人民公开。只有让人民大众知晓发生的一切,让他们能够对此进行评判,并进而做出自己的决定,国家才真正有了力量。(60)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8页。这也是消解公共风险谣言的一种方式。
奥尔波特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谣言的重要公式:谣言=模糊性×重要性。(61)[美]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页。不确定性和焦虑是谣言盛行的肥沃土壤。(62)Walter R.Schumm,D.Bruce Bell,“Predicting the Extent and Stressfulness of Problem Rumors at Home among Army Wives of Soldiers Deployed Overseas on a Humanitarian Mission”,89(1)Psychological Reports(2001),p.130.法国研究者弗·勒莫作了如下概括:“流言并不是一种人为的现象,它的根子是人们感到自己缺了点什么,它又以摸棱两可的感觉在扩展延伸,它存在的基础是使人希望对事物有进一步的了解或是对隐约感到的威胁的一种反映。”显然,谣言是公众应付社会生活的一种应急状态,是公众解决疑难问题的不得已形式。(6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5页。在公共风险事件这种紧急状态下,公众就很容易产生信息渴求心理。在疫情期间,民众在初期担心封城,后期关心开学,本质上就是因为这些信息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重要。当民众身处不可控的灾难性风波时,会特别渴望知晓实时动态,以决定如何应对,来舒缓焦虑情绪。重大的事件最为容易产生谣言,原因在于重大事件的发生对国家、社会、群众的利益影响巨大,往往会激发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造成大规模的恐慌和骚动,引发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在此过程中大量谣言也就“乘虚而入”。尤其是在真相匮乏时,谣言更会大举泛滥以回应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在人们对信息极度渴望的情况下,真相的缺失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绝佳的土壤。谣言在特定时期内的实际传播取决于特定种类信息的供给和需要。当信息缺乏而需要显著的时候,小道消息最活跃;当信息丰富而需要贫乏的时候,小道消息最消极。(64)Theodore Caplow,How to Run any Organization,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6,p.77.信息的正式传播渠道与谣言的非正式传播渠道往往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因此,一个相对可靠减少事与愿违的谣言的策略是“足量供应”——供应比小道消息相关话题需要的更多信息。(65)James L.Garnett,“Coping with Rumors and Grapevines:Tactics for Public Personal Management”,12(3)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1992),p.46.由于公共风险事件的重要性难以减轻,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做的是尽可能减少与谣言相关信息的模糊性,及时公开信息,消减谣言生成的土壤。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信息公开。与其将大量资源投入到事后封堵、整治等救济措施,不如用于加强信息公开,事先预防,收效更大。(66)胡凌:《网络传播中的秩序、谣言与治理》,《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第10页。公权力机关要依法及时地公开信息,全面、透彻、及时的公开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必要的恐慌,减少因公开信息滞后而带来的辟谣成本,进一步增加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67)赵青娟:《重大疫情中谣言治理的法治理性》,《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3期,第38页。从过往经验上看,信息公开透明是消解谣言传播最为有力的手段与举措。第一时间告知群众有关信息,是民本政府应该树立的执政观念。“正义要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唯有让公众“看得见”,以公开保证公正,以透明确保清明,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打造阳光政府出发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才能加强公民与政府的互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68)单晓辉:《论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公信力提升》,《人民论坛》2014年第34期,第61页。在民众不清楚、不了解、不明白,引发质疑乃至谣言时,政府不能忽视,更不能轻视,应及时有效地回应民众有关诉求,与社会大众进行即时的信息交流与良性互动,让民众看见,“真看见了”,看的“是真的”,使得“不明就里的群众”可以及时知晓有关真相。(69)支振锋:《治理网络谣言关键靠法治》,《法制日报》2012年4月17日第7版。
反之,信息不对等就容易引发“信息倒逼”机制,以谣言的反向权力要求国家、政府在辟谣过程中实现信息公开。(70)何明升等:《网络治理:中国经验和路径选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第286页。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这是信息的黑市。(71)[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上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如约瑟夫·奈所言,权力的获得来自于对有效信息的占有,权威信息的掌握者如果不能发挥“稀释”主体的责任和作用,谣言就成为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72)张文祥、杨林:《网络谣言的行政规制与协同治理:兼论公共权力及其边界》,《新闻界》2022年第5期,第75页。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就是真相,不管是好事坏事,民众首先要知道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唯有开诚布公、公开透明,政府公信力才能伴着阳光不断生长,也可防止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73)杨妍:《自媒体时代政府如何应对微博传播中的“塔西佗陷阱”》,《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5期,第27—28页。。如果对信息藏着、掖着,甚至用虚假信息欺骗民众,会诱发更多谣言而且会使政府信息失去权威性,加剧群众焦虑不安的心理,错失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Sung-Un Yang在韩国MERS疫情后的调研就曾经显示,政府对公众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会显著地提高疫情信息在公众中的可信度。(74)Sung-Un Yang,“Effects of Government Dialogic Competency:The MERS Outbreak and Implication for Public Health Crise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95(4)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18),p.1011,p.1020.2011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以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为渠道对1714位受调查者进行了线上调查——谣言泛滥的原因是什么?调查结果给出的最主要原因是“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致使信息不透明”(73.1%)。(75)王勇:《别让网络谣言成为突发事件的“次生灾害”》,《人民论坛》2013年第20期,第59页。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独自垄断事件的信息,在事件处理上如果政府语焉不详、捂着、盖着,公众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其他途径来打探信息。等到“纸包不住火”,政府无法抑制舆论的蔓延时再去解释真相,就会变得十分被动,不容易得到民众的信任。(76)周莹:《法治视野下热点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1页。
因此,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第二款的规定,需要促使政府从公共信息的拥有、垄断、管制向公共信息的提供、开放、服务转变。通过畅通公民的公共信息获得渠道,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及背后的政治、文化权利,进而根除公共风险谣言产生的土壤。(77)周振超、张梁:《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的法理诠释与实践向度》,《理论月刊》2021年第1期,第131页。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可以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政府拥有最多的公共信息,因此更应该在有关事件发生后主动公开相关信息,保障公民知情权,以公开促阳光型政府。此外,在民众申请公开的情况下,也要回应民众诉求,公开相关信息。信息公开还要符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第一款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3条“及时”和“准确”的要求。及时也就是第一时间将有关信息公布出来,直接在初始阶段就消除谣言产生的机会;准确即毫无保留地发出有关信息,即使在公共风险事件初期,政府由于自身认知也存在局限导致了解的有关信息还不够充分、完整,但哪怕是这些信息的发布,也足以减轻人民大众对于事实真相的渴望。(78)王二平:《铲除滋生谣言的土壤》,《求是》2013年第18期,第54页。政府就算对于一些情况还不知晓、不清晰,但只要及时跟进相关信息,也会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诚意,从而有利于政府的公信力提升与谣言治理。根据现实中政府人员常常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的理由拒绝政府信息公开的情况,则应当要求其详细说明具体的理由与依据。健全问责机制,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公开政府信息的人员要进行追责。
在公共风险事件中优先公开哪类信息和如何进行信息公开的问题上,政府要学会从民众角度换位思考: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在公共风险谣言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与民众进行公共风险交流,加大沟通交流的力度,对人民群众更为关心的内容进行更为详细的信息公开。如果民众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反馈,那么一般来说,这时的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就是比较到位的。公共风险事件具有突发性,且和大众生活联系紧密,也因此极易导致民众缺乏安全感,产生恐慌心理与焦虑情绪。以新冠疫情为例,在疫情这类公共风险事件中,民众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健康是否会受到威胁,这就要求政府优先针对这类信息进行公开。比如在美国波士顿爆炸事件发生后,波士顿警局在推特上优先发布了逃生和救援指导等内容,(79)王颖吉、王鑫:《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治理》,第119页。就是因为在爆炸类公共风险事件中,民众最为关心的是生命、人身是否会受到威胁。公权力部门需要根据公共风险事件的类型,优先对民众最为关切的内容进行信息公开。在公共风险事件中,政府还要向公众表明政府对事件的态度和处置方法——政府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还将要做什么,进而向公众展示政府的能力与责任感,从而树立公权力的良好形象。政府工作议程的公开也可以减轻人们因对公共风险事件不明了而产生的不安和恐惧,抑制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在语言表述上,公权力部门则要考虑到公众的接受水平,避免冷冰冰的公文形式,而尽量多采取生动的方式传递更多的实质信息和细节证据。
在具体公开路径上,政府部门除了在传统的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信息公开之外,还可以充分借助传单、报纸、广播、电视、电话、短信、互联网等各种信息渠道,特别是重视主流媒体的作用,及时对热点事件、焦点话题进行公开解析,纠正个别谣言对于真实信息的恶意扭曲,重新还原客观、如实的信息。还要认识到,在大部分的公共风险谣言中,政府都与谣言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作为一方的当事人与谣言涉及的公共风险事件具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单方面释出相关信息,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的疑虑,其可信度自然大大降低,(80)张新宇:《网络谣言规制中的突出问题及其应对》,《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5期,第127页。容易出现“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情况。而非政府组织因为身处第三方位置,持有非官方立场,由其公开有关信息予以澄清,民众鉴于有关信息的中立性特点往往更为信赖,可以形成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因此,在规制主体上,要实现多元化,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与社会的自净功能,鼓励行业自律,重视通过民间团体和企业、个人的监督作用弥补“观点市场”的失灵。(81)王颖吉、王鑫:《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治理》,第174页。可以学习英国“公民咨询局”和西班牙“抵制谣言代理人”的经验,鼓励在基层社区设立由群众自发组成的辟谣机构,通过群众参与信息公开与辟谣的方式加强民众对政府信息的信任。还可以通过公共人物、技术专家、专业机构等民间“意见领袖”进行信息公开,从而抑制谣言的产生。
虽然以新冠疫情谣言为例对公共风险谣言的行政法治路径进行了分析,但其原理在公共风险事件中却是相通的。除疫情之外,环保、股灾、金融危机等问题都是公共风险事件,谣言在这些情况下也非常容易滋生,有着较为类似的情况与特征。在过去的“抢盐风波”“7·23动车事故”“江苏响水爆炸”等公共风险事件期间之所以谣言泛滥,也是因为在实质法治环节上政府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因此,如何从权利本位出发,以一种更为人本主义的方式进行公共风险谣言的治理是需要反思的。本文提出的以实质依法行政为思想指导,审慎认定与处罚公共风险谣言行为并加大政府信息公开以消解公共风险谣言的具体路径,希望可以为现实的公共风险谣言治理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