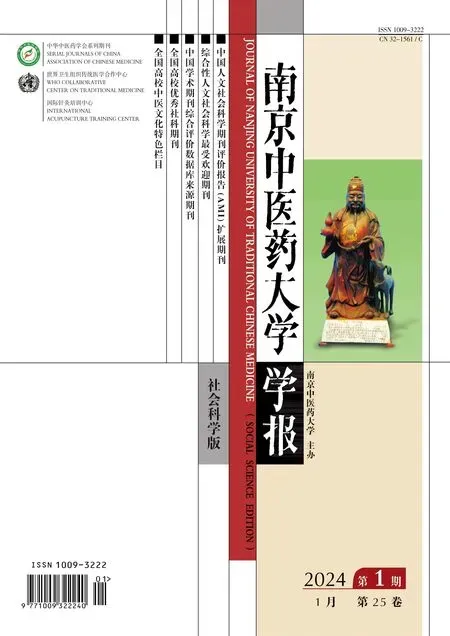变容与平衡:西药东渐背景下近代中国汤剂改良之争
朱睿思,崔军锋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25)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各界对西医药的认知逐步深入,中医药渐入窘境。中医药界内部分化加剧,虽部分中医斥责革新中医药即为西医药之奴隶,但改良派仍积极奔走,谋求变革。由于政府无心支持与中医合法地位的缺失,中药改良的重担主要由医药两界承担。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或从技术与文化的角度考察中药的发展历程[1-3],或从具体对象出发对近代中药改良进行探讨[4-5]。不过,上述研究重点关注中西医论争中的相关史实,对中药改良的历史缺乏整体关照。
汤剂,古称汤液,因其适应辨证施治、随证加减的原则,一直是中医施治时使用的主要剂型之一。晚清以降,伴随西医药而来的科学化语境几乎完全否定传统医药,随着西药逐渐占据中国市场,历来为医家所推崇的汤剂因操作繁琐、服食不便屡遭诟病。深受刺激的近代中医试图驳斥西医界认为传统医药无法科学化的言论,从改良汤剂出发推动中医药革新,为中医医理、药理正名。本文将探讨近代汤剂的工艺改革问题,尤其关注外来医药技术的进步对本土药物改良的实际影响,希望对现代中医药的发展有所助益。
1 西药入华及其影响
中外医学交流源远流长,中国人将踏浪东来的外邦药材或是单方制剂称为番药、西药。明清时期,传教士所献西药仅供统治阶级及亲贵之家使用,海通之后,西医西药陆续传华,进入普罗大众视野。1858年,清政府与各国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宣告在华销售的外国药品可免缴关税,于是大量西药通过洋行入华,如怡和洋行的飞力脱、天祥洋行的西药等。然西药起初并不被中国市场认可,学者蒋梦麟(1886—1964)在回忆孩提时代的乡村生活时曾言:“浙江老家虽然西医已经有所传入,但仍是中医的天下。”[6]传统中医也认为西药性质未明,不合国人体质,不可轻易尝试。
战火与灾荒加速了疫病的流行,各地接连暴发时疫。许多华人西医将有效的化学药物配伍中药,制成中国人常服的中成药剂型(如药油、丸、散等),并取中药名上架出售,如梁培基发冷丸、唐拾义止咳丸、陈六奇济众水等,确为缓解疾痛提供了便利,也让民众对西医药的看法大为改观。外国西药业也趁机以庞大资本为依托打压中国药商,用压倒性的宣传优势和品质精纯的药品掳获民心。1905年,调查称金鸡纳皮的输入额较10年前翻倍,一跃至425万磅[7]。1911年,上海华商药房资本亦从晚清的几千元增至56.6万元[8]。广州的西药行业已基本成型,隐隐显露后来居上之势。以金鸡纳霜为代表的西式药品药效显著且价格低廉,药丸制品或作胶囊或裹糖面,服食便利,口感亦佳。西药带着“特效神药”标签,占据中国本土的医疗市场,给中药业造成了不小冲击,城市居民日渐接受西医西药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与此同时,不少欧美医药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药材,并运用其擅长的化学研究方式制成酊剂或流膏。大量以中草药为原料提炼而成的药粉药精,打上科学化的标签,被精美包装后转售回中国,价格虽高却很畅销,它们或液或丸或粉,便于服用,利于携带,效力似乎也远胜中药。中医界内部亦产生分歧,或提出中西药物互补之说,肯定部分西药疗效;或批评时风不正,感慨中药之未来堪忧。史学家全汉昇将清末医者对西医药之态度总结为赞成、反对和折衷三派:赞成派认为西医胜过中医;反对派认为中西医完全不同,不必也不屑学习;折衷派首提方药之改革,“(西药)制丸煎膏,机器完备,……是又当仿而行之,不可拘拘守旧也。”[9]
民国初年,西医因被纳入官方医疗系统而地位攀升,势力逐渐庞大,进一步压缩中医的生存空间,中西药品的商战与中西医界的学战一触即发。西医高效神速而中医却多庸医的舆论甚嚣尘上,俞樾“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言论被大肆传播,废医存药之倡议得到一批改革先锋的支持。梁启超亦曾言:“(中医)确有名医,但总没有法传给别人,所以今日的医学和扁鹊、仓公时代一样,或者还不如。”[10]面对亲西医派的攻讦,中医界回应称药效即医效,中医所用药物的选择、配伍、制作与服用,与中医的智识与经验密不可分,但中药较西药而言确有诸多不足,有待改良。医家使用最广泛的汤剂,在第一时间被推上了改良的风口浪尖。
汤剂适应中医辨证施治、随证选方,且因其药效显著,同时还可外用于含漱、熏蒸与洗浴,故医者多嘱患者将方药煎作汤剂服用,“故汤液之用居十之七,而丸散与醪糟膏丹则居十之三”[11]。然而汤剂煎煮流程繁琐,多须趁热服用,味苦量大,且汤头所用之假药、伪药常辨别困难。倘孤身在外突发疾病,即便平日信奉中医的病家也多问诊于西医,服用较为方便的西药。为此不少有忧患意识的医家感叹,中医之不振,实为中药所累。于是部分改良人士主张适应时代,从汤剂着手积极创新,挽回医权。
2 剂型之争:便捷服用与灵活配伍之取舍
中药传统剂型中不乏服用简便之品,中医杨赞民认为汤剂之繁在于煎煮,提议废除煎剂,将汤药改良为膏精末露等已有的剂型(如散剂、膏剂、丸剂等),并列举了数百种药物及其操作方法供汤剂剂型改良时参考。此提议得到响应,部分医者积极投入改良剂型的试验之中,“是以有精制丸散改变汤液之议也”。[7]然而,由汤化丸的尝试最先宣告失败。传统丸剂多用于久病之人的舒缓治疗,但若以汤化丸,所需药材量将是丸药平均用量的数倍。当时中药丸剂的制作基本依赖人工,精细化程度低,而转化后制成的药丸体积较大,有时一粒丸即重达三四钱(约为11~15g),“殊劳脾胃之运化,或因此而饮食减少。且妇女孩童或因丸太粗,或因味太苦往往不善吞服。”[12]且丸药制作必经重筛,需将所有药材研为细粉后与水、蜜等混合制成,而汤剂所用药材多需高温煎煮才能析出有效成分,因此汤剂转丸剂在实际临床使用中的转化率很低。
另有将汤剂转化为食用散剂,即根据所用药材研磨的颗粒大小区别其服用方法,细末直接用温开水、酒、茶、米汤等冲服,粗末则需与水共煮后,按医嘱去渣服用或连渣吞服。此法在唐宋时较为盛行,理论上散剂与汤剂制法相近,但制作散剂时药材损耗相对较少,煎煮程序也得到简化。然而医者朱让卿将钱氏异功散化汤化丸时发现,很多药物并不适合汤剂转散剂。如半夏之类有毒性、味涩的药物,大多需煎制,研末后不仅毒性未定,患者在服食时也较困难,“以少数之散冲多数之水,(患者)不能不连渣吞咽也”[13]。操作时,某些药物在作散剂煎煮时容易糊化粘锅,需煎药者时刻关注拨动,很不方便,且所制散剂功效与汤剂也相去甚远。
浓厚黏稠者为膏,内服膏剂是常见的滋补养生之品,外用膏剂不仅能疗外伤,亦可治愈部分内科疾病。清代外治大师吴师机曾言:“今以汤头还为膏药,于义为反其本,以为妄变古法者,非也。”[14]他提出凡是临床上行之有效的汤剂、丸剂皆可改制为膏剂,尤其适合不愿服药或无钱求医之人。然而,膏剂制作难度极高,使用药膏之医者还须清楚知悉古方今制之精要,做到内外治法随证而变,因时制宜。
唯有与西式药水最相近的药露,改良效果最明显。药露制法源于《泰西水法》,是以草木瓜果等为原材料蒸馏而得,但药露与饮剂相似,由于药性轻薄常被制为饮品,少用则无效,若要达到一定药效必下猛剂,随之导致与主药配比的其他药材剂量大幅增加,“此灌水牛之药也,病人耐之乎?”[15]
随着西方健康观念在华渐趋流行,教会藉医传教,西式医院环境整洁,服务周到,与中医诊所形成鲜明对比。“凡华人一切疑难危险之证,中医所不能治者,一经界入医院,施以手术,饮以药水,不难著手成春,是有医院而药水之名乃大。”[16]注入密封玻璃瓶的西洋药水,乘着科学与文明的东风,成为时代先进医疗体验的重要标志。或是出于上述原因,医界的汤剂改良方向开始有意或无意地从膏精末露等传统剂型转变为药水,模仿西药形制,仿照西医计量水杯的样式将药物用包装瓶包装后出售。1902年,天津中西药房(后改名为中西制药厂)率先模仿西药形态和包装方式对汤剂进行改良。
严格来讲,当时医药界并未出现汤剂改良的突破性成果,杜鎏煇曾言:“吾所望于医药界者,无他,不过作广告之竞争,以及药品与装制之改良耳。”[17]多数医者的汤剂提精之法,仍延用传统煎煮方式煎成浓汁,如西医姚邦杰在治疗恶疫时发明的药水胜毒饮[18]。由于初步提炼后始终面临着汤剂药力与药量的抉择问题,加之受医者水平与客观条件所限,汤剂在剂型转化时常因效力不足而失败,故中医延用旧法抓药煎制者居多。
自古医家最重煎药,煎煮方法适当与否决定了药物的最终品质。水量、火力、药材先煎后下,以及冷服热服都需因药性不同作出调整,且难度较高不易普及。如何在保证药效的同时使服用方法也简便灵活,成为医家探讨汤剂改良时关注的焦点。中医张叔鹏提出可由患者取药物粗末煎作浓汁,或由医家帮忙代煎,需服药时再用百沸水冲服,如此不仅出门在外服用更为方便,居家用药时也能少些繁琐功夫。但亦有反对者表示可操作的对症药方有限,即便初服时效果不错,时间久了患者也会对医者不能按病情及时加减药物而不满,根据病情灵活变通地服用汤剂的特点也因此丧失。因此,不少医者也曾推崇过药铺附赠的煎药服务,但商人重利,各地皆存在不良药铺欺百姓不识药材,鱼目混珠,或将废料进行二煎三煎的丑闻,病家多不相信药铺所煎制的方剂疗效。
既然汤剂煎煮无法代劳,便有部分改良人士尝试模仿西药,规定汤剂制剂标准,在保留药材药性的同时,尽可能简化汤剂的煎煮流程,方便普罗大众日常使用。1930年颁布的《中华药典》直接采用西式剂量法,将煎法规范化。1933年1月,上海市医药两业统一改用新度量衡,要求中医列方添加“以上药品均系新秤”字样,方便病家备药时折合计算。不少医药期刊也登载一些民众日常生活中可用的汤剂煎制方法,戴竞先曾给《铁樵医学月刊》去信探讨西药的药物与水分配比看似正确又有定量,而中药汤剂却视病情而定,不知如何配比才算正确?编者回复大约20两之药,用水1斗,煮出4升(古重)即可[19]。叶劲秋总结前人经验,得出煎煮的通用流程:“以药物切成均等之粗末,入磁罐,加适当之水,时时振烫之,在重汤煎上(俗谓隔汤炖)煎三十分钟。”[20]
诚然,在大众眼中,汤剂煎煮不便已毋庸置疑,可医家却违奉参半。部分保守言论如汤剂为古来圣贤相传之法,是我国国粹,绝不可废等,一向被西医支持者们抨击,也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亦有医者表示汤剂确实亟待改良,但必然所费甚靡,目下之中国尚无如此庞大的试错成本,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也不支持。而多数医者不支持汤剂革新的深层原因在于,改良者在转换汤剂剂型、简化制作流程时削弱了中医医理的指导作用,不便于中医诊疗的临床应用。 中医潘文田就曾于报纸上声明反对废除煎剂,表示将中药改同西式制剂一事,“逖听之下,令人齿冷”[21]。 汤剂可随证加减的灵活性特征是西药无法替代的,复杂的煎煮方式也是为保证药物药性不失。多数中医不愿放弃自身秉持已久、或古或今的方药煎服理念,传统医者与改良医者的汤剂存废之争仍在继续。
3 应用之争:汤剂与西方化学技术的结合
20世纪20年代,医界改良人士纷纷提倡药材化验——告别传统的肉眼气味识药,利用西方的生药学知识,对药材进行彻底而全面的认识,“若生地、当归、牛膝、参耆之类,富含滋养浓液者,得化学之试验,以分析其含质之成分,更可推广效用,此我中药之仰赖西法而益彰也。”[22]在此情况下,中医界仍尤为重视汤剂与中医临床治疗的紧密联系,倡导保留其因人而异、随证加减的特点。林大燮等医师基于其时生药学研究成果,提出汤剂与西式药水相比,逊于成分之冗杂,若能分离传统验方中的药物成分,将汤剂中无用与有毒成分剔除,或可达到精制药水的疗效。
1919年秋上海暴发霍乱,上海医药界实感煎药之繁琐,成功将需要煎制的治疫汤剂制成药水,并于次年霍乱再次暴发时有效遏制了疫情,三个月内治愈了数千例患者。拥有初步实践经验后,李平书等医者对饮片提精之法深入研究,并于1920年创办上海粹华制药厂。作为上海第一家中药制药厂,粹华尤为重视单味药材的精制,即将道地药材古法炮制后,利用化学方式将其制成药水,种类有数千种之多,患者不必煎煮,可直接按照中医配伍的药方购药服用。药厂开业当天柬邀各界人士参观总发行所,药水部更是摩肩接踵,颇受改良派医者的青睐。1922年,粹华制药厂追加资本分设发行所,受邀参加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举办的首次展览会,厂方负责人于会上发表演说。全国各地高校如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国立商业专门学校、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等,都曾组织学生入厂参观学习,直言该厂组织完备,炼制科学,实乃开创中国医药界新纪元。
然而在实际使用中,这些科学中药并未完全获得消费者的信任,社会上对粹华制药厂所制药物的批评逐渐增多。朱菊庭总结粹华药水三弊:其一味苦辣,其二不能久存,其三配方随意且不公开。[23]该厂制药主任王祖德也表示因能力有限,药物成分尚未化验清明,药品精制后还要加入无毒防腐剂以防变质,这使得药剂成分更加复杂。1923年,朱保熙曾在医报上提问,为何用玻璃瓶装的粹华当归药水总是破裂?回答者也语焉不详,推测可能是药品药性强烈,具有膨胀性,回复未能周全[24]。医师远志听说有人将瓶子破裂归因为当归属木,玻璃属土,木克土故而瓶裂,感叹其荒诞,遂来信解释或是由于当归药水含糖,霉天时药品中的糖类物质发酵产生气体,气体膨胀致使玻璃瓶破裂[25]。1924年,粹华制药厂因登报招盘而全局变动,被迫闭门歇业,原制药部长郑平叔另组建上海国华化学制品厂,继续生产并出售粹华杏仁精、净血片等产品,但没坚持多久也销声匿迹了。
粹华制药厂虽在万众期待下草草落幕,但汤剂改良研究仍在逐步推进,将有效的传统汤方提精制药,已然被一众医家认为是保存中医药最有效的途径。1922年,费泽尧曾在牙痛治疗时发现一验治药方,试验得知此古方具有抑制神经痛的疗效,“苟能将是方提炼精华,制成药水,吾思必不逊于西药也”[26]。自粹华制药厂、国华化学制品厂后,1930年成立的上海佛慈药厂也自称生产科学化国药。佛慈厂内特设制造部与药物研究部,制造部由西医柳镇永领导组织,延续了粹华制药厂精制中药的思路,优化传统炮制、煎煮工艺,研发国产新药。该厂特别要求测定药物之有效成分与实际功效,必须经过动物试验与化学研究,因此另外饲养动物,提供青蛙、白鸽、鸡、犬等供研究员进行研究。然而1936年,佛慈在福州的代理商却因原料不明且未经政府验核,遭到当地中药店联名反对[27]。个中原因确有药品监察时发现存在问题,但也不能排除受到竞争同行的干扰。
抗战时期,西药来源骤减,药价飞涨,为解救药荒,科学化浪潮席卷至中药业,“科学的改良运动,为我医药界之最大急务”[28]。不断有中医将西药技法融入中药的使用中,如将中药注射液注入患者体内,避免其服食汤剂之苦。中药注射剂的有效性也在多次烈性传染病的大规模暴发中得到反复实践验证。1932年,中医李健颐在《医药卫生月刊》上公开了自己根据西医注射剂原理,将二一解毒汤制为中药注射液的实验记录。经过临床试验后,证明该药确能治愈霍乱、鼠疫、猩红热等诸多病症,疗效显著[29]。不久后,李氏又发明了治疗温疟的中药注射液,患者接受注射后十余日即完全康复。淮安西医刘耀宗诊治天花病人,使用西药注射后不效反剧,于是“取升麻葛根汤药味制成液剂,掺以蒸馏水少许,注射病者静脉,立刻化险为夷”,焕发汤剂使用的新生机。[30]郭定若在进行制剂改良时,也曾多次提及部分中药“如能设法析出有效成分,供作注射用更佳”。[31]当紧俏的西药失去特效标签,革新后的中药就具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观此可知中药之为注射,实可与西药注射并驾齐驱”[32]。
无论是精制饮片、科学国药的提出,亦或是中药注射液的发明,都是近代改良人士试图结合传统中医的辨证论治,引进西方化学技术,避免汤剂原有不足,对其进行的便捷化改造。然而在战时背景下,药品紧缺虽在客观上成为中药科学化研究的一大助力,然研发的大多数国产药物都脱离了传统中医的理论框架,沦为某种西药的替代品。社会各界对产出药品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效果也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原因在于西方科学知识尚未完全普及,更多的则是中西医诊疗观念的冲突。医界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医手中,汤剂革新也始终未能形成体系,最终成为某门某派、某一药厂的独家疗方,中药式微的状态并未改变。
4 学理之争:何为真正的“中药科学化”
20世纪30年代,随着西医药走入普通百姓生活尤其是城市居民生活,其也逐渐走下神坛。民众发现西医在技术上存在不少局限,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常有疏漏,误诊或无法治疗的情况时有发生。且医院的服务态度不如以往,西医曹芳涛认为医院往往视金钱重于人命[33]。反观中医,虽学理饱受诟病,治疗手段被认为相对落后,但对比之下服务态度却远胜西医。
西医的药学研究能力也受到国内医界的质疑,许多实验室的药材化验成果存在争议。部分精制实验后的药材不能保证其原有功效,更无从得知经配伍煎制的汤剂在有机组织内发生的效力,而使用未加工的生药煎制效果反较化学精制的药品疗效更佳。邓亮例举黄连、麻黄、石膏、胡桃等多种药物经过科学精制后,常会出现药效转变或完全失效的情况[34]。胡德茂在文章中引用其他医界人士的结论,比较化学炼制麻黄剂与生药麻黄的功效,指出由于尚未有实验验证,若中医为省功夫直接使用麻黄剂,恐有发汗不效之虑[35]。黄国材提出生药较化学药品更为有效,原因是生药中存在一种生活素,经过化学煅炼后即全数消散,“盖以其化学药,不若生药之适于生理也”。[36]
国外的“汉药热”也让中药成为各国药物科研团队关注的焦点。1929年中国留美学生陈克恢在校研究中药麻黄并成功提取有效成分,发明麻黄制剂爱发德灵(Ephedren),获得纽约医药联会奖金[37]。美国李利制药厂(Lilg Drug Co.)及夜鹰制药公司(Owl Drug Co.)都曾重金聘请中国医药专家研究中药材。1936年,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派遣医药博士越智真逸来华,搜罗120种珍贵药品、民间秘药带回神户,提出“把古药加以整理,使之近代化,作一融汇中西的研究”[38]。
德、日也提炼中药材之精华制成各类药品,所制之药大量涌入中国市场,除了当归精(优美露)、麻黄精(爱发德灵)之外,还有提取人参有效成分制成的今则甯、提取桔梗有效成分制成的爱服甯等药品。更有日人对中国名方汤剂中主要成分的精华进行萃取,重新配伍后制成药剂,畅销日本国内,远播欧美。这些国外药剂逐渐由单味剂转向复方剂,用量少,效力强,广受好评。国内医者、药厂闻风而动,各类药物精华仿品频出,美其名曰支持国货,如1935年杭州民生药厂科学提炼当归的有效成分,制成健美露(Gimenor),同类型药品还有信谊药厂的当归流膏、佛慈药厂的当归素等。梁心结合国内外的药材实验研究成果,举一反三,制成当归、川连和桔梗等数种国药煎膏,并公开制作方式,注明用法、疗效及注意事项,方便医家、病患直接煎为汤剂服用。[39]朱寿朋提出中国有大量杀虫、治疗疟疾特效药,若加以科学方式煎制精华,保存有效成分,必然胜过山道年与金鸡纳霜。[40]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医者认为模仿西药制剂虽有一定成效,却与中医治疗观背道而驰,是一种沿袭西医的制药理念、带有投机色彩的科学化。西医所制精华能否完全展现药材的最大功效犹未可知,如西医黄胜白就曾评价德药优美露售价较高,可直接购入全当归一支,煎浓汁服下,效果亦相差无几[41]。改良者们呼吁汤剂的科学化改造须抛弃套路化的借鉴沿袭,首先从研究复方汤剂的药理出发,再学习西医的药物研究模式和手段,结合临床用药经验,确定汤剂的方效与药效,从而完成将良方制为良剂的过程。如李怀仁用西医的生理知识分析中医补脾胃之药,并验证了白虎汤等煎制药剂的科学原理与实效。[42]
此外,中医改良派不再执着于用所研究的科学化中成药完全替代汤剂,而以保存国药为先,“当宣传中医固有之文化,使国内国外,洞悉真实之价值”[43],收集传统中医优质单方,结合西方的化学实验验证,利用动物实验、临床经验确定中药汤剂中的有效成分,做到科学国药的市场化应用。医家叶橘泉曾将祛痰镇咳的汤剂制成保尔肺药液,发出样品830余份,回收评价250份,认为有效者占86.4%。后又制新药敌痢康,以代替局限性大且有副作用的治痢西药厄米丁(Emetin),并在报纸上刊登信息征求医界试验[44]。新药在上市前须经批量试验一事,已成时医之共识。叶橘泉所制之药物经实验验证,结果显示其疗效确较西药更佳,且价格实惠。但由于大量试用者领用后并无回音,实验结果缺少说服力,其社会反响有待考察。
谢筠寿曾公开谈及粹华制药厂的各类酒精浸剂、膏剂只是表面的科学化,怀疑佛慈药厂所售产品不能算是真正的科学化产物。如何跳脱出所谓的“科学化困境”,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传统药学生存发展的新路径,引发了国内医界人士的多次探讨和争论。近代中医改变将传统药理与西医学说杂糅以证科学化的方式,直接上升至对科学的重新定义,认为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医学均为科学,因此中国医药亦为科学。中药科学化不是西药化,更不是复古化。恽铁樵认为,基础的药物化验研究都是西医的工作,中药的科学化研究必须结合中医治疗理念,绝不可本末倒置,否则反倒成了促进西医发展的驱使力。时逸人赞成学习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必以中医之经验为重,参用西法化验之补助,则改进中医与制造国药并进,斯无误矣。”[45]中医梅永茂则提醒须警惕勿使中医融化于西医,“须以真正之中医学理,与西医互相切磋,互相中和,而产生一种新中医”[46]。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药科学化目标的实现,尤其是汤剂改良,医者需学习西方的生药学、药物化学和药理学知识,还需兼备中药炮制知识与中医治疗经验,“用科学方法将中国药物之储能,依医食同源特殊之汤剂学,推广其效实”。[47]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决议“请教育部学校系统添列中医一门案”中,于课程科目中设置制药实习与方剂学,解释传统汤剂的制方原理,并以西法改良。1941年上海复兴制药社提出精制中药计划,在民间收集流行的验方、单方与秘方,经过药方鉴定与化验分析后,统一制为成药并投入动物试验。但可惜的是,一直以来,各地学校团体研究成果并不互通,培养人才分散,教材标准各异,“教授各自为政,支离矛盾,在所难免”[48]。据统计,1930年全国设立中医学校合计不过十余处,教学设备奇缺,学员也无处实践学习,只能向相熟的药房、医院借用器械与场地。[49]更兼几年后战时特殊情况,资金、场地都难以维系学校运转,那些发展中医药的美好期许,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就被迫叫停,汤剂也未能得到真正的科学化改良。
5 结语
晚清西药入华,使得发展中药不仅是中医行业生存之要求,更是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中国利权之要求。中医界跟随时代的发展谋求变革,汤剂首当其冲成为中药改革的焦点。心怀理想的医界人士客观审视西医药之优点,从器物到学理层层拆解,不断深入,汤剂革新的背后,是近代中国社会对西医学的收受与变容,对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把握与平衡。
但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汤剂改良成效并不显著,即使中医界所呼吁的科学化已是老生常谈,然而对于如何实现却意见分歧,以致汤剂改进的方法始终未能一致,只得付之阙如。汤剂与成药不同,具有因人而异、随证加减的用药特点,革新后的汤剂无法完全融入传统中医的诊疗观念,这也是多数近代中医不支持汤剂改良的重要原因。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是近代汤剂的工艺改革之争,涉及汤剂这一形式应否、可否及如何西制的争议,其中应用成方、辨证论治之争与中西医诊疗观念差异的问题,限于篇幅未能展开,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另做专门探讨。
清末民初,中医反对者一直有“废医存药”之论,可一旦脱离中医理论框架,包括汤剂在内的中药药材选择、配伍和制作逻辑构建就没有任何意义。探讨近代中国医药界为中医药现代化所做的努力,以及他们对汤剂科学化的思考和预想、矛盾与纠结,如今看来仍未过时。值得庆幸的是,新时代的医药研究人员承续使命,始终坚持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现代化的药物研究模式为中药科学化提供科研数据支持。而近代社会对于中药汤剂改良争议的探讨,虽不能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或能为中医药未来的发展思路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