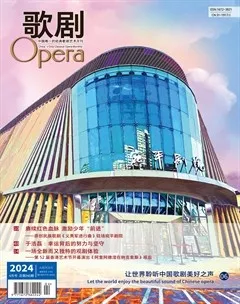因中致和 和而不同
王雅宁
17世纪到18世纪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法国音乐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同时对法国社会及其启蒙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启蒙思想强调理性、批判传统权威、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这一时期不仅作为娱乐和审美的对象,也成为传播启蒙理念的重要手段,在法国启蒙思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音乐作为社会交往与沟通的平台,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有助于启蒙理念的传播和接受。同时也作为一面镜子,反映了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社会的精神面貌和变革趋势。音乐家通过创作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用音乐表达启蒙运动的思想内核,对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687年吕利去世后,拉莫逐渐成了法国抒情悲剧的代表人物,他的第一部歌剧《希波吕特与阿里奇埃》(Hippolyte et Aricie)创作于1733年,此后他创作了芭蕾舞剧《殷勤的印第安人》(Les Indes galantes,1735)。1737年,歌剧《双子星卡斯托与波吕克斯》(Castoret Pollux)问世,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是拉莫的歌剧代表作。拉莫创作的芭蕾舞剧《赫伯的节日》(Les Fêtes dHébé,1739)、歌剧《达耳达诺斯》(Dardanus,1739)和《纳瓦尔公主》(La Princesse de Navarre,1745)等,都是出色的作品。1745年他被任命为皇家室内乐作曲家(Compositeurdela Musiquedela Chambre)。晚年的拉莫除独幕芭蕾劇《皮格马利翁》(Pygmalion,1748)和抒情悲剧《琐罗亚斯德》(Zoroastre,1749)外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问世。
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音乐的性质也发生着变化。如何将音乐的感性与理性兼收并蓄,如何实现和解,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二元性的问题。在歌剧的舞台上,男性理性控制与女性感性放纵的设定或者理性文本与感性音乐之间的竞争,将二元性提升到了高度性别化和道德化的维度。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也为之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
音乐中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并不是法国启蒙运动所独有的。在几十年后的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人成熟的古典风格中,这种对立也同样是强烈且普遍的。但是与法国阶段不同,那个时代的顶尖思想家很少与作曲家或者音乐理论家进行持续的对话与沟通,因此,音乐思想和创作之间的直接关系或对应关系比较罕见。但拉莫时期则不同,我们经常可以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识别出思想的音乐对应物。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等著名的思想家,都对音乐的表达与创作有着各自的观点与见解。

卢梭作为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作家和音乐理论家,对音乐的看法深受其自然主义哲学影响。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在于能够表达和激发人的自然情感,他强调音乐应该简单、自然,能够直接触动听者的心灵。在他的音乐观念中,情感的真实表达远比音乐形式或技术上的复杂性更为重要。而拉莫的音乐哲学观念更加偏向于理性主义,其理论着重于音乐的和声结构和科学原理,他认为音乐的美来源于其内在的数学比例和秩序,强调音乐表达应该遵循严格的和声规则,这与当时的启蒙时代尊崇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则的趋势相吻合。
同时,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音乐理论家达朗贝尔对拉莫的理论表示赞同,并在他的《百科全书》中为拉莫的理论辩护。达朗贝尔认为拉莫的和声理论是音乐理论发展中的重大进步,它将音乐理论建立在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之上。他尤其赞赏拉莫试图将音乐原理归结为自然法则和数学原理的努力。然而,尽管达朗贝尔在原则上支持拉莫的观点,但他也指出拉莫音乐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与不足。达朗贝尔认为,尽管拉莫试图将音乐理论建立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但方法过于复杂并且在实际音乐创作中的应用有限。音乐的美感和情感表达不能完全归结为数学规律,他强调音乐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感受与表达,应该重视旋律的重要性。这些分歧都体现了音乐的双重性在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倾向之间形成的张力。

拉莫作为法国抒情悲剧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试图从音乐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复杂的双重性,寻求歌剧创作中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和解。然而,拉莫时代的法国歌剧流派仍然完全沉浸于过去,被旧时的习俗和信仰所支配。这些习俗和信仰在本质上不仅不符合启蒙运动的精神,尤其不符合拉莫歌剧中所表达的创新观点。他在面对这些强大且对立的力量时经历了调整与适应的过程,最终他选择延续象征着政权与权力的传统歌剧模式,同时在创作的每一部歌剧中理性和感性做出调整,找到创造性的方法并使其更符合他的歌剧观念。拉莫歌剧创造中的和解,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和”的文化思想——“和”的真正意义是在千差万别的世界中,认识矛盾发展,运用中和之法,求同存异,和谐共生。在拉莫的歌剧创作中,“和”的哲思始终贯穿其中,理性设计和情感刻画在传统的延续与创新的发展之间获得深入人心的效果。
性别的平衡
虽然拉莫似乎遵循了抒情悲剧中存在的性别传统的刻板印象,但他的音乐处理使这些刻板印象复杂化,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更加微妙,通过加入优美的咏叹调、重唱等音乐手段使女性角色在剧中更为突出。拉莫歌剧中女性角色类型广泛,从贤妻良母到复仇女神,从纯洁少女到权力女王。这些角色的多样性展现了女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各种面貌,丰富了歌剧的情感和主题。同样,拉莫在女性角色的情感刻画方面非常细腻,不仅仅是爱情,还包括友情、亲情、嫉妒、复仇等复杂的情感。通过音乐刻画女性角色的性格和情感,利用不同的旋律、和声和节奏来表现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将音乐与角色的紧密结合,使角色的情感表达得更加生动和真实。

在歌剧《希波吕特与阿里奇埃》中,法厄同(Phèdre)作为忒修斯的妻子,不幸爱上了自己的继子希波吕特,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悲剧事件。法厄同的角色复杂,充满激情和内疚。拉莫在第三幕第一场中安排的著名的唱段“来自爱的无情之母”( Cruelle mère des amours),表达了法厄同对爱神丘比特的诅咒,以及她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悲痛。在《双子星卡斯托与波吕克斯》中,特拉伊拉(Téla?re)作为卡斯托(Castor)的情人,在剧中展现了强大的情感力量。在卡斯托死后,她的悲痛和对爱情的忠诚成为剧情的重要推动力。其著名咏叹调“悲伤的准备,苍白的火炬”( Tristes apprêts, pales flambeaux)是整部作品中情感表达最为强烈和深刻的场景之一。特拉伊拉面对着卡斯托的死讯,深感悲痛地为卡斯托准备悼念仪式和葬礼用品,本应用于他们的婚礼的物品却成了葬礼之物。这首咏叹调充满了对爱情的回忆和对死亡的哀悼,展现了特拉伊拉对卡斯托深深的爱恋和无尽的悲痛。通过这首咏叹调,拉莫不仅展现了他精湛的音乐才华,还深刻描绘了特拉伊拉这一角色的情感深度,使得听众能够感受到她的悲痛和绝望。这首咏叹调因其情感的真挚和音乐的美感,成为了巴洛克歌剧中最为著名和动人的选段之一。
这些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以及她们的咏叹调不仅展现了拉莫精深的音乐才华,也体现了他对女性角色独特的理解和刻画。通过这些角色,拉莫探讨了爱情、忠诚、牺牲和女性力量等主题,使得他的歌剧作品具有了深刻的人文价值和艺术魅力。
舞蹈的融合
拉莫延续了吕利创立的法式歌剧风格,这种风格体现了对宫廷舞蹈、合唱以及对法国文化和传统的强调。吕利将舞蹈场景纳入歌剧中,并使之成为法国歌剧的特色之一,拉莫在延续吕利风格的基础上将舞蹈处理得更加丰富和复杂,他将舞蹈紧密地融入剧情和音乐之中,与情节和戏剧人物更加贴合,使之成为推动剧情发展和深化角色情感的重要手段。
拉莫歌剧中的舞蹈不仅仅是装饰性的,而且是被视为与歌唱和戏剧部分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具有强烈的表达性和戏剧性。舞蹈可以直接反映出戏剧人物的情感、性格以及推动剧情的发展,能够增强歌剧的整体艺术效果。在舞蹈风格上,吕利的舞蹈场景通常用于增强剧情的情感表达,或者作为戏剧高潮的一部分,并作为戏剧性情节的装饰或幕间剧,其舞蹈形式倾向于正统和典雅,是皇室威严雄伟的象征,反映了当时宫廷的审美偏好。这些舞蹈场景虽然美观,但通常与主要剧情相对独立,有时甚至会打断戏剧发展的流畅性。而拉莫的舞蹈则更加多样,富有强烈的表现力。拉莫在舞蹈音乐中运用了更加复杂的和声与节奏,使得舞蹈部分更具有感染力。吕利和拉莫在歌剧中舞蹈场景的不同设置及美学思想,不仅体现了两位作曲家个人的艺术风格和创新,也反映了从17世纪到18世纪,法国音乐和舞蹈审美观念的演变。

《双子星卡斯托与波吕克斯》在1737年首演之后于1754年进行了调整与修改。这部歌剧以希腊神话中的双胞胎兄弟卡斯托和波吕克斯的故事为基础,讲述了生与死、爱与恨以及两人的兄弟之情。在1754年的版本中,拉莫在舞蹈场景中增添了视觉的效果,通过舞蹈表达了情感,加强了剧情,使得这部作品在视觉、音乐和戏剧上都更为丰富和引人入胜。

通过《双子星卡斯托与波吕克斯》舞蹈场景设置与戏剧意涵可以看出,拉莫将舞蹈音乐提升到了新的表达高度,每个舞蹈场景都通过音乐和舞蹈的结合以及舞者的表演,深化了剧情的情感和主题。拉莫的贡献不仅仅是对于舞蹈的精心编排,更是将舞蹈在表演中与声乐交织在一起,这种去娱乐化的美学范式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歌剧《双子星卡斯托与波吕克斯》不仅是音乐上的杰作,也是舞蹈艺术在歌剧中应用的典范。
合唱的社会性
拉莫使用合唱来强化歌剧中的情感表达,无论是庆祝、哀悼还是赞美,合唱都能以其强大的音响效果和集体的情感力量,使观众的情感体验得到加深。与吕利歌剧中的合唱不同,拉莫的音乐更加复杂,倾向于使用更加丰富的和声和音乐结构,使合唱部分更具有变化和深度。而吕利通常采用较为简洁直接的音乐语言,注重节奏和旋律的重复,以强调舞台上的动态和戏剧性。
在拉莫的歌剧中,合唱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意涵,它们经常扮演着对话、角色心理状态的反映等更加复杂的角色,来表达神性、命運、自然力量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和主题。通过合唱,这些抽象的概念得以具体化,为观众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而在吕利的歌剧中,合唱通常代表着“群体”形象,如宫廷、军队、神祇等,它们往往表现出对主角的支持或者对抗。与吕利不同,拉莫的合唱能够融入整个音乐的架构之中,与独唱者、舞蹈和乐队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形成更为复杂的声音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