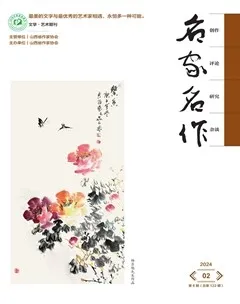论梁晓声近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理想叙事
[摘要] 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塑造了许多真实鲜活的人物形象,其中不乏性格各异、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人世间》中的“天使”郑娟,为理想出走的“娜拉”周蓉,《我和我的命》中的“平凡好人”方婉之,这些女性形象身上凝聚了作家对中国各阶层女性命运的关注,借助他们的人生故事,表达了作家对理想女性、理想人性和理想社会的思考探索。
[关 键 词] 梁晓声;《人世间》;《我和我的命》;女性形象;理想叙事
无论在20世纪的知青文学,抑或21世纪以来的《伊人伊人》《人世间》《我和我的命》等作品,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塑造了许多真实鲜活的人物形象,其中不乏性格各异、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梁晓声自己曾说:“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主义——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1]这种理想主义的写作诉求不仅寄托于他笔下的知青形象,也同样延伸到了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身上。尤其是《人世间》中的“天使”郑娟,为理想出走的“娜拉”式周蓉,《我和我的命》中修炼“三命”的方婉之,这些女性形象身上凝聚了作家对中国各阶层女性命运的关注。她们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经营,对家庭和事业的取舍,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补充丰富了梁晓声有关理想主义的思想内核。
作为叙事线索贯穿《人世间》始终的,是周家三个儿女的婚恋故事,向读者集中展示了三种不同的理想爱情与理想人生方式,同时也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女性群像。其中,以做“贤妻良母”为荣的传统女性郑娟与 “娜拉”式的现代女性周蓉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坚守的“天使”郑娟
在《人世间》中,主人公周秉昆的妻子郑娟正是 “家宅中的天使”的典型演绎,她的身上集合了许多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外表美丽,内心善良,无怨无悔,无私奉献。周秉昆平淡无奇的人生也因为与郑娟的相遇相爱而逃脱无望的黑暗,进而显现出某种传奇色彩。青年工人周秉昆受人所托去救济被处死刑的工友涂志强的家人,见到了美丽柔弱、孤苦无依的年轻寡妇郑娟,还有她卖冰棍的老母亲和盲眼弟弟光明,秉昆第一次见到郑娟,就仿佛瞬间被按下开启情感欲望的按键,在初步激发的好奇、同情以及狂野的情欲冲动之后,秉昆的灵魂便被郑娟及其家人的苦难境遇悲剧深深震撼到了:“眼前的郑娟有张蛾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楼梦》中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恓惶,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惜香怜玉起来,周秉昆当然也不能例外。”[2]90-91在黑暗简陋的破旧老房子里,深陷生存险境的郑娟如一个等待着牺牲也等待着拯救的圣母一般,发散出微弱但圣洁的母性光芒。郑娟的身影仿若《少女与死神》的插画,也仿佛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美人》变成了现实,她被周秉昆的主观想象附加上一层神秘朦胧的艺术光辉,使得她即使身处黑暗,却像无法埋没的宝石一般。但是,当理智回归,现实困境摆在眼前时,周秉昆清楚如果自己娶了这个拖家带口的寡妇,他不仅会承受沉重的道德压力,更会成为整个周家的罪人。二人的僵局在他们第三次相见时,被郑娟打破了。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以近乎献祭的大胆态度,主动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爱献给了周秉昆。在这一行为中,我们看不见丝毫的卑贱,只有全然的纯洁。由此可知,郑娟绝不像她的外表那般柔弱,也绝不会只等待来自外界他人的拯救,面对可能的幸福,她会毫不迟疑地主动抓取。这是由于,郑娟拥有着难能可贵的一颗心,这心灵是如此美好、纯洁、坚定与勇敢。在今后与秉昆的人生历程中的种种遭遇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变故和意外,郑娟都能第一时间撑起家庭的屋檐,扛起男人也深感沉重的责任。当秉昆被捕入狱时,郑娟不顾“没名没分”的舆论压力住进周家开始操持家务,以一己之力维持住了濒临崩溃的周家,细心照顾着秉昆和她自己的家人。当秉昆屡次遭受生活的打击,当儿子周楠意外身亡,每一次都是郑娟勇敢地站出来,用行动展现出令人钦佩的坚强。
可以说,周秉昆和郑娟的爱情最初来自男人对弱女子的同情之情与拯救之心,但是到了后来,是像水一样柔情婉转,更像水一样坚韧的郑娟在婚姻家庭中起到了“主心骨”的重要作用。可见,真正的爱是对彼此的无私奉献,其本身所蕴含着的彼此拯救、互相分担的力量使郑娟和周秉昆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互相救赎,度过了虽然跌宕起伏但不失幸福的一生。
郑娟是毋庸置疑的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是典型的旧式女子,她自己也始终以做一个符合传统美德要求的贤妻良母为荣:“跟你们说实话,我可乐意当家庭妇女了,做做饭,拾掇拾掇屋子,为丈夫儿子洗洗衣服,把他俩侍候好,我心里可高兴了。我觉得自己天生是做贤妻良母的,不是那些喜欢上班的女人。”[2]263正如作家所言,女性“温和、冷静、耐心、最肯牺牲”的“美德”能够治愈男性的“迷惘、痛苦、狂躁”,“好女人”是可貴的。[3]20做一个对丈夫、孩子和家庭有益的好女人,这也是郑娟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道德期许。不同于受过文学审美熏陶的周蓉,也无法与出身上流的郝冬梅相比,郑娟知道自己只适合做好“贤妻良母”,但郑娟对此毫不自卑,她明白自己的能力和特质,她乐于接受命运对她的安排也好,馈赠也好,考验也好。郑娟单纯但绝不无知,虽然她对文学、政治和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缺乏了解和认知,但她深谙生活的智慧,她懂得底层人民最朴素的人生道理,那就是要善良、感恩,做个好人。正如孔特在《小爱大德》中所说的:“单纯是智者的美德,也是圣徒的智慧。”[4]149其实,越是简单的东西,越难被人理解,郑娟的单纯令人欣赏,其强大亦令所有人钦佩。在《人世间》的故事最终,看似最平凡的秉昆和郑娟凭借着友情、爱情、家庭、婚姻和仁义的力量得到了最朴素和最伟大的互相救赎。当然,如果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来审视郑娟,郑娟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女性主体意识的:她被动地以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她甘于乃至乐于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而忽视了自己的个体价值,她被拘囿于家庭中而从不主动参与社会生活,这导致她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人和家庭这一小环境。小说以周秉昆的视角立场肯定了郑娟对家庭所做的无私奉献,却忽略了对其个体价值的关注,但郑娟毕竟不是周蓉那样饱读诗书的叛逆知识女性,运用“主体意识”这样的要求去衡量特定时代语境下这位“家宅中的天使”,未免过于严苛。
二、出走的“娜拉”女神:周蓉
美丽、独立、坚定、勇于反抗的周家二女儿周蓉在小说里被称为“爱神的化身”,从小她超乎寻常地热爱文学、热爱自由,从书籍中感染到“不自由、毋宁死”的思想。无论是求学和工作过程中的起伏,还是爱情与婚姻经历里的得失,她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塑造周蓉这一极具魅力的“新”女性形象,作家表达了他对新时代背景下,女性勇敢追求自由、实现独立人格的理想期待。
周蓉的一生都与文学、与美息息相关。是文学教会了周蓉,女人应该独立思考;是文学告诉周蓉,追求自由和大胆“出走”的意义;当然也是对文学狂热开启了周蓉的初恋,少女周蓉爱上了一个远在北京的“右派”诗人冯化成。因为对文学共同的痴迷,周蓉认为自己与诗人在心灵上已经合二为一,为了与冯化成结合,她瞒着家人与落难的诗人一起下乡到贵州一所小学教书,不久后生下一个女儿,过上了她理想中诗一般的理想生活。可惜,如诗如梦的爱情经不起世俗的挑战。高考恢复后,周蓉顺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夫妻两人回到了北京。但是大城市里不仅有梦想、有机会,还有令人目眩的诱惑,周蓉发现了自己丈夫沽名钓誉的真面目,她终于拨开了遮蔽在其眼前长达十几年的玫瑰色迷雾,陷入了对自己判断力的短暂的迷茫。直至丈夫冯化成与其身边的女记者、女诗歌爱好者、女文学青年(就像曾经的周蓉)不断发生着艳遇,经历“丈夫出轨—原谅—再次出轨”的不断重复后,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周蓉的爱情梦被无情地戳破了,这段婚姻终于被按下了停止键,她毅然提出了离婚。
周蓉的第二段婚恋故事选择了年少就苦恋追求她的蔡晓光。如果说周蓉将冯化成当作文学与理想的化身而无悔追求的话,那么同时,蔡晓光也将周蓉当作了自己的“女神”,视其为文学与美的化身。在小说中,蔡晓光不止一次向周蓉表白自己的真挚情意:“由于人生中有真爱,我活得越来越知足,也越来越愿意做好人,越来越善良了。”[2]296在周蓉和蔡晓光看来,爱的理想足以引导每一个平凡的人成为理想的人,爱的力量亦能启示我们走向更好的人生道路。可惜的是,真正的幸福不仅来得有点晚,甚至很快迎接了重大的考验——为了追回被前夫冯化成带去法国的女儿,周蓉只身踏上寻亲的道路,这一去就是夫妻二人长达十二年的分居分离。在这段漫长孤独的日子里,事业成功、魅力十足的蔡晓光吸引了各色女人前仆后继来“献身”,虽然偶尔也会耐不住寂寞,终究克制地坚守住了对周蓉最纯粹的爱。二人重逢后,蔡晓光坦诚地向周蓉做了深刻的检讨、剖白,彼此达成了谅解,重新燃起了婚姻之爱的火花。
在小说中,作家始终没有忘记对周蓉完美形象的强调和保护。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打拼、寻亲的周蓉,社会角色从大学教授迅速转变为在商店和旅行社打工的流浪者,即使如此,周蓉始终是那个美丽、自信、坚定、强大的“女神”。没过多久,不再年轻的周蓉又因为她那“略显忧郁又高傲的气质”在异国他乡引起像年轻时候那样的高回头率了。“她仍然愛美,每天上班,她都要对着镜子仔细将头发盘起,绝不允许有一丝乱发。她那么认真不仅是出于爱美之心,也是职业使然。周蓉很在乎自己作为职业女性能否给人以自信而美好的印象。她很敏感别人的目光,她常常觉得自己其实也是中国职业女性的形象使者。”[5]111
梁晓声在曾对自己心中的理想女性做出过阐述:“首先她是美的,其次她是善的,第三是她的爱超越了世俗……”[6]可见作家对理想主义人格的塑造过程蕴涵着他独有的审美追求。小说中,作家不吝笔墨描绘周蓉美丽的外表,其实在周蓉美丽的外表之下,更加珍贵的是她独立强大的人格和追求自由的高贵灵魂。具体而言,周蓉是以其三次大胆“出走”行动勾勒出了现代女性突破束缚,改变命运,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蜕变历程。第一次“出走”发生在周蓉少女情怀萌动的青春期,为了追求被其视为信仰的爱情,少女无惧道德舆论的压力,孤身一人从东北奔赴贵州与冯化成结合。周蓉离开了父母的家,开始她叛逆大胆、勇敢追梦的人生冒险。第二次“出走”发生在周蓉的中年。意识到丈夫的庸俗真面目,对一次次的背叛忍无可忍之后,周蓉离开了与丈夫的家庭,经由此,周蓉进一步成长为理性、独立、清醒的成熟女性,以无限的勇气和魄力重新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周蓉孤身一人远赴异国他乡寻找女儿的第三次出走,证明了她之前“以己为先”的价值立场有所转变,她开始认识到自己应该担负起对他人命运的责任。周蓉不同时期的人生追求与选择,透视出那一代知识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艰难过程:不断逃离、出走,经历受伤、疗愈,最终成长、成熟。可以说,《人世间》中的周蓉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和她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取舍,是作家对“娜拉”式女性做出的新思考。
当然,周蓉这一形象是理想主义的,但肯定不是完美的。为爱情第一次“出走”时,青春稚嫩的周蓉满心都是自己渴望的诗意人生和纯粹爱情,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此种任性行为会对家人朋友造成何种无法挽回的情感伤害;在第三次出走时,周蓉将丈夫蔡晓光独自留在国内十二年,很难想象如果不是丈夫的坚持守望,这段婚姻能否再续前缘。郑娟以贤妻良母的家庭辅助角色实现了自身价值,而周蓉是自己人生戏剧的导演编剧和唯一主角。她可能不是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实现个体自我价值为目标的个人主义者,这显然背叛了传统女性被要求遵循的道德伦理规范。但是周蓉不在乎他人的批判眼光,她拥有独立自主的强大自我,她全身心关注的是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她属于她自己。小说中曾这样描述周蓉对理想信仰的坚持:“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7] 87很明显,周蓉是作家心中对理想主义精神追求的勇敢实践者,符合作家对集“美”“善”“爱”为一身的理想女性的审美想象。
三、“平凡好人”方婉之
借助“好人”形象传播 “好人”文化,阐释对“现实应该是什么”的思考,是梁晓声一直以来在文学创作中致力实现的目标。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延续了《人世间》具有理想色彩的现实主义风格,透过小说主人公方婉之从一个被遗弃的山区女孩成长为“好人”的各种际遇,表达了作家对“好人”哲学的理想化思考,而方婉之和她的“命”,也从某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命”。
方婉之出生于贵州山区一个叫神仙顶的地方。虽名为“神仙顶”,实际上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加上当地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出生不到一天的方婉之便被亲生父母遗弃在县城,被护校校长方静妤收养。不同于《人世间》中周蓉通过三次“出走”来完成人格的淬炼,方婉之是通过“三命”的修炼来实现做一个“平凡的好人”的人生目标。养母方静妤曾向年幼的她解读何谓“三命”:“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这决定了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 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实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观,是生活与命的关系的组合词;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8]50被身居高位的养父母收养并精心爱护,足以证明方婉之的“天命”是优越的,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方婉之的成长提供了珍贵的养料。养母去世后,方婉之意外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遭受巨大的情感刺激后,她选择辍学逃离家庭和家乡,远赴深圳打工。从大学生变为打工妹的经历中充满了意外、危险乃至对人性的考验,但方婉之始终保留着家庭环境赋予她的良好品格:善良、宽厚,善于思考,在好朋友李娟和丈夫高翔的帮助支持下,她最终成为一名企业家,经由此种“实命”,方婉之进一步完善了她的“好人”形象。虽然大学辍学,但是在方婉之的青少年时期,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她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且养成了热爱读书、终身学习的习惯。方婉之先是通过自学,通过了深圳的“新居民考试”,之后又考取夜大文凭,高效地完成了新的身份认同。这其实就是方静妤所说的文化给的“自修命”,“自修命”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让她更有自信,更有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她做“平凡好人”的理想。
梁晓声曾给自己笔下的“好人”以定义:“无论对于男人或女人,无论对于年轻人或长者,第一善良,第二正直,第三富有同情心,第四敬仰人道主义懂得理解和尊重美好事物,大致也算一个好人了。”[9]349不难发现方婉之与郑娟有许多相似的特质。从出生即被遗弃的方婉之,仍然无法割舍与原生家庭的血缘之情,面对亲人们的苦难,她无法置身事外;面对老家亲戚们对她这个“有钱人”的骚扰,她也多次不計前嫌伸出援手;面对工友同事,她也敢于主动站出来帮助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惜自己丢了工作……虽然她与郑娟的“三命”并无相似,但是她们具有一致的价值立场,表现出宽容大度、无私奉献的美好品德,身处都市的企业家方婉之和守护家庭的郑娟都是“好人”标准的实践者。
方婉之也经由一次“出走”开始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只不过《人世间》中周蓉的“出走”基于其追求爱情和理想人生的自主选择,而方婉之的“出走”源于被亲情、爱情所伤后的无奈逃离,恰如她离开神仙顶也源于被遗弃的不幸“宿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管周蓉担负了何种社会角色:下乡到贵州山区的青年教师,京城重点大学的教授,抑或私立中学的副校长,周蓉始终是一个主动的教育者角色,以丰富的知识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影响着其他人。而在方婉之从贵州偏远山区到小县城,再到现代都市深圳、上海的人生经历中,好友李娟和爱人高翔或多或少地承担了“引导者”的角色,帮助她积累生活经验,掌握为人处世的方法,每次方婉之遇到令自己手足无措的困难时,都是丈夫高翔站出来,运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帮助她解决问题,渡过难关。由此而见,方婉之缺乏周蓉的独立和理性,其“好人”人格的完善需要借助他人的“教导”。值得注意的是,周蓉更为强调个体价值的充分实现,而方婉之在追求理想人生的同时,始终不忘帮助亲人、朋友、同事和父老乡亲,坚持兼顾家庭亲情集体。从这个角度看,方婉之这一形象更像是周蓉和郑娟各自优良品质的结合体。
“文学应该书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10]作为一个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梁晓声敏锐观察到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也察觉到在急速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的矛盾问题,他将自己观察到的社会现状和矛盾问题通过笔下人物的曲折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天使”般的郑娟、“娜拉”式的周蓉抑或“平凡好人”方婉之,她们遭遇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她们对家庭与事业的抉择处理,她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叛逆与犹疑,既承载了作家对女性的审美想象,也反映了作家对中国女性在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命运的关切与思考,进而表达作家对何为“理想女性”,何为“好人”,“现实应该怎样”的思考与实践。
参考文献:
[1]丛子钰.梁晓声.现实主义亦应寄托对人的理想[N].文艺报,2019-01-16(2).
[2]梁晓声.人世间:上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3]梁晓声.好女人是一所学校:梁晓声散文精选[M].深圳:深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6.
[4][法]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小爱大德[M].赵克非,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5]梁晓声.人世间:下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6]梁晓声.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关于创作中若干问题答读者问[J].中国文化研究,2019(4):2-6.
[7]梁晓声.人世间:中部[M].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8]梁晓声.我和我的命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9]梁晓声.关于 《好人书卷》[A].梁晓声文集·散文 10[ C].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
[10]梁晓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关于《人世间》的补白[J].中国文学批评,2019(4):31-32,158.
作者简介:
马媛颖(1986—),女,青海西宁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青海师范大学中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2QSK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