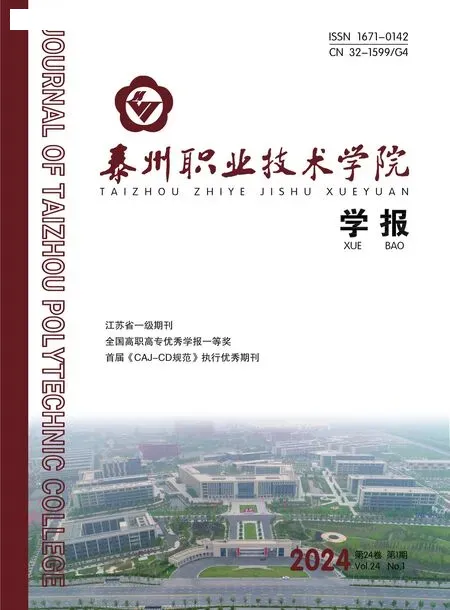费孝通与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思想交融
李红梅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江苏 泰州 225300)
费孝通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但学界甚少有研究者关注马氏学术思想对费孝通思想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研读马氏文化思想的相关文献,分析费孝通重读《文化论》《江村经济·序言》以及《文化动态论》等文献的所感,探寻马氏文化论思想对费孝通的学术影响,这对中国社会发展及其话语体系建设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1 费孝通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师生缘
马林诺夫斯基作为20 世纪初期英国最突出的社会人类学家,创设了亲自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法,拉起功能主义的大旗,开始了以实证主义为主的功能派人类学研究。
费孝通1930 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师从吴文藻。1933 年在导师吴文藻的推荐和帮助下,师从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史老师用欧洲大陆盛行的功能主义人类学方法教授费孝通,费孝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开始学习马氏的功能主义。1936 年费孝通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费孝通博士毕业后,师生未再有缘相见,但马氏思想对他的学术指引影响其终生。本文从费孝通出国前、在英国、回国后三个时期分析他们的思想交融。
2 费孝通出国前受到的马林诺夫斯基思想影响
1930 年到1933 年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期间,学生们提出“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学术为实用”之争, 吴文藻“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介绍进来,为学以致用提出了更有力的理论基础”[2]。
1933 年费孝通开始师从俄国教授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史老师采用马氏功能主义中的生物(物质)需求理论、文化的整体论和系统论指导费孝通学习体质人类学。后来有人在读到《江村经济》后询问费孝通“你怎么会在没有和L.S.E 接触之前,就走上了功能学派的路子?”[3],直到那时费孝通才明白他“从史禄国那里学来的这些东西,着重人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原来就是马氏功能论的组成部分”[3]。
1934 年费孝通运用功能主义思想完成了与后来的“江村”调查“格调完全一致”的社会实地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这个报告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整体性功能主义思想:瑶族社会的家庭、亲属、村落、族团的各自特点和密切关系被视为一个完备的整体系统。这个报告被吴文藻誉为用“功能法”考察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社区研究实例和基石[4]。
费孝通出国前学习社会学的经历表明马氏功能主义思想在30 年代已经传到欧洲的人类学界和中国的社会学界,并开始为学者们接受和应用。这段经历解释了马氏为何在第一次见费孝通关于“江村”的草稿时就非常中意,因而从弗斯的手上接过来自己亲自指导其博士论文的撰写及后续的出版工作。
3 费孝通在英国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
1936 年秋费孝通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马氏,学习时长两年。第一年学习《文化论》,第二年学习《文化变迁的动力》。同时,费孝通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江村经济》。
1936 年吴文藻得罗氏基金资助,重游欧美各国,与马氏相聚数月,畅谈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问题。临别之际,马氏宴请吴文藻,赠送《文化论》初稿,并嘱费孝通翻译,先行在中国出版。之后,1940 年《文化论》在中国出版,费孝通欣然写下《译序》,记录该书的形成过程,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视角分析马氏思想,并阐述其译本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之意义。
1938 年费孝通完成《江村经济》博士论文,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当年暑假,费孝通从英国辗转回国,用马氏的功能主义理论和田野调查法开始他自己的中国社会学田野实践。1939 年马氏将《江村经济》这篇论文介绍给Routledge 书局,编辑阅后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最终以Peasant Life in China(《 一个中国农村的农民经济生活的调查》)为题出版,马氏欣然写序。
1942 年马氏病逝后,他的学生P.M.Kaberry 整理马氏遗下的有关文稿和笔记,编成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文化变迁的动力学——非洲种族关系的探讨》)一书,1945 年4 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时中国兵荒马乱,费氏与外界失去联系,直到90 年代才借到该书的复制本。因此,费氏重读该书,写出读后感,并用作第三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讲稿,供大家阅读、讨论。
4 费孝通回国后对马林诺夫斯基思想的应用、研究与发展
1940 年之后因世事纷争,费孝通的学术发展受到阻碍甚至耽搁,之后一直到80 年代,他才能够继续他学术的第二人生。此时,马氏的思想仍然指引他前进的方向。其应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直接采用马氏的功能主义学派的参与观察法,开展各项社会研究,以建立社会学的中国学派;(2)重读马氏相关论文,分析其关于文化的思想、变化及其对当今中国发展的指导意义;(3)重解马氏思想,继承、发展与融合并用,提出“文化自觉”。
1995 年到1997 年费孝通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和《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重点分析了马氏思想三个重要的变化阶段:从书本研究到实地参与观察调查,从对野蛮人的研究到对文明世界的研究(从“他文化”到“己文化”),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概述其对人类学的学术贡献。同时,费孝通将上述思想内容分三次在北京大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分享,探讨马氏思想对当今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指导作用,足可见这些文字对费孝通的影响力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4.1 《文化论》及《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文化论》是马氏在写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后的第一本理论著作,是对他的功能主义思想和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总结与概括,即人本主义的文化论。此外,《文化论》实际是对“文化表格”所作的理论说明,是马氏为人类学者准备的在田野工作时的指导性参考表格。马氏与吴文藻的临别赠礼中包括一份“文化表格”的打印稿,后来译成中文收入《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4]。
关于文化的概念,马氏接受了前辈泰勒(E.B. Tylor) 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中关于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其他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一切其他能力和习惯。在此基础上,马氏增加了物质方面,解释“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以及价值而言”。他认为文化是“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人工体系”,文化是生活的手段,“是为人们生活服务的体系”[4]。
马氏文化论思想把文化作为物质、语言、社会和精神结为一体,填补了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裂缝。人文世界是文化的总体,是自然世界中的人自己创造的以物质为基础的世界。研究文化所代表的人文世界就要研究人的生活,即文化的四个方面,四者缺一不可,同时作用。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去观察和分析以取得有概括性的知识,可以成立人文的科学。
再次,语言与历史不可分割。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化是历史的积累、继承与创造。历史的发展带来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差异和变化。马氏提出反对重构历史学派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反对将自己看到的或设想到的具体的历史文化强加于其他不相干族群,反对凭空臆造的历史,不是反对研究文化的历史,而是要“强调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的实证论”,这是他倡导科学人文主义的一个初衷。
最后,《文化论》所反映的生物(物质)需求理论。20 世纪初,马氏强调以生物需求作为文化的基本需求,后受当时“行为学派”的影响,逐步接受“需求”是个体和群体生存的必要条件,接受“文化并非简单地从生物基础上直接演化而来,而是通过人类形成了群体,有全体的集体生活而产生了社会组织,才形成复合整体的人文世界”[7]。马氏将文化分列了三类不同层次的需求:生物需求、社会需求及精神需求,层次间逐渐递进,后者以前者为基础, 三者共同形成文化。
4.2 《江村经济·序言》及《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1938 年马氏安排《江村经济》的出版事宜,并在序言中评价该书是人类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但费孝通认为,此书只是“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1]。
30 年代时的费孝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之大。直到1981 年费孝通获得人类学学科中最高的荣誉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他再次踏上英国的土地去领奖,与同行交流后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价值。马氏描述该书的意义在于费孝通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以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的本乡人民作为调查对象,完成了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本书是对马氏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升华,完成了马氏关于文化发展的一些还无法实现的梦想,解决了马氏想要解决而无法解决的人类学发展面临的两大问题:“他文化”向“己文化”过渡和民族志在文明社会的适应。
首先是马氏想从研究“他文化”转向研究“己文化”。马氏的民族志调查对象主要在澳大利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以及后来的非洲和墨西哥,研究的是以没有文字的原始部落为主的“他者”的“静态”文化,马氏是以一种贵族姿态和外来者的身份参与并实施的田野调查。而费孝通是对现代文明中的“自己”社会的动态研究,以“自己人”的身份参与到“自己”的社会中调查。因此,马氏盛赞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弥补了他自己学术的空白和遗憾,这预示着马氏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30 年代末期马氏已经意识到现代人类学的转向问题,只是限于现实而无法实践。费孝通通过“江村”否定了人类学只能对他者文化的研究,实现了从“他者”到“自我”的研究,开辟了人类学研究的新路径。这是两位学者思想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融、继承与发展。
另一问题是民族志方法是否只能用于研究简单的“野蛮”社区,而“不能用于我们自己本地的‘文明’社区”研究?费孝通在研究中发现:与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的历史性研究相比,功能学派更具有科学性,更贴近现实,更适宜从现实社会中寻找问题和发现问题,也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们接受了功能学派的方法,并不断尝试运用这一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们自己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是不容易的,但“不容易”并不等于“不可能”。因此,完成花篮瑶的田野调查之后,费孝通希望用同样的方法研究江村,以期证明该方法可研究不同性质的社区。这种学术研究带来的的方法论上的思考与探索使得费孝通“无意”间参与到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变革之中,解决了马氏的困惑,确认了田野调查法既可用于研究非洲的野蛮社会,也可用于研究亚洲的文明社会,成就了《江村经济》的“里程碑”地位。
4.3 《文化动态论》及《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
《文化动态论》原名是《文化变迁的动力学——非洲种族关系的探讨》。费孝通修改此书名有一定用意。对于90 年代的中国来说,书中有关非洲殖民地人生活的具体叙述和分析已没有指导意义,只具有历史意义。他认为研读该书的重点应是“直接从这段历史的教训入手”,考虑当今社会发展如何“延伸和发展马老师所提出的有关文化动态论”的观点[5]。
马氏依据自己30 年代非洲人类学考察的见解,指出其原本主张的文化功能一体论的缺陷,认为文化研究不能再局限于单一而自立的空间,而应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寻求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与手段。马氏的文化论思想开始从文化整体论转向多种文化并存的观察,人类开始文化的动态研究。
首先是马氏的讲述从“文化表格”转向提倡文化“三项法”。1937年暑假马氏到非洲访问看到了变化中的非洲。当时的欧洲列强已经进入非洲,非洲地区一分为三:一是已经完全被欧洲文化同化的地区;二是受欧洲文化半冲击地区;三是还完全没有被欧洲文化侵蚀的地区。这次访问对他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之后,马氏不再提“文化表格”,而开始用“三项法”分析文化动态。
其次是马氏的文化观从静态转向动态。马氏讨论主题的变化反映了其学术思想的变化。1937年的非洲殖民地和1915 年的特罗布里恩特群岛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前者因欧洲的入侵,文化正在或已经发生变化,而后者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没有外来文化的侵入。因此,之前以静态文化分析为主的功能主义的基本理论遇到变化中的非洲文化,表面看是对原有功能主义思想的修改,其实是对不同文化接触引起的文化动态的分析,这一变化过程是人类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变化。
最后从马氏的文化动态思想到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晚年的费孝通一直提倡学术反思和讨论,他自己身体力行,重读马氏文献,与学者同行展开讨论。面对21 世纪多文化共存和交际问题,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
费孝通引用马氏《文化动态论》的结语“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他解释是“殖民主义不可能解决文化共存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讲,以力服人为之霸,以理服人为之王。霸道统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6]
5 结语
马氏与费孝通的认识与缘分,其实来自于他们对田野调查同样的思考。
费氏对于马氏思想的继承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关于“文化”的思想,形成后来的“文化自觉”;二是关于“科学的人文主义”,是费氏在多个文献中反复呼吁的“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文化”[7]。此外,费孝通在继承马氏功能主义思想和方法论的同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对该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客观地认识该思想的局限性,拓展其理论的空间范围,增强其解释能力。因本文篇幅有限,有关费孝通对功能主义思想的修正与拓展将在后续文章里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