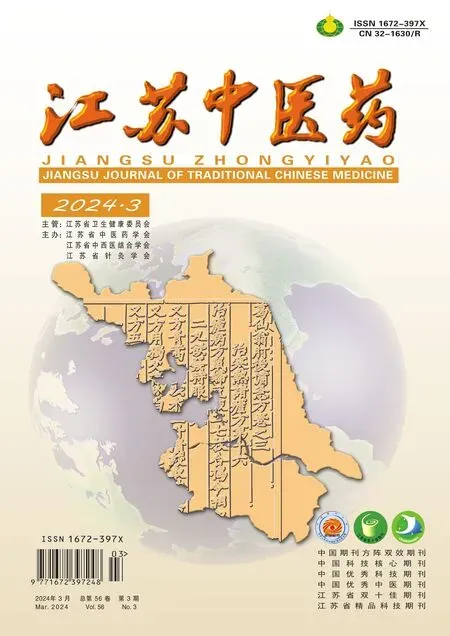基于“土壅木郁-膏脂转运障碍”辨治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思路探析
李世淋 赖秀玲 宁 博 冯兰栓 余湖斌 赵明君
(1.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陕西咸阳 712046;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陕西咸阳 712000)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简称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心肌缺血缺氧的心脏病,严重威胁人的生命健康,给国家、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1]。目前CHD已被描述成为一种由脂质驱动的纤维增生性疾病[2]。由胆固醇逆向转运障碍引发的血脂代谢异常是CHD的病理基础。研究表明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等脂代谢异常是CHD发生发展的致病性危险因素[3]。因此,调节血脂异常,有益于截断CHD的恶化转归,缓解症状,改善预后。目前在CHD基础治疗方案的前提下联用他汀类、贝特类等药物进行降脂治疗,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肝损害、肌损害等副作用不容忽视[4]。
中医学认为脾生膏脂,并依赖肝之疏泄功能转输全身。CHD合并血脂异常归因于膏脂转运障碍,与肝脾密切相关,属脂质代谢失调性疾病[5]。《灵枢·卫气失常》[6]101言:“众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与气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称其身,命曰众人”,指出膏脂在人体中的动态平衡调控着人体的气血平和、形体协调,是人体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若土壅木郁,肝脾疏泄运化功能失司,膏脂转运障碍,沉积血脉而生湿、浊、痰、瘀、毒,日久则发为胸痹。本文基于“土壅木郁-膏脂转运障碍”探讨CHD合并血脂异常的理论机制,以丰富土木关系理论,冀为中医药干预CHD合并血脂异常提供新思路、新靶点。
1 “土壅木郁-膏脂转运障碍”之理论内涵
《读医随笔·升降出入论》[7]云:“脾主中央湿土,其体淖泽……静则易郁,必借木气以疏之……故脾之用主于动,是木气也。”脾将水谷转化为精微,肝受滋养得以疏泄全身气机,将膏脂输送至全身各处,则气机有序,升降协调,人即安康。肝脾在生理上相互联系,在病理上必定相互影响。“土壅木郁”乃因五行相克关系异常而出现乘侮的病理状态,是脾土壅滞引起肝木郁滞。脾土壅滞多因外邪侵袭中焦,气、血、痰、火、湿、食等壅滞,或因脾虚失运而壅滞,同时情绪失调、郁闷失落也可致脾土气结而壅滞。秦伯未[8]在《谦斋医学讲稿》中提及“土壅木郁”是脾胃湿滞、肝失条达所致。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认为肝郁气滞与中焦痞塞互为因果,终成“土壅木郁”[9]。周莉涵等[10]认为脾失运化使湿浊内生、阻滞气机,枢机不利、脾病传肝是土壅木郁的内在病机。秦进芳等[11]提及土壅责之脾虚,脾虚失运影响肝之疏泄,形成土壅木郁的恶性循环。田晓玲等[12]提及土壅木郁与情志失调、劳倦内伤导致中土壅滞、肝木失于调达有关。实证、虚证日久易演变为虚实错杂证,导致恶性循环[13]。综上可以看出,“土壅”之因或实、或虚、或虚实夹杂,易致“土壅木郁”之变。
中医学并无“血脂”之名,目前普遍认为中医学著作中的“膏脂”与现代医学中的脂质大致相同。《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认为脾生膏脂[14],《灵枢·五癃津液别》[6]67言:“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阴股。”说明膏脂为脾所生,经气化温煦后化为膏脂精微,经肝脾输送至全身各处滋养和保护肢体官窍。“土壅木郁”导致膏脂生成与转运障碍,积于体内,留于脉中,与血液相合,终致高脂血症[15]。血脉之中湿、浊、痰、瘀、毒等病理产物积聚,血行凝涩,痹阻心脉,最终发为“胸痹心痛”“真心痛”等。正如《儒门事亲》[16]所云:“夫膏粱之人,起居闲逸,奉养过度,酒食所伤,以致中脘留饮胀闷,痞膈醋心。”
2 “土壅木郁-膏脂转运障碍”为CHD合并血脂异常之核心病机
究其根本,CHD合并血脂异常是“土壅木郁-膏脂转运障碍-复合病变”的多因素、多环节、多层次的复杂病理过程。“土壅木郁”导致膏脂转运障碍,留滞的膏脂积于血脉之中导致血脂异常,湿、浊、痰、瘀、毒内生,病理产物与血相互胶结形成粥样斑块沉积,最终发展为CHD。
2.1 土壅木郁,膏脂失衡为先 脾气健运是现代研究人体能量代谢平衡、脂代谢的先决条件[17]。脾气健运,膏脂正常化生转运对人体正常运转具有重要作用。《类经》[18]载:“郁则结聚不行,乃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病作矣。”肝脾失和,肝气郁结则疏泄、运化失责,小肠分清泌浊功能失调,导致膏脂代谢失衡,转运障碍,留于脉中,则阻滞脉络,溢于皮下则形成“纵腹垂腴”“虽脂不能大”“上下容大”等不同肥胖状态,导致血脂异常。进食过量碳水化合物、糖类、蛋白质、脂肪等,导致脾土壅塞,肝木郁滞,膏脂化生失度、转运障碍,具体表现为以TG、LDL-C为主的检验指标升高,血管内脂质沉积并有斑块形成,增加了CHD的发病风险[19]。“土壅木郁-膏脂转运障碍”导致膏脂留于脉中化生成浊,凝结为脂凝、脂结附着脉中,成为CHD合并血脂异常早期的病理特点和致病因素[20]。由此可见,肝脾失调,膏脂转运障碍是CHD合并血脂异常发病的始动环节,“土壅木郁-膏脂转运障碍”致使气血凝涩,变生脂结,脉积渐成是CHD合并血脂异常初期的主要原因,早期积极干预膏脂转运障碍,防治脉积形成是此阶段的关键措施。
2.2 膏脂化浊,酿生痰湿为本 《素问·通评虚实论》[21]曰:“甘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土壅木郁,中焦受损,膏脂转输障碍,酿湿生痰,可形成“膏人”“肉人”“脂人”等不同肥胖形态[22]。心为血脉汇聚之所,膏脂生痰聚湿停积血脉之中,气机凝涩,易变生实邪[23]。膏浊为阴邪,重浊黏滞,痰湿内阻,阴乘阳位,上犯心脏,积滞凝结不畅,闭阻心脉,致使心气鼓动无力,心脉血液不得充盈,心失濡养,不通则痛,不荣则痛,发为胸痹心痛。痰湿上犯心胸,则心胸闷痛、喘憋;阻于中焦,则见痞塞满闷,纳呆脘胀,头身困重,痰多体胖,口黏乏味;伴有舌苔胖大、浊腻、边有齿痕、脉滑数等临床表现。现代医家认为,膏脂与血脂相似,能够调节糖脂代谢而影响能量代谢,是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物质,CHD合并血脂异常的患者具有更高的心血管事件风险[24-25]。总而言之,“土壅木郁”,膏脂化浊,酿生痰湿,是CHD合并血脂异常的病机之本,贯穿了本病发病的始终。
2.3 痰瘀同源,毒瘀互结为变 膏油皆脾所生,脾为生痰之源,如果脾失健运,则水湿停聚,而成饮成痰。痰与瘀的病理变化,似乎各有其源,然而追溯其本,痰源于津,瘀本乎血,痰浊瘀血久郁于内易化火,熬津为痰,滞血为瘀,二者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或先瘀而后痰,或先痰而后瘀,最终导致痰瘀同病,进一步加重膏浊沉积。由此可见,痰湿、瘀血内结实为“无形之邪”到“有形之邪”的病理演化过程[26]。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27]中云:“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可认为痰阻则血难行,血凝则痰易生,痰必化瘀,瘀必生痰。痰瘀互为因果,相互转化,最终导致痰瘀同病,成为加重心脉不通的二次病因。痰瘀阻滞,膏浊久而不去,内郁生热成毒,毒瘀侵害血脉则可见毒瘀搏结、痹阻心脉。“土壅木郁”导致气化停滞,湿滞日久聚而为痰,无形之痰浊膏脂留滞皮下,则致形体肥胖,积于脉中日久则痰瘀互结,膏浊沉积,毒瘀损心,变生粥样斑块这一“有形之邪”。且痰、瘀、毒作为“土壅木郁-膏脂转运障碍”的病理产物和二次病因,参与了“血脂代谢异常-粥样斑块沉积-血栓事件”的整体过程,毒从邪化、变从毒起,最终导致本病反复发作,缠绵难愈。
3 辨治思路
3.1 健脾疏肝以平和 《素问释义》[28]云:“中枢旋转,水木因之左升,火金因之右降。”若中焦脾胃失调,则升降失司,气机不畅,膏脂转运障碍,病由始生。临证应重视肝脾之调畅,配伍降浊、化浊之品,从而使升降相因,出入相济。对于土木关系失和,常用方剂如香砂六君子汤、越鞠丸、逍遥散等。香砂六君子汤可调理肝脾气化,化痰燥湿,在此基础上加入枳实、厚朴、陈皮疏理脾胃,佛手、香橼、柴胡等疏肝理气以醒脾运脾。诸药共奏益气健脾、化湿降浊之效,使得生理性膏脂得以输布,则病理性膏脂生化无源。视病情不同,可选用黄芪、白术、人参等健脾益气,川芎、香附、郁金等调达肝气,枳实消气滞,瓜蒌豁痰浊,薤白开胸气,山楂化膏浊,泽泻利湿浊等。诸药配伍,以达醒脾启枢、燥湿清热、化浊消脂之功,使痰浊膏脂得利。以此选方用药以调和土木,使肝脾恢复正常关系,调控膏脂正常化生与转运,使气血津液平和以防病。
3.2 化痰祛湿以清浊 国医大师邓铁涛认为“痰为瘀之初也”,“土壅木郁-膏脂转运障碍”状态下,膏脂积于脉络血管之中,生湿酿痰。痰湿关系密切,其质地重浊黏滞,易致脉中积滞凝结不畅,闭阻不通,因此治疗上常以化痰祛湿为法,方选瓜蒌薤白半夏汤、瓜蒌薤白桂枝汤、温胆汤、二陈汤等。此阶段患者体质偏于痰湿型,可加用茵陈、黄柏、薏苡仁、茯苓、泽泻、萆薢等健脾渗湿,化浊降脂。痰湿、膏浊皆为阴邪,若偏用苦寒之药,非但此邪不除,反易伤脾而助痰湿,遵仲景“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法,佐入温燥之药,如姜半夏、木香、桂枝、胆南星、白术等。若膏浊痰湿凝结,可选用石菖蒲、麝香、皂荚等增强祛痰之效。总的来说,在膏脂停运,酿生痰湿的病理内环境下,以化痰祛湿为法,化痰湿,泄浊邪,清膏浊,膏脂转运调和,则邪毒无所生。
3.3 化瘀解毒以通滞 朱丹溪言:“痰挟瘀血,遂成窠囊。”瘀为痰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痰瘀内郁生热成毒,瘀毒并见,致病广泛,病情复杂。膏浊致病,痰、瘀、毒三者互结,临床症见胸痛剧烈、持续不解,伴有汗出肢冷、手足青至节、舌绛紫、脉微欲绝等,甚则烦躁不安、意识不清,此乃瘀毒暴戾化火,耗气伤血。因此,予以化瘀解毒祛除有形实邪,防止瘀毒变化,改善膏脂转运的内环境,是治疗的关键。方选血府逐瘀汤,在活血化瘀的基础上佐以黄连、栀子、竹叶等清心解毒之品。同时考虑到患者病程日久,痰瘀胶结为干血,须重视虫类药物的运用[29]。虫类药物为血肉有情之品,形胜于气,走窜善行,无处不到,如水蛭、虻虫、土鳖虫、蜣螂等,均属祛瘀之峻剂,性猛而效甚,畅达脉中干血。用之需注意顾护正气,防止正气过伐。
4 验案举隅(赵明君主诊)
游某,男,76岁。2023年12月21日初诊。
主诉:发作性胸痛、胸闷、气短2年。患者2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呈发作性,每次持续几分钟,活动及劳累后加重,休息后可缓解,偶有咳嗽、咯白黏痰,痰较稠厚。近期患者上述症状反复发作,遂来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就诊。刻下:发作性胸痛、胸闷、气短,活动后加重,偶有咳嗽、咯白黏痰,食欲不振,寐差,舌质暗、苔白,脉弦滑。血脂检查提示:TG 1.84 mmol/L,LDL-C 3.66 mmol/L。冠状动脉造影提示:右冠优势型,左主干无狭窄,前降支无狭窄,前向血流TIMI3级;回旋支中段局限性狭窄90%,前向血流TIMI3级;右冠近端局限性狭窄50%,前向血流TIMI3级。西医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型心绞痛(心功能Ⅱ级);高脂血症。中医诊断:胸痹(痰浊内阻证)。治宜化痰祛湿。方选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减。处方:
瓜蒌15 g,姜半夏10 g,薤白10 g,丹参15 g,麸炒枳实30 g,炒桃仁15 g,三七粉3 g(冲服),陈皮15 g,莱菔子12 g,砂仁6 g(后下),郁金10 g,黄连3 g,炙甘草6 g。5剂。每日1剂,水煎分早晚温服。
2023年12月26日二诊:服药后患者胸闷痛、气短较前好转,未诉咳痰,食欲尚可,夜眠差,舌脉同前。予初诊方加太子参30 g、生黄芪30 g,7 剂。
2024年1月4日三诊:服药后患者病情稳定,胸痛、胸闷未再发作,余症均较前明显减轻,复查TG、LDL-C结果均处于正常范围,遂继续以二诊方为基础化裁,以巩固治疗。
按语:本案患者为老年男性,精气渐衰,营卫虚损,脏腑功能损伤,阴阳气血失衡,胸阳不振,痰浊内生,膏脂转运障碍,使心脉痹阻而致胸痹心痛。肝脾失调则水湿不化,胸阳不振,痰浊内生上犯心肺,故可见胸闷痛、气短、咳嗽、咯白黏痰;痰湿阻于中焦,故见食欲不振;阴阳失衡,阳不入阴,则夜眠差。治宜化痰祛湿。故以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减。方中瓜蒌、薤白、姜半夏行气解郁,通阳散结,祛痰宽胸;陈皮、砂仁皆入脾胃而行气调中,使湿去而脾运;郁金、麸炒枳实疏肝理气,活血止痛;莱菔子化痰消脂,助膏脂转运;丹参、三七活血祛瘀通络;炒桃仁活血通脉,使邪去不留瘀;少加黄连以苦降,泻心经之火解毒;炙甘草调和诸药。二诊时患者诸症明显减轻,考虑患者病程日久,正气虚损,加太子参、生黄芪以培补正气。三诊时患者病情稳定,诸症未再发作,以二诊方化裁继续巩固治疗。本案以化痰祛湿,兼调补正气为大法,以调肝脾、化膏浊、祛痰湿、行气血,使邪尽去,膏脂转运调和,并及时培补正气,正气充盛,邪气难以侵袭,则疾病无从发生。
5 结语
从土木关系的角度出发,基于“土壅木郁-膏脂转运障碍”探究可发现,CHD合并血脂异常以土壅木郁、膏脂失衡为始动因素,膏脂化浊、酿生痰湿为核心机制,痰瘀同源、毒瘀互结酿生病情之变。针对此病机,临证相应采用健脾疏肝以平和、化痰祛湿以清浊、化瘀解毒以通滞为治则,以调理肝脾治本,祛除痰浊瘀毒治标,从整体上辨证论治。在尽早、有效的干预治疗下,恢复土木关系,改善膏脂转运的内环境,重建膏脂化生和转运的动态平衡,不仅能及时干预本病病情的进展,也可改善患者预后,且不良反应少。目前研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中医药干预膏脂转运的分子机制尚需进一步借助现代技术阐明,合理配伍、量化药物比例需要高质量的循证医学依据等。今后需要深入整合中医治疗CHD合并血脂异常的优势,持续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充分发挥中医药辨治本病的独特优势,使更多的患者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