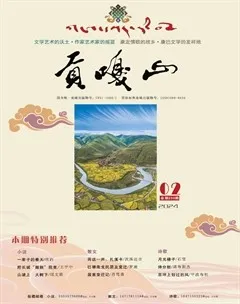月光梯子(组诗)
石莹
林深处
看不见的航线
把两个地址、姓氏连接起来。蜻蜓的翅膀
在树林里穿行。伐木工留下拆迁的证据
我们成为忐忑的伴侣
蛇在树洞里吐出信子
我们仿佛两只鸟儿,相互问候。在某个
城市、某棵树木
身上,重新遇见自己
颤动翅膀让生活不至于跌落大地,让诗歌
亲近于信仰
点燃松脂驱散内心的浓雾
我们日夜鸣唱,赞颂倒春寒来得
像一场春天的雪
我们尝试飞。采摘新鲜的苔藓覆盖夜空
我们共用同一个咖啡杯,用一个吻痕
覆盖另一个吻痕
我们关闭内心的防火门
你说,“有人正在演奏舒伯特,而对
那个人来说
此刻音符比任何事物都要真实”
凌霄与春天
二月的瞳孔冒出花蕾
我爱上这种纠缠
细微的蛩鸣挂在窗棂之上,仿佛蛇的呓语
“春天是适合思念的季节”,妈妈和燕子在房檐下
低声说话
虫子小声呐喊
仿佛语言不在纸上苏醒,它们就不罢休
当她下定决心出门的时候
炮仗在枝头上雀跃、炸裂
我的妈妈重新变回少女,迷恋刺绣、缝纫
编织藏满暗语的围巾
唯有春天不可辜负啊
清风泻入流水
苏醒的二月,把重新写出自己变得轻而易举
井
它比我有内涵。两块青石板掩护着它
日夜朝外掏泉水
也掏出大山和野棉花藏起的小秘密
乌鸫叼起的叶子
从凤尾竹高处落下来。在母亲的水瓢
溅起一个年轻妇人清晨的欢喜
现在是我。坐在井沿上,一遍遍听泉水
讲述曾经遇见少年
竹筒的水杯,盛满的爱恋
星星将水底的灯光点亮。路过的乌梢蛇游得这样慢
像梅花机械表的指针
我的老井,清澈的眼神被时间割伤
双手捧起的脸还是那个曾经的少年
我们说悄悄话。手心里的湖闪着波光
仿佛天上的眼睛
月光梯子
挤在窗口看天空,脸被挤成一张张
平面肖像画
从月光里逃出来的东北虎在村庄周围盘桓
它追逐汽车
却放逐它们。像我放飞的竹蜻蜓
现在它蹲在我的脚边
改头换面做一只名叫“阿呆”的棕色小猫
它舔舐爪子
如同回味野外狩猎的前世
我们坐在阳台上,听它讲述从前的故事
用我早已忘记的语言
而月光往前递出梯子
它走过来,触摸我的裙角
发出轻微咕噜声
又小心翼翼地收回去
现在,它拆解着线球。这个动作
已经重复了很多年
我拉上窗帘,从窗玻璃上取下粘贴的面具
外面下着雨
没有多年不遇的超级月亮
只有雨水不断地吐出一轮红月亮的血
我尚且还不知道它的性别
微茫
九月是属于告别的季节:树叶、掌心;或者
某个具有温度的背影
“我想要和你说对不起,却找不出
恰当的语气助词”
是的,遇见可以是石沉大海
也可以是词语在指缝里流失带着刺
“心情一直在落雨。”这是个俗气的表达
我没有伞
其实,也并不需要一把伞
一棵树
“我们将要同行一段路,然后分别很久”
枯萎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植物属性
比如我的父亲,住进了花岗岩的长方体
也不妨碍他
为我留下一把遮挡风雨的伞
他把我带到此处
然后消失,仿佛夏日里的霧
墓地上每一片花、叶上都能找到他的影子
但我无法完成一种收拢
或者挣脱
“往前走,去寻找想要遇见的溪流、彩虹
或者星星。我会留在这里
等待一只灰雀
衔来你的欢喜,或者忧伤”
这是一份契约——这里其实没有树
我们之中有一个人留在这里
生长出根系
水母
八月的海风是咸的。我们站在岛礁伸出的胳膊上
它一放下手掌,就可以亲吻海水
事实上,先来亲吻双脚的是肥皂泡般透明的生物
它们冲上礁石,搁浅在水洼里
仿佛我们刚用玻璃杯装满啤酒
泡泡飞扬跋扈地存在,像我张扬的马尾
肥皂泡终究也只是泡沫。每一个年少轻狂
都会熄灭
我们朝海中央扔出去的漂流瓶,至今还下落不明
脚印再也没有回到过那片海
只有透明的梦每年依旧涌上来,在石头上碎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