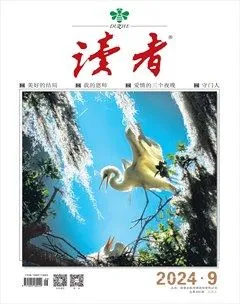绍兴会馆的中秋家宴
王珩

1912年5月5日,一个和煦的暮春天。外省海归青年周树人几经舟车劳顿,抵达北京,开启了他长达14年的“北漂”公务员生涯。
4个多月后,一夜,皓月当空,清辉入户,树影摇曳,楚楚可人。他比平日回来得晚,还喝了酒,有些醉醺醺的。这一天是他北上的第一个中秋节。初来乍到,人事风土尚未全然适应。归寓途中他举目望月,念及千里之外的母亲,客子的漂萍羁旅之感倍加强烈。
想家归想家,但他并不落寞,毕竟有两位好友陪着他过节。
他们是许寿昌和许寿裳。许寿昌是许寿裳的长兄,曾任财政部佥事、盐务署会办等职。4个多月前,风尘仆仆的周树人抵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许寿裳的陪同下,乘着月色前往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拜访许寿昌。二人初次晤面即有倾盖如故之感,以一册李慈铭的《越中先贤祠目》订交。次日上午,有赖许寿昌热心关照,周树人顺利入住藤花馆。后因闹邻扰眠,他避喧移入第二进一处有槐荫匝地之美的僻静独院——补树书屋。1917年春,周作人来京工作,他便把卧室让给二弟,自己搬入靠北一间采光很差的屋子。
至于许寿裳,与周树人关系更密。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窗,后来还成为同事。周树人称许寿裳为35年的挚友,许寿裳称周树人为平生诤友。他们相依相助、相互辉映、始终不渝的友情,堪称知识分子交谊的典范,许广平赞其“求之古人,亦不多遇”。说起来,到1912年,二人相交已10年了。1902年秋,他们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时相识。周树人在许寿裳的影响下,剪掉辫子,为杂志《浙江潮》撰稿。两个人还一同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他们志趣相投,立场相契,总是形影不离:昼则含英咀华切磋学问,夜则抵头促膝盱衡时事,就连吃面包的小细节都可见二人相交之莫逆。许寿裳很有些绅士做派,吃面包只吃中间的芯。周树人则比较平民化,觉得这样太浪费,便把许寿裳撕掉的面包皮捡起来塞进自己嘴里,并托词:“这个,我喜欢吃的。”许寿裳信以为真。此后凡是两个人一起吃面包,许寿裳总会先把皮小心翼翼地撕给同伴。
1909年回国后,许寿裳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紧接着,他就把周树人介绍到该校当教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请乡友许寿裳共襄盛举。而此时,周树人在老家被无爱的婚姻煎熬着。
他在致许寿裳的信中一再诉苦,称“越中棘地不可居”,望老友代为谋职,只要能离开绍兴,“虽远无害”。于是,许寿裳雪中送炭,郑重地向蔡元培推荐了他。蔡元培很给面子,痛快地答应了:“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
“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周树人总算得偿所愿,从绍兴憋闷的空气中解放出来,成为教育部部员,后随部北迁,与许寿裳一同赴京履职。两个人共事期间,乡谊日醇,私交弥笃。他们或偕游小市猎奇,或同逛琉璃厂淘书,邀酒聚餐频密,互赠美食不断,经济上常通有无,精神上砥砺深耕,还常往钱粮胡同探视被软禁的老师章太炎。
住在嘉荫堂的许寿昌和许寿裳是周树人寓居绍兴会馆七年半时间中,其日记里出现最多的名字。每逢端午、中秋、元旦、除夕等佳节,兄弟俩总会准备几道“肴质而旨”的可口家常菜,招呼他过去把盏共叙乡情。而他与许寿裳的“食鹜情缘”,尤值一提。
笔者据周树人的日记统计,从1913年11月到1918年1月许寿裳离京赴江西任前夕,周树人共接受挚友“投喂”成品熟食28次、鸭馔10次。这还不包括三天两头被邀至其寓所同餐,以及隔三岔五地收到火腿、鱼干、笋干、笋煮豆、辣椒酱等小食的情况。许寿裳似乎很爱烹食禽类,尤其是鸭。这种“食鹜情缘”一来可能与绍兴人喜好烹鸭的地方食俗有关,二来也说明周树人确对鸭肉青睐有加。每遇赠则喜悦之情油然而起,他必特书一笔,其余吃食便统以“肴”字概而括之。
周树人不厌其烦地记录着,我们兴味盎然地品读着。他那乍看似流水账的日记并无啰唆之嫌,反倒让人的心底腾起一股暖融融的感动。因为在这年年岁岁的重复动作中,饱含着老友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贴心关怀。众所周知,周树人是绍兴会馆斜对门那家宣南百年老店——广和居的资深“钉子户”,与朋侪聚饮笑乐于此的次数不可胜计。但毕竟不能天天下馆子,家的味道终归无可替代。“单身汉”的各项日常想必简省单调,吃饭更是含糊将就。许寿裳便时不时把自家烧好的饭菜端过来给他改善伙食,用一碗碗热腾腾的美味抚慰着老友那个思乡病屡屡发作的胃和那颗苦闷彷徨的心。
身为北洋政府的一介文官,周树人总得设法摆弄一两样“嗜好”,才能多少让当局放心。周树人昼则赴部上班,“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夜则蜗居补树书屋,沉浸在抄碑帖、读佛经、校坟典、阅拓本中,任由寂寞像绿萝一样疯长蔓延,连除夕之夜都“殊无换岁之感”。闲治朴学,勤辑古逸,本是他避人耳目的自保之举,竟无心插柳地做出不少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的拓荒性学术成就。依此路径发展下去,他那部关于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应会更早问世。但日后一个人的出现,使他改辙易途,暂且搁下学术研究,转向了小说创作的快车道。
1917年9月30日,又是一个中秋之夜,周树人“烹鹜沽酒作夕餐”。他的中秋家宴上来了一个怕狗的《新青年》杂志编辑。他们惬意地就着月色,吃着鸭子,喝着绍酒,聊着文学革命。
而40多天前,一个晴朗的夜晚,小院里那两棵浓荫如盖的老槐树见证了他们石破天惊的“铁屋对谈”。“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听罢此言,周树人的心弦轻颤了一下。“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槐叶沙沙作响的背景音把他的心潮映衬得有些澎湃。他没想到,这个手提大皮夹的胖子日后会经常深夜造访。尽管每次都被狗吠搞得心悸不止,这个编辑还是执着地登门约稿、催稿,直至他交出一篇用他擅长的日记体写的短篇白话小说。这个人就是钱玄同。
如果没有钱玄同的积极敦促,或许就没有《狂人日记》的横空出世。周树人还是那个以稽古为乐的公务员,静默地过着“槐蚕叶落残碑冷”的潜修生活。他“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的第一声呐喊,或要推迟多年才发出也未可知。
1918年5月15日之后,隐士周树人成为我们所熟知的斗士鲁迅。他走出“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的故纸堆,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
他笔挟风雷、尺水兴波,不克厥敌,战则不止。他用文字的利剑划破长夜寒春的月色,他小说中的月,亦不复往昔日记中皎然澄澈的唯美之态,而是射出一道道清寒凌厉的冷峻之光。
(两由之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家宴》一书,李 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