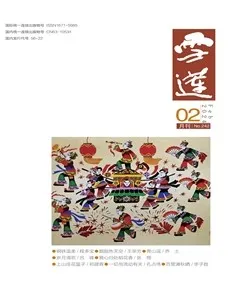远去的春节
【作者简介】 郁小尘,本名王书阳,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网络作家高研班学员。在《短篇小说》《奔流》《雪莲》等刊物发表小说和散文,曾获观音山游记征文奖、鲲鹏文学奖等奖项。著有散文集《时光谣》。现居深圳。
1
村头老槐树下,我和小珍、红玉一起跳房子,边跳边唱:“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稀稀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炕锅边;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灶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馍篓;三十,贴人儿;初一,供祭儿……”西边打麦场上,用土砌起的土堆上,十几个青壮年正在钉木桩,为唱年戏搭戏台,四周围满了人。
奶奶到村头喊我吃午饭,我抹下额头的汗飞奔回去。奶奶把盛满腊八粥的碗递给我,笑着说“快去! 先给椿树王吃!”我接过碗筷,双手捧着,小心翼翼走到椿树下,用筷子挑粥往椿树上撒,边撒边说:“椿树王,椿树王,我长高来你变长。我长高了穿衣裳,你长高了做嫁妆!”连说三遍。小珍站在旁边,满脸羡慕地看着我,“阳阳,你真行!不会说反!”
冬天的阳光洒满院落,奶奶站在阳光里,满脸都是笑容,她用无限慈爱的目光望着我,仿佛她的孙女一下子长高长大了。奶奶说,腊八节这一天,在椿树王跟前许愿是很灵验的,我的阳阳长大后,一定能长高个长成才的。不知何时起,家乡流传这么一个风俗习惯:孩子们要在腊八节这一天,用熬好的腊八粥,“喂”院里最高大的树王“吃”腊八粥,预示着孩子将来长得高大,能成才。
所幸我的嘴巴还巧,奶奶教的话,我学两遍便记住了。跟我同年同月生的小珍却老唱反。小珍端着腊八粥到自家的老槐树前,边撒粥边说:“槐树王,槐树王,你长高来我变长。你长高了穿衣裳,我长高了做嫁妆……”“叭”一声,小珍妈一巴掌呼过来,“死妮子,笨死你了!先说‘我,再说‘你!‘我长高来你变长。我长高了穿衣裳,你长高了做嫁妆!你咋老唱反呢?” 小珍流着泪接着唱:“槐树王,槐树王,我长高来你变长。我长高了做嫁妆,你长高了穿衣裳……”小珍拐不过弯来,总说错,小珍妈气得跳着脚骂她,“死妮子,长大也长不高了!”
腊八粥的配料要精挑细选,需选八种以上当年收获的农作物和蔬菜,如:大米、小米、红豆、绿豆、豇豆、花生、红枣、芝麻等五谷杂粮,再加上肉、红萝卜、白菜、粉条、海带、豆腐等蔬菜掺合在一起,熬上满满一大锅。腊八粥中午一餐是吃不完的,晚上热了再接着吃,有时能吃上三五天,象征着来年五谷丰收、年年有余。
2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传说中这一天是灶王爷的生日,家家户户要炕“火烧馍”祭灶,俗称炕锅边。奶奶说,灶王爷吃了“火烧馍”,来年咱家就有馍馍吃。
奶奶对过小年分外重视,她在前一天晚上扭着小脚开始在灶前忙碌。火烧馍的做法极为讲究:把发好的面和好,擀成片儿,撒上油盐葱花,卷成卷儿,切成均匀的小面团。再把小面团压扁,用面杖擀成烧饼模样,先在锅内用油正反两边焦黄,放进锅内蒸十分钟。出锅时,那诱人的香味儿扑面而来。母亲和奶奶在灶房里忙碌,母亲负责擀面,炕火烧馍,奶奶烧火。烧火要适中,不能大,也不能小了。火大了,火烧馍容易烧焦烧糊,影响外观与味道;火小了,火候不到,炕出来的火烧馍不香不焦,味道不鲜美。奶奶烧火时,火候掌握得极好,出锅的火烧馍,通常是色香味俱全。
二十四这天扫房子。母亲用一根长竹竿绑着扫把,打扫屋内外的各个角落。那时,村里的房子多为瓦房,屋顶的灰尘日久聚积,便成了一道道蜘蛛网。扫完了顶子,擦拭完门窗和家具,挂上新窗帘,铺好新床单,屋内屋外整洁敞亮。
将近晌午,父亲赶集办年货回来,我和弟弟围了上来。父亲像个魔术师,从袋子里掏出一件又一件的年货:鞭炮、红纸、五香瓜子、糖果、海带、香菇、鱼、粉条等。年货刚归位,母亲便在厨房喊吃饭了。
二十五是磨豆腐的日子,父亲担着泡好的黄豆,到后院的英嫂家排队磨豆腐。豆腐物美价廉,在那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是农村人最常见的招待客人的上桌菜。自家制作的豆腐滑润、细腻、营养丰富、经济实惠,绝对是纯天然食品。豆腐的做法有多种:红烧豆腐、家常豆腐、麻辣豆腐、油炸豆腐、清蒸豆腐等,母親总能把平常的豆腐,做成一道道风味不同的美味佳肴。每年腊月,英嫂家的豆腐坊从早到晚,排满了等待磨豆腐的人。那头蒙了眼睛的小毛驴,拉着石磨,一圈一圈,不知疲倦地转着,白花花的豆浆,便从石磨里滚滚流下。
“喝豆腐脑哟!”俊俏的英嫂在豆腐坊里一声呼喊,我和伙伴们便端着茶缸飞跑进来。英嫂挽起袖子,从热气腾腾的锅里给我们舀豆腐脑儿,诱人的豆香味儿弥漫在空气里。
二十六这天杀年猪。三娘家的院子里早已围了一大群人。我跟着母亲到她家时,猪已被赶出了栏圈。众人都夸猪膘肥体壮,身条长,卸下来的礼条一定好看。玉东哥拿着“双龙”牌子的过滤嘴香烟撒向人群。三娘在院子里新搭的土灶前烧火,母亲走过去接替了她烧火的工作。三娘过来摸摸我的头,笑着嘱咐我:“丫头,晌午在三娘家喝骨头汤。”
等我们跳完房子,人们已在分礼条。“石头家,五斤二两;三拐子,六斤八两;猴子家,八斤九两……”胡老二油腻的手在过称,玉东哥在本子上记下赊账人家的姓名。母亲挑选了五个礼条,笑着对三娘说:“走亲戚就要这种礼条,既好看又拿得出手!”陆陆续续的,人们拎着三五个或大或小的礼条乐呵呵地回家。院子里的大锅“咕嘟咕嘟”地熬煮着骨头汤,那诱人的香味,飘荡在村庄的上空,浓浓的年味在村庄氤氲开来。
二十七,杀灶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馍篓。母亲在这三天最为忙碌,她在厨房里忙着杀鸡宰鸭,炸鱼炖肉,一锅一锅蒸馒头,有红枣包、绿豆包、菜包、糖包等,预备过年的食物。
3
年货置办得差不多了,二十九这天,父亲几乎足不出户,在家忙着写对联。邻居家早几天拿来了红纸,让父亲帮着写春联。那个年代,村里家家户户门上贴的对联,差不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父亲写春联时,从不看对联书。那些对联,早已记在他的脑海里,融入到他的心里。毛笔在父亲的手里来回游走,龙飞凤舞的字体便出来了。父亲自己也编春联,他编的春联,上下联平仄相调,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乡邻间的相互帮助,一根烟、一壶酒、一杯茶,有的只是一句感谢的话,足让父亲心满意足。他一年又一年乐此不疲地为村里人写春联,在人们的赞美与感谢声中,收获劳动的喜悦。
年三十晚上,本家本族的人聚在一起熬年守岁。大人们谈古论今,孩子们聚在一起凑热闹。零点将近,爆竹声此起彼落,村里渐渐热闹起来。“拣炮喽!”一声呼喊,引来一群伙伴,孩子们拎着早已备好的红灯笼,飞出家门。红灯笼越聚越多,开始时几盏、十几盏、几十盏,到后来村头巷尾到处都是奔跑着的红灯笼。东家的鞭炮响了,“红灯笼”跑到东家去,西家的爆炸响了,“红灯笼”便跑西家去,“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是我们童年守岁的真实写照。三十熬年守岁的风俗,在我的家乡延续至今,“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之夜,在这个合家欢乐、全民欢庆的夜晚,是多么美好与让人难忘。
大年初一这一天,大人小孩都穿新衣、戴新帽,吃了早饭,孩子们跟在父母亲的后面,挨家挨户地去给长辈家拜年。奶奶说,她小的时候拜年,长辈端坐于堂屋里,面前放着两个草垫子,晚辈要跪在草垫子上给长辈们磕头。如今,磕头的礼数早已免了,晚辈们口口声声叫着“过年好啊!给您老磕头了!”却迟迟没有要跪下的意思。长辈们呢,也只是哈哈地笑着,也不去较真。不磕头,压岁钱还是少不了的,得了压岁钱的孩子们欢天喜地,到外面玩游戏。
拜了年,各族家相约去上坟祭祖。在故乡,这是一项盛大的民俗活动。人们用烧香、上供、叩拜、烧纸等形式,来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外地工作的人员要在这一天携家带口回老家祭祖。人们相信,祭祖是一件至关家族兴旺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各族家都十分重视,也办得非常隆重。祭祖回来,主妇们备好了年饭,七盘八碗摆满桌子,各族家围在一起,吃得热热闹闹,聊得开开心心,共同举杯,祝愿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
4
正月初二是去外婆家拜年的日子,母亲通常会在前一天把礼物备好,一个猪肉礼条、一份粉条、两包糖果、两纸包白砂糖,吃过早饭,带着我和弟弟去外婆家拜年。
那时,村子里都没有自行车,人们走亲访友,再远的路程都是要步行的。好在我们村和外婆的村子相隔不远,中间隔一条河。冬季,河里结着厚厚的冰凌,河面上横着一座小木桥。人踩在上面,晃晃悠悠,吱吱呀呀地响。过了小桥,再走上二三里地的路,便到了外婆家。
初二这一天,外婆家的亲戚有很多:在县城工作的大姨一家;外婆的娘家侄女平平姨和青青姨;外公最得意的学生剑民,以及外公的挚友郭医生。
姨夫骑着自行车,带着大姨和表姐来了,他们是城里的工人,他们的自行车,在当时的农村,十分新奇。平平姨和青青姨也来了,她们是外婆的娘家侄女。平平姨长相有点像外国人,像电影明星一样漂亮,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悦耳动听。我总是拿着故事书,缠着平平姨读故事给我听。相比姐姐,青青姨则十分普通,她的长相和言行,无法与平平姨相比。常听外婆叹着气说:姐妹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真不像一个娘生的!
剑民是外公的学生,在县检察院做文书,戴眼镜,举止儒雅。他跟外公在一起,总有讲不完的话。郭医生往往是最后一个到的。郭医生50多岁,身材瘦而高,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郭医生的自行车刚推进院子,外公便迎了出来。郭医生抱拳道:去东营看了一位病人,来晚了!失礼,失礼!外公抱拳回道:客气!客气!请进,快请进!
客人到齐了,饭菜也准备好了,黄酒和白酒摆上了桌子,外婆家的亲戚们相聚在一起,谈笑风生,举杯畅饮。
后来家里有了自行车,再去外婆家拜年,父母便用自行车带上我和弟弟。大姨因为工作忙,便让大表哥来拜年。大表哥骑着摩托车,戴着墨镜,威风凛凛地呼啸而来,后面带一个穿裙子烫卷发的时髦漂亮女孩。大表哥搂着女孩向外婆介绍:“外婆,我的女朋友——于真真!”于真真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亲亲热热地叫声“外婆!”外婆喜得眉开眼笑,撩起衣服掏红包。
那年,平平姨考了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在外婆家看到她时越发漂亮。没有看到青青姨,母亲说,青青出嫁了,嫁了邻村一个会木匠手艺的年轻人。那年,也没有见到剑民,外公说他调回郑州了,三月份出差回南阳再来看他。
后来再去外婆家,见到了大表哥和新婚的表嫂,看时,却不是于真真。大表哥搂着女孩,大大咧咧地向我介绍:“你表嫂——苏佳佳!”见我疑惑的样子,大表哥笑着说:前年那个叫真真的表嫂呢,是假的;今年这个叫佳佳的表嫂,是真的!佳佳表嫂笑着,满院子追赶大表哥,拿拳头捶他。
5
正月初三,年戏便开始了,连续唱三天,一直唱到初五结束。
村里的二拐在这几天特别兴奋,他带领村里的半大小子,一瘸一拐挨家挨户收唱年戏的钱。二拐自小爱看戏。豫剧、曲剧,越调,只要听过一遍,他都能唱得有腔有调。回娘家的姑娘们,东家10元,西家20元,唱年戏的钱一下就凑齐了。掏了年戏钱的姑爷们,村里人以姓氏加“相公”称呼他们,姓李的是李相公,姓范的便是范相公,在村子很是体面。
戏台设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用几根粗大的柱子支起,上面用红红绿绿的布搭成戏棚,四周挂上十几盏马灯,外面用红纸糊成灯笼状,这样看来外表美观,而且晚上看戏时能收到很好的舞台效果。一帘红布把戏台隔为台前幕后,边侧是孩子们的天下,他们所处的位置既可欣赏前台的节目,又可看到演员在后台化妆的情景。年戏分为“正戏”和“找戏”两种,“正戏”是全场戏,时间长,故事情节有始有终;“找戏”则是在“正戏”结束后,剧团演上一段嬉笑打闹的戏,这类戏出场的一般都是些丑角,他们丑陋的扮相,夸张的表演,让观众笑破肚皮。年戏在开戏前要打20分钟的锣鼓,俗称“打闹台”,一是催促未到场的人,要开戏了;二是传说可以消灾避邪。村里的戏迷们则趁此机会过把戏瘾:他们化了妆,换上戏服,登台有板有眼仿一段名家名唱。随着闹台响起,观众也差不多到齐,负责道具的人员换上场景和道具,年戏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正式开场。
姑娘们出了唱年戏的钱,便有点播剧目的权力。于是,上演的戏曲是五花八门,新老剧目都有。有为父母亲的生日点播《五女拜寿》的;有为祖母的寿辰点播《五世请缨》的;有为哥嫂的结婚纪念日点播《西厢记》的;有为待嫁的小妹点播《抬花轿》的。一场《七品芝麻官》让众人捧腹大笑,一场《玉堂春》使戏迷们流泪不止。今天这家的老姑为闹矛盾的侄儿、侄媳点播上一段《打金枝》里面的“唐王劝女”,明天那家的大姐为说服封建的父母反对小妹的婚事点播一段《拷红》里面的“红娘跪劝老夫人”,那个人称“赛香玉”的女演员惟妙惟肖的表演,听得固执的“老夫人”心服口服,最终促成了一对有情人。今天的《穆桂英挂帅》刚卸下战袍,明天的《花木兰》又披上戎装替父从军……
俗话说,“识戏的看门道,不识戏的凑热闹”,此话一点也不假。识戏的和不识戏的,你只要往戏场上一站就一目了然。那些在前排正襟危坐的一定是铁杆戏迷,他們是忠实的观众,每天早早来到戏场,从头看到尾,从演员的服装到台上的道具,从人物的造型到演员的唱腔,演员的一举一动甚至每一个表情,他们都不轻易放过。他们完全生活在戏中,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恼忧愁,随着剧情的发展时喜时悲、时哭时笑,宛如痴人。那些吃着瓜子凑在一起聊天的多半是些年轻的媳妇,她们的话题往往是谈论东家的婆媳吵架,西家的夫妻拌嘴之类的琐事。当然,她们也有感兴趣的戏曲,什么“莺莺会张生”,“白蛇与许仙”之类的爱情剧目。村里出嫁的姑娘们回到自小长大的村子,儿时的伙伴,久违的亲人,多年未见面的朋友,终于聚在一起,兴奋的心情无与伦比。她们三人一群、二人一伙地坐在一起,边欣赏戏曲边亲切地交谈。谈儿时的趣事,谈成家后生活的甜酸苦辣……那些站在戏场后面,多半是村子里没成家的年轻后生。他们一会喝冷饮,一会儿吃西瓜。心情不全在戏台上,目光多半是追寻着邻村年轻漂亮的姑娘。看到中意的,便会请来媒人,备上礼物,到女方家求婚。那些年,村上的年戏,不知让多少有情小儿女结成眷属。年戏在零点之后全戏进入了高潮,戏场外也是一番忙碌的情形:王家的大伯升起了火堆,李家的大娘带来炒焦了的花生,招呼众人来品尝,纯朴的民情尽现眼前。一直到凌晨两点钟,伴随着台上丑角令人捧腹的搞笑表演,众人才呼朋引伴,在欢声笑语中一一道别……
“三天戏,五天年,哧啦哧啦就过完。”过了正月初五,唱罢年戏,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立春了,农人在地里忙碌,新的一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