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春风化雨情
杜少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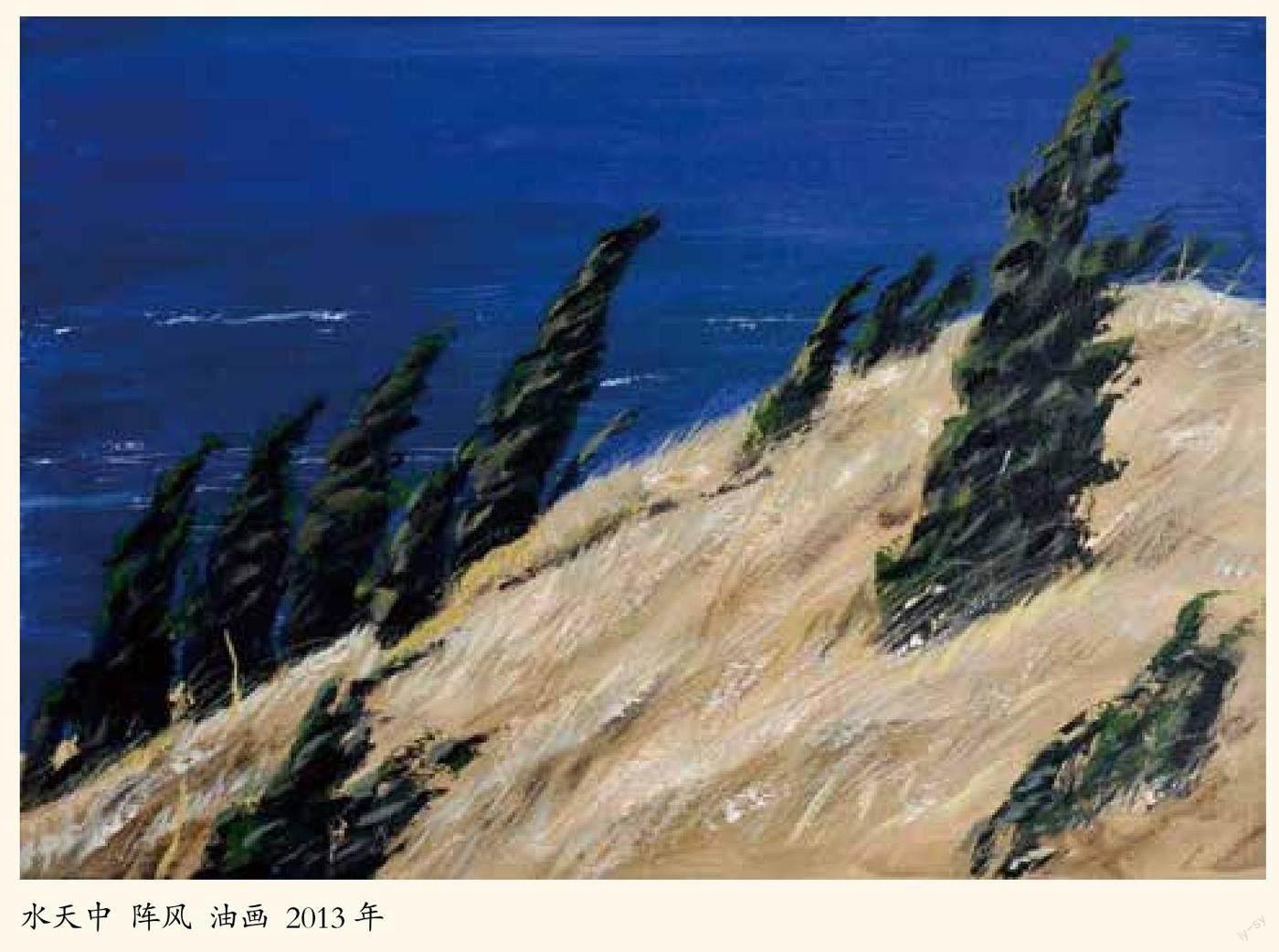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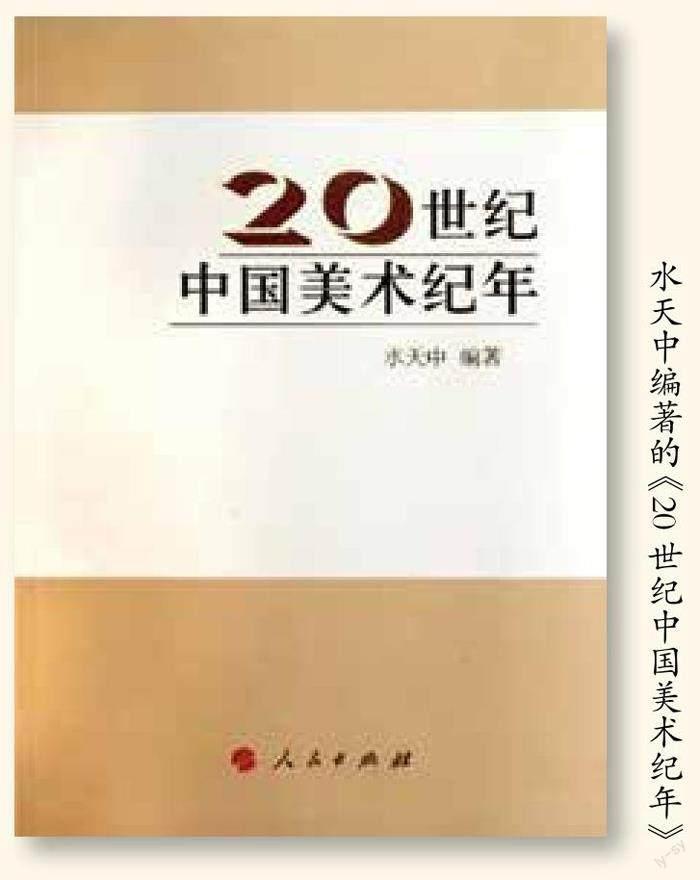
最早知道水天中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术书刊和报纸上。当时署名水天中的系列文章曾一度引起我的注意,其文“跌宕昭彰,朴实纯真”,读之亲切有味。适逢“85新潮”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创办的《中国美术报》影响很大,自然成为年轻人爱不释手的读物。大概是1987年后,水天中出任该报主编,以后的每期报纸上便都有他的名字。其时思想解放的大气候已经形成,文学艺术界也开始焕发青春,诸如哲学界的“美学热”、文学界的“历史反思”、美术界的“现代新潮”等思潮连绵起伏、千姿百态,“犹如思想的闪电”瞬间划过这片土地的上空。
2006年的春季,我荣幸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并得以忝列水天中门墙。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和水天中先生见面时的情景:水先生早早地在客厅等候,我到他家的时候门早已打开,是虚掩着的。他面容清癯,举止儒雅,性情温和。他坦言,“理论家是一个高危职业,更少利益可言,你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我微笑着告诉他:“选择学习美术理论,是因为兴趣,从未考虑过个人利益。”我们由此打开了话匣子,相谈甚欢。水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此后每遇困惑,我便登门求教,水先生不仅面传心授,而且经常通过邮箱传递文字,亲自改稿,十分谨严。每当我看到文稿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常常头上冒汗,自惭形秽,体会到文字之艰深。水天中对新事物的接受很快,他不仅习惯使用电脑,而且很细致地在我们往来的电子信件中纠正我的粗心和疏漏。记得有一次,我从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有关历史的普及读物,水先生立即指出其中错误,令我汗颜。由此感慨,诚如《隨园诗话》所言:“诗虽奇伟,而不能揉磨入细……诗虽幽俊,而不能展拓开张,终窘边幅。”尝闻细节决定成败,金针可以刺绣,对于文字的态度更应该慎之又慎。
水天中在美术圈有着极好的口碑,凡接触过他的,皆有赞誉之词。他既有温和儒雅、豁达大度的人格魅力,又同时具有坚持己见、不畏强权的文人风骨。王璜生这样描述水天中:“有学者风范、文人风骨、君子风度”,此语很是恰当。水天中与我的交往十分平等,尤其给学生以充分的尊重,指出问题时十分温和,寥寥数语,让人如梦方醒。每与水天中交谈,我都会有“如沐春风”之感。水先生对于晚辈后生,皆以全力相扶持,所承诺之事,无一不落实,且往往能以己度人,始终替别人着想,其“耿直”的个性,令人难以忘怀。
如果说他优良的品德来自于性格和教养,那么,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对学术立场的“坚守”,应该源出艰苦生活的磨砺。他不完全是“思辨型”的理论家,他的同学顾森曾在一篇题为《老水这个人》的文章中谈道:“随和与固执是老水这个人性情的两面”,他的行为让许多深谙人情世故的人无法理解。也正因为这个“固执”,使他赢得了尊敬。
水先生对我的培养并不局限于书本之上,而是更注重读书思考和学术实践,更注重独立思想的精神价值。2007年春,水先生推荐我赴广州参加广东美术馆举办的“浮游的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了参会论文,会议期间,我亦有幸参加了日本学者鹤田武良的“图书捐赠”仪式。鹤田武良是国际上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重要学者和理论家,也正是参加这个捐赠仪式,给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和启发。我又两次从北京到广州翻阅“鹤田武良捐赠”的书籍资料,历经月余,收获甚丰。
2007年冬季,我跟随水先生到北戴河参加中国油画学会主办的“中国油画的现代性学术研讨会”,并且参与一些辅助性工作。尔后受《美术观察》杂志社委托,回京后由我执笔撰写综述,发表在2007年12月的《美术观察》刊物上。当然,我的收获远远不止这些,受到水天中鼓励,我又大胆地拟定了一个有关“中国油画与后现代主义”的论文题目,这篇文章我在2009年2月份向中国美术家协会投稿,并惊喜地接到了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当代美术创作论坛”的邀请函。当时担任第三场发言的评议人,是水天中和梁江,我与导师在中国美术馆七楼学术报告厅不期而遇,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水先生对我的雕琢是在“润物细无声”中进行的,言传身教,没有一点“刻意”的痕迹。对于薪火传续问题,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水先生十分看重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回应”和“个人体验”,我在学术方面些许的进步,与水先生对我的悉心载培有着很大关系。跟随水先生读书期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为快乐的时光,这个时期,也是我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和参加学术活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当时的《文艺研究》《美术观察》《美术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美术馆》《吉林艺术学院学报》等多种刊物上,以及出版的各种美术文集中,偶有我撰写的文章。然而对我而言,这些通过勤奋努力获得的显而易见的成就并不十分重要,甚至是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我从前辈学者身上学到了处世的态度、待人接物的方式、对待学生的仁厚与宽容,以及对待学术的敬畏之心……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