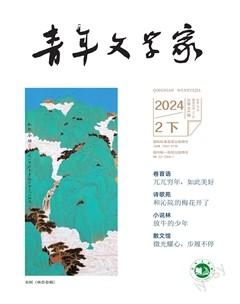伊格尔顿《文学事件》中“非纯粹性”价值的探索与掘进
杨钧雁

2017年,伊格尔顿所著的《文学事件》被引入中国后,引起了理论界的一定关注,但研究成果颇微,在批评对象的广度与深度上尚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指出文学活动由作品、世界、作家、读者四者共同构成,此“四要素说”范式仍对现阶段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目前,以《文学事件》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论文在研究成果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对比《文学理论导论》研究伊格尔顿的文学本质观流变,研究文学语言的虚构层面,研究读者的阅读策略,即作者、文本、读者三方面。换言之,在对《文学事件》的当前研究中缺乏对“四要素说”范式中“世界”要素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将从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核心观点“策略说”入手,以缺失的“世界”要素为联结点梳理《文学事件》的核心观点,并进一步探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不同程度建构“纯粹性”思想的背景下,《文学事件》超越二元论的“非纯粹性”立场。本文意聚焦于文学事件研究的核心范畴“独异性”,演示在“无利害审美”与“意识形态产物”的虚假两难处境中,《文学事件》对处理审美的形式与内容、文本与世界等问题的独特价值。
一、《文学事件》“策略说”梳理
(一)处理作者与世界关系的策略
“文学作品的悖论之一在于,在不可改变性与自我完成方面,它是‘结构,然而它必须在永恒运动中进行自我完成,并且只能在阅读行动中实现自己,就此而言它又是‘事件。”(伊格尔顿《文学事件》)
伊格尔顿认为的“策略”是文学成为“事件”的关键,即作者突破固有模式的结构化过程,以文学带有“自我指涉性”的特有方式对内容进行编排。在传统文学与现实二元论成为探讨文学问题的无意识前提的环境中,“策略”理论的颠覆性意义得以凸显。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影响形成了强调“文学是现实反映”的传统二元论,这样一个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天然逻辑起点易导致创作无法脱离现实逻辑,研究无法脱离现实可见性等问题。伊格尔顿则用“文学性”巧妙离开二元论场域,规避了此类局限性。伊格尔顿借用了詹姆逊的“潜文本”概念,打破了文学与现实的简单对应关系而代之以复杂的态度處理文学的自我建构。也就是说,文学“不再被视为外部历史的反映,而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劳作……由此挫败了一切内部与外部二元论的僵化认知”(伊格尔顿《文学事件》)。在此意义上讲,“策略说”中的世界之于作者,既是文学产生的因素,更是文学解构的对象。相比于说作者忠诚于世界创作文本,更契合“策略说”的应为作者忠诚于文本中编织的语境世界,现实的外部世界不过是文本形式的指涉对象。
(二)处理文本与世界关系的策略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具有人类按照自我意义编织和重组现实的意义建构价值,获得了独立于物理世界律令外的自我指涉性。而文本策略的关键在于形式对内容的编排,如何在稳定文本自我指涉性的结构的同时,实现对动态问题语境的回应,或者说如何在文本不可分解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寻求和解与平衡。比如,伊格尔顿在书中以《失乐园》中审美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表达出作者人文立场的暧昧为例,说明“和许多文学文本一样,《失乐园》抛出它试图解决的种种问题,有时候在此过程当中还会创造出更多的问题”(伊格尔顿《文学事件》),即文本的复杂性不在于物理世界而在于形式与内容的持续性互动。
在处理文本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伊格尔顿否定了只偏重结构外壳的“绝对形式主义”静止文本观,也对巴迪欧、戴维森等已有的“事件”哲学颇有隔膜。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自我指涉性的完成不是单纯的语言学问题,他赞同费什“文本的特性是人们以某种方式给予关注的产物”(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观点,以“基于依据目标功能实时进行自我统合”阐述自我指涉性。依靠于形式与内容动态化的统一整合,伊格尔顿的文本具有了转换为事件的生成性与开放性,文本策略的世界观在文本实践中得到表征。
(三)处理读者与世界关系的策略
文本无论是作为具有开放性与生成性的结构化过程,还是对其包含语境的想象性回应,都具有读者介入的必要性。伊格尔顿借用伊瑟尔的观点阐述阅读策略:“我们在阅读时或多或少会在建立幻象和打破幻想之间来回摆动。在试错的过程当中,我们对文本提供的资料加以组织或重组。”(伊格尔顿《文学事件》)
这里强调了读者的阅读不是对静态结构的介入与解读,而是“积极介入一组策略以便解读另一组策略”(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动态化过程。文本在其构造的开放性语境中抛出假设并给出想象性回应的过程是作者“策略”性的书写,读者的阅读一方面是以自身策略多元解读作者策略以实现文本的结构化过程,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作者与世界关系对读者与世界关系的生成性影响。生成性影响促使文学完成“事件”意义,也在动态化互动中为读者呈现物理世界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意义在于呈现而不在解决。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不会就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教科书式的解决方案”(伊格尔顿《文学事件》),也没有必要过度强调目标导向,文学存在于逃离标准范式的颠覆与沉默之间,从这一点来说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就不能仅以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说法囊括。
文学的独特价值在于非确定、非唯一的生成性,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需抽象地剥离世界与文本的实用化联系,“策略”在作者、文本、读者与世界之间谋求到了一个可靠的关联点。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学作品反映了词语和现实之间的乌托邦式的统一。”脱离现实追求单纯的审美意义只会使文本成为孤立的纯粹性存在,形式与意义的共生使文学之为文学。
二、文学的“独异性”与“非纯粹性”问题
(一)文学事件的“独异性”
将文学视为“事件”并非伊格尔顿所首创,最早的学理出处也在《文学事件》的注释中有所提及:
将文学视为事件,参见Derek Attridge,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2004),pp.58—62.
伊格尔顿同时期的德里克·阿特里奇在《文学的独特性》中对文学事件作出了正面论述,其论述从语言层面开始将核心聚焦于文学事件的“独异性”。阿特里奇所说的作为事件的语言,首先指的是语言对规范的偏离与革新,这类似于什克罗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通过对传统规则的挑战和重铸来挖掘语言的分歧与张力。这实质上是阿特里奇对“文学工具性”的反思,但阿特里奇没有止步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并非每一次需要对原有规范进行重塑的语言革新就是文学创新……只有当这种重塑事件被读者作为一个事件而体验,并且这个事件开启了意义和情感的新可能性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开启具有事件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释文学。”也就是说,并非每一次“语言的偏离”都是一次语言的革新,只有当它促使文学本体成为潜在的可读对象,并开启读者新的情感与意义可能性的时候,才可以被认为是一次“作为事件的语言”的完成。阿特里奇从动态生成性的语言出发,将其构建的文学同样置于不稳定、开放性的事件过程中,提出了独异性的创新概念,“并不产生于不可还原的物质性核心,或者我们使用的文化框架不能渗入的纯粹偶然性之脉,而是产生于一般特性的排列,在构造一个实体时那些特性会超越由一种文化规范所预先编制的可能性”(阿特里奇《文学的独特性》)。这段文字很明显地区分了独异性与特殊性、偶然性等概念的不同,受到独异性构词的影响,其含义常被人所误解。
语言实践中的独异性问题是引发阿特里奇思考的起点,他试图通过分析文学文本与其他类型文本内在语言机制的运作差异,寻求文学语言的独异性,但在诸种尝试中表明此类从创作者视角切入文学事件研究独异性的方式并不可取,也就是说文学事件独异性的完成主体实然是读者。文学不同于静态的文本,其独异性体现在差异的生成,使阅读成为动态的、开放的“事件”。阅读是“事件”而非对象的标志就在于“体验”,当读者谈及文学作品时所论述的不是统一标准的百科全书式范式,而是涉及私人化情感体验的阅读感受和回忆想象。
除了上述动态的生成性外,独异性作为“对规范与习惯的一种调整过程”,也有区别于唯一性、相异性、偶然性的特殊意義。首先,独异性不是一种性质,而是一个事件,它作为特殊的文化事件在调整规范的过程中连接过去与现在。其次,独异性的要义在于创造与生成的过程,而非寻求相异性的结果以得到不可复制的优越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独异性的本质是非纯粹的,这准确地击中了现代思想转型的要义。下面本文将单独围绕“非纯粹性”的内涵与价值进行探索与补充。
(二)“非纯粹性”问题
针对独异性的要义“非纯粹性”,阿特里奇有这样一段论述:“它本质上不纯洁,总是容易受到污染、嫁接、事故化、重新解释与再文本化。它也不是无与伦比的;相反,它是显著地可加模仿的,并可能引发大量模仿。”(阿特里奇《文学的独特性》)
阿特里奇对“非纯粹性”的关注集中在论述独异性区别于唯一性具有可复制性与再文本化,即事件与重复的关系。但“纯粹性”的内涵在发展中得到不断扩充与丰富,与之相对“非纯粹性”的研究也不应局限于对独异性与唯一性的区分,而应探索其在文学事件及思考文学与“世界”关系领域,更具现代意义的独特价值。
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追求消除束缚与对立的绝对自由,诗化情感下,对陌生化表达的追求与天然情感的释放,使文学创作与研究指向“纯粹化”的终极导向。浪漫主义早期主张“纯粹性”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完美乌托邦,至本雅明将“纯粹性”推至形式层面对纯粹语言的追求。19世纪中期康德与席勒艺术的纯粹性思想发展,在法国出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纯粹性”概念得到基本的确认与发展。20世纪后,后印象派、达达主义等带有解构性质的现代艺术流派,急于在对传统艺术的反叛中寻找艺术的纯粹真实,“纯粹性”含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康德的无功利思想作为基本要义从未得到颠覆。海德格尔阐述的纯粹“上手”状态、“此在”本真状态等均建立在康德的无功利思想基础上,康德也被公认为虽未直接谈及纯粹性,却为纯粹性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思想根据。康德提出“合目的而无目的”说,其纯粹性思想是建立在理性主体的认识能力之上“对理性的纯粹性使用”。
海德格尔虽支持纯粹性以无功利思想为基础,但他并不认同无功利等同于纯粹性。尼采提出对康德意义上的纯粹性的批判,他认为康德用无功利概念将艺术导向无生命的世界,而真正的艺术不应是无功利的。俄国形式主义过分强调文学内部与外在形式的二元对立,易出现局限性强的狭义文学创作与研究,悬置隔离文学与“世界”联系的政治价值和伦理意义。常有研究者对《文学事件》将“策略”与政治意识形态捆绑的论述进行批判,但意识形态本身是组成历史真实不可剥离的部分,创作与阅读作为不掺杂利害的审美过程无法割裂对潜文本的生产与接受。
但也需承认的是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坚持存在片面之处。伊格尔顿指出艺术可以在形式方面自由延展,但在框架中需完全隶属于意识形态。文学创作与批判如果完全倾向对无利害的形式美追求,会将抽象审美悬置于内容之上,朴素意义的泯灭是文学大众趣味的权利性剥夺,文学大众化的审美意义在对审美意义的“纯粹化”追求中反被压制。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试图回拨,对形式主义缺失的政治和伦理维度进行了一定补充。
综合来讲,《文学事件》虽在一定程度上受伊格尔顿长期坚持的政治批评立场影响,在部分观点上展现出政治主导色彩,但是瑕不掩瑜。文学事件的独异性对康德在理性认知上的“纯粹性”观点具有突破性意义,在超越二元论的“非纯粹性”立场上融合包容。它揭露了在被提纯和美化的表象背后更为复杂的“世界”,在美的概念意义中寻找到了丑的价值。“策略”理论的提出以开放性的姿态展现世界远超乎想象的未知性和严峻性,为审视文学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特视野和现代思考价值。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