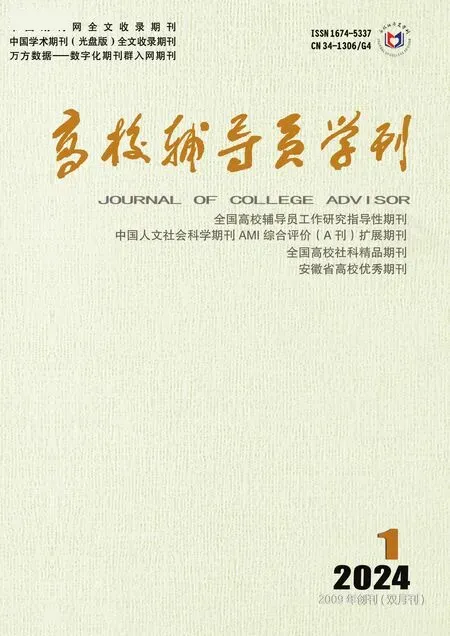青年“emo时听红歌”:现象、本质与启示
闫 旭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随着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emo”已成为当代青年表达“伤心、难过、抑郁、丧”等多种负面情绪的网络流行语言,并于2021年12月30日入选《中国新闻周刊》“年度十大热词”。在“emo”流行于网络空间的同时,“拒绝emo”也逐渐成为当代青年情绪自我疗愈的网络文化新趋势,其中“emo时听红歌”便是较为值得关注的网络文化现象之一。截至2023年10月18日,以“红歌 emo”为搜索关键词,网易云音乐平台中的相关歌单达285个且其最高收听次数达79.3万,小红书平台中相关的笔记共345个且累计获赞33.59万,B站中有关视频30个左右且其最高播放量达211.6万,微博平台中相关话题的最高阅读量达274.4万,抖音平台中相关话题的视频最高播放量达530.7万、单个视频最高点赞量达66.1万,微信订阅号中有关的文章最高阅读量达4.4万。
作为红色文化精神的载体,红歌与“emo”在网络流行文化中的组合搭配令人耳目一新,在网络圈群的视角下“出圈”感十足。本文将从网络圈群和音乐疗愈的角度来探究“emo时听红歌”现象在青年群体中产生及流行的原因,以求为青年的培养工作提供有益探索和经验。
一、“emo时听红歌”现象的传播特征
(一)多平台交叉的传播轨迹
网易云音乐平台中,有关“emo时听红歌”的最早歌单为2021年9月2日由用户“不知秋Q”所创建的“当我emo的时候我听点红歌”;微博平台中,最早使用有关“emo时听红歌”的话题标签的微博由用户“131416光芒”于2023年5月29日发表;小红书平台中,最早使用有关“emo时听红歌”的话题标签的笔记由用户“影娱大咖”于2023年5月31日发表;B站中,最早有关“emo时听红歌”的视频作品由用户“资深观众刘根红”同样于2023年5月31日发表;抖音平台中,最早使用有关“emo时听红歌”的话题标签的视频由用户“功不唐捐”于2023年6月1日发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最早出现的有关“emo时听红歌”话题的文章由用户“笑嘻了”于2023年6月2日发表。
根据时间线可知,“emo时听红歌”现象在各个网络平台出现的先后顺序为“网易云音乐平台—微博平台—小红书平台与B站—抖音平台—微信公众平台”。随后,经过网友们在各个平台间持续不断交叉传播,“emo时听红歌”现象形成了一定的热度。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视角来看,各平台内不同用户进行“emo时听红歌”信息交互的需求和动机各有差异。其中,“emo时听红歌”文化的核心受众主要聚集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以抵抗“emo”情绪为主要需求,其信息交互动机多为价值传递的自我实现;而非核心受众在各平台均有分布,有以兴趣分享为需求和动机的普通网友,也有以获取流量为需求和动机的网络博主。
(二)“星星之火”的传播样态
经过不断传播,“emo时听红歌”现象逐渐进入部分主流媒体视野,其中“重庆共青团”抖音号、“河南共青团”微信订阅号和“安徽共青团”微信订阅号分别于2023年6月1日、6月15日和6月22日对其进行了传播助力。当前,网易云音乐平台中“emo时听红歌”相关歌单的交互数据仍在持续增长。
整体来看,“emo时听红歌”现象当前尚处于多平台、波动性的初始流行阶段,呈现出“星星之火”的“微火”样态,传播势头虽显乏力,但仍具备较大的传播价值和潜力。以小红书平台为例,数据显示“emo时听红歌”现象首次互动(4.49万互动数)出现在2023年5月31日,并于6月3日达到高峰(9.17万互动数),短时间内呈现“M”形波动后转入低位传播,其间共发布笔记127个,涉及红人126个,累计评论6820条,累计收藏数4.13万。
(三)内容情感积极正向的话语表征
在“emo时听红歌”现象中,青年网友行为交互呈现出积极正向的情感态度。通过对网易云音乐平台“emo时听红歌”歌单中播放量超过10万的两个歌单的分析发现,用户对“emo时听红歌”歌单给出了高度一致的正向评价,几乎所有的评论文本都呈现出了积极正向的情感倾向,“拒绝emo”“增强磁场”“真的有用(有效)”等词句成为高频评论。同样地,在网易云音乐之外的其他平台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到网友们对“emo时听红歌”作品积极正向的肯定。
虽然各个平台中有关“emo时听红歌”的评论内容都呈现了积极正向的情感态度,但其各具特点。以人际传播的自我表露来看,就单个作品而言,以视频为表现形式的作品,其评论表露的量、主动程度、信息深度都是最高的,其次为音乐,再次为文字。其中,以音乐为表现形式的作品的评论表露内容对“emo时听红歌”作用的关注最为集中。
二、“emo时听红歌”现象的文化溯源
(一)“emo”的由来与研究现状
在当前网络文化中,“emo”可用来表达“伤心、难过、抑郁、丧”等多种情绪,常被认为是emotional的缩写。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emo”一词便已经出现,初为Emotional Hardcore的缩写,指代一种与朋克摇滚相似的情绪化音乐风格[1]。
当前有关“emo”的学术研究较少,而且集中在语言文学领域。研究认为,“emo”是青年群体“丧文化”的表达符号之一[2];“emo”类网络流行语有利于青年群体表达情感态度、宣泄和排解情绪压力,在群体效应下具有一定的精神治愈的效果[3];在模因论视角下,其快速流行于网络的内部因素是语言的经济性和词汇的可及性,外部因素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丧文化”的社会环境[4]。总体而言,当前学者们对于“emo”作为网络流行语的态度较为客观辩证[5]。
(二)红歌与“emo”的“破圈”交融
网络圈群是网友群体基于某种特定原因组合而成的网络聚合空间[6],在此视角下,“emo时听红歌”现象已具备一定的网络圈群化特征,青年人以音乐社交的形式聚集在网易云音乐等网络平台。与“emo时听红歌”圈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抑云”圈群,该圈群以负面文风、伤感表述、颓废主义为主要特征[7]。从网络圈群的聚合过程来看,“emo时听红歌”圈群鲜明区别于“网抑云”圈群,成员们以抵抗“emo”情绪为共同情感追求,以红歌为文化认同,聚集在以网易云音乐为主的网络平台,完成了“认异、求同、聚类”[7]的基本建圈环节。
“emo时听红歌”作为一种青年网络文化现象,具有“亚文化”属性[8],而红歌作为主流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被青年人主动用来抵抗“emo”情绪,则彰显了红色音乐文化作为新时代主流文化构成的重要价值和无尽魅力,体现了十足的文化“破圈”感。这种文化“破圈”,不是红色主流音乐文化向“emo”亚文化的有意渗透,而是“emo”亚文化内部受众向红色主流音乐文化的主动奔赴,这种主动奔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三)“emo时听红歌”现象的本质
“emo时听红歌”现象,就其本质而言是当代青年的情绪自我疗愈,是当代青年与不良情绪的自我抗争,客观上兼具与消极音乐文化对抗的效果。青年在成长成才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困扰和压力,进而产生“emo”情绪,产生不良的心理体验。红歌所呈现的旋律、传递的情感和表达的价值内涵能够将听众带入积极向上的情绪氛围中,进而对其不良情绪进行中和或者剥离,最终实现情绪的疗愈。个体情绪的自我疗愈行为,经由网络的传播和聚集,逐渐形成了“emo时听红歌”的亚文化圈群。从“网易云”到“网抑云”的污名化,再到“网愈云”的出现,明显体现了网络音乐亚文化圈群间的对抗性,而“emo时听红歌”现象的出现则充分体现了红色主流音乐文化与消极音乐文化的对抗。
青年人在以音乐排解和释放“emo”情绪的决策过程中,主动选择以听红歌作为疗愈手段,是当代青年对红歌情感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主动找寻。这种主动的找寻与其对不同音乐文化的体验经历有关,是其基于现实情感和精神需求对主流红色音乐文化的合理选择,是对红歌的红色音乐实质、红色文化实质和红色精神实质的三重肯定。同时,这种选择所带来的积极正向的效果反馈也为“emo时听红歌”现象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动力基础。
三、“emo时听红歌”现象的功能机理
“emo时听红歌”不仅是一种行为选择,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使用功能。“emo时听红歌”所体现的对“伤心、难过、抑郁、丧”等多种负面情绪的疗愈功能存在着相应的机理。
(一)“磁场论”下的行为自洽
通过观察“emo时听红歌”圈群成员的网络评论可以发现,“磁场”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其中。在“emo时听红歌”圈群成员看来,人本身带有一种磁场,当自身磁场变弱时,自身容易受到其他不良情绪的影响,红歌这类带有革命色彩和家国情怀的歌曲所拥有的强大磁场可以增强自身磁场以抵御“emo”情绪。这种“磁场论”被“emo时听红歌”圈群的成员广泛接受,成了其解释自身行为选择的重要内部理论,也是对外界“为何选择以听红歌的方式来抵抗‘emo’情绪”疑问的直白回答。
“增强磁场,拒绝emo”作为“磁场论”常用的口号式表达,可以形象、快捷地表达其思想,不仅有助于圈群成员行为与认知的自洽,也有助于吸引新成员更快地加入其中。“磁场论”并非随着“emo时听红歌”的出现而立即诞生的,而是在“emo时听红歌”圈群成员不断聚集的自组织过程中产生的,其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也是“emo时听红歌”圈群成员不断行为自洽的过程。从“认知一致性理论”来看,“磁场论”的持有者对该理论的主动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其与他人间的认知矛盾的影响。
(二)情绪调节下的音乐疗愈
“emo时听红歌”圈群成员对“磁场论”的选择有可能源于2010年出版的《磁场:世界上最神奇的吸引力法则》一书,其作者H.B.达哇曾在书中表述过“所谓的磁场,其实就是你的吸引力”的观点。这一观点与“emo时听红歌”圈群成员所持的观点非常相似,但是唯心主义色彩过于浓重,不足以科学地解释“emo时听红歌”的功能机理。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音乐是有关情绪和时间的艺术,黑格尔在其《美学》文集第三卷(上)中提出了“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的观点。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音乐能够通过其形式元素的组合变化以声音为介质作用于人的大脑。使用音乐来进行情绪治疗的方法也古已有之,《黄帝内经》中的五音疗法思想作为中医音乐疗法思想的精髓已存在两千多年[9],现代医学实践中也常采用音乐疗法辅助治疗各种疾病。因此,红歌可以通过其独特的节奏、旋律和和声来对听众进行积极的情绪调节,进而达到中和或驱离“emo”情绪的效果,最终实现情绪的疗愈。
(三)情感体验下的精神鼓舞
情绪是情感的外部表现,情感是情绪的本质内容[10]183,“emo”情绪的长效疗愈需要触及其情感症结。红歌在短时的情绪调节作用之外,还能赋予人更为持久和深刻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使红歌具备鼓舞斗志、启迪思想、交流情感、纯洁队伍的重要价值和功能。其价值和功能的实现过程为,以“集体认同—价值认同—身份认同”的心理体验方式,通过“情感表象”体验、“情感意象”体验和“组织情感”体验的心理体验路径,来达成人性需求意义上价值认同的心理目标[11]。
红歌可以通过情感体验为面临“emo”困扰的人们提供强劲的精神鼓舞,在短时情绪调节的基础上帮助人们建立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引导人们直面导致“emo”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激励人们勇敢实施解决“emo”问题的具体措施,为长效解决“emo”问题提供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
四、“emo时听红歌”现象的发展困境
“emo时听红歌”现象的出现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是值得关注、鼓励和肯定的青年网络亚文化现象,但也面临着亟需摆脱的发展困境。
(一)组织聚合度不足
“emo时听红歌”圈群成员的聚集形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对“emo时听红歌”功能价值需求的有意识聚集,即“需求型聚集”;另一种是出于对“emo时听红歌”现象好奇心的偶然性聚集,即“围观型聚集”。“需求型聚集”以网易云音乐平台为代表,圈群成员的聚集空间为“emo时听红歌”歌单;“围观型聚集”以抖音平台为代表,圈群成员的聚集空间为具有较高网络热度的标签话题。事实上,“围观型聚集”在短期内具有较好的网络热度,进而带来一定的“需求型聚集”,但其也会随着网络热度的消退而迅速消散。因此,“需求型聚集”才是保持“emo时听红歌”圈群存续的关键所在。
虽然“需求型聚集”为“emo时听红歌”圈群的存续提供了组织保障,但其圈群成员间交互的紧密程度仍然不足。如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中,用户主要有分享、评论、收藏、听歌四个行为,现有(截至2023年7月17日)播放量最高(21.5万)的歌单的分享和评论数分别为426和83,由此可见其用户交互的紧密程度不够理想。此外,“emo时听红歌”圈群也没有准入门槛和行为规则的设置。因此,可以判断“emo时听红歌”圈群尚且属于松散型的网络圈群,缺乏足够的组织聚合度。
(二)群体认同感不足
“emo时听红歌”圈群成员基于对红色音乐的文化认同和“拒绝emo”的价值认同集聚在网络中并形成了亚文化圈群,但其松散的组织聚合类型未能给圈群成员带来足够的群体认同感,主要表现为成员间的互动程度不足和符号化表达不足。
圈群成员间紧密深入的信息交流有助于增进群体归属感进而强化群体认同,但“emo时听红歌”圈群尚未建立便捷、高效、稳定的交流平台(如交流群),也尚未出现组织圈群活动的核心成员,成员间的交流互动方式主要为随机性的评论互动,交流的频次和交流的深度都较为不足。此外,符号化表达是圈群成员身份塑造的重要方式,在符号化表达方面,“emo时听红歌”圈群对外常用的语言性符号表达方式为“红歌+emo”的组合式造句,在内部的交流中常用的语言性符号表达方式为“增强磁场,拒绝emo”,但“增强磁场,拒绝emo”这种表达亦非为其所独有的。而且,“emo时听红歌”圈群尚未形成其他非语言性的符号化表达方式。
(三)亚文化产出不足
当前“emo时听红歌”圈群的亚文化产出仅仅是用于抵抗“emo”情绪的歌单,其尚处于对红色音乐的组合使用阶段,缺少具有自身独特色彩的原创性亚文化产出。“emo时听红歌”圈群亚文化产出不足的原因在于其文化生产的驱动力不足和技术门槛过高。
“emo时听红歌”圈群的主要聚集动机为以听红歌的方式抵抗“emo”情绪,这种聚集动机多数情况仅以听红歌的方式即可满足,因此其圈群成员缺少进一步进行亚文化产出的有效动力。同时,“emo时听红歌”圈群作为一种音乐亚文化圈群,其文化产出的一个重要方向便是音乐创作,但大多数圈群成员作为红色音乐的听众并不具备音乐创作的能力,因此无法满足这一亚文化产出的技术要求。但是,“emo时听红歌”圈群成员亦可尝试在音乐创作之外进行亚文化产出的有益探索,文化产出的形式也不必限定为红色歌单及音乐创作。
五、结论与启示
“emo时听红歌”现象是一种以听红歌为主要方式来抵抗“emo”情绪的“红色圈群”[12]亚文化现象,“emo时听红歌”有助于青年的情绪自我疗愈、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播和红色精神的弘扬,虽然其尚处于初始流行阶段,也面临着一定的发展困境,但其仍具有较高的传播价值和潜力。通过对“emo时听红歌”现象的研究,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一)重视当代青年的情绪需求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发布的数据显示,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达24.1%,25—3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达12.3%,这说明当前我国青年群体存在着不小的心理压力和面临着一定的心理健康风险。近年来“emo”类网络流行语的持续出现,则正是这种压力在网络空间中的文化体现。在网络空间中,青年使用“emo”类的语言表达自我,真切地反映了其情绪需求,而“emo时听红歌”的出现则是这种需求的自我满足。虽然“emo”不代表抑郁,但青年抵抗“emo”情绪的需求若被长久忽视,其所导致的“emo”情绪的持续出现和加重必然会加剧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风险,严重影响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因此,不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要及时从“emo时听红歌”现象中读懂青年群体的情绪和情感需求,并及时采取有效的针对性措施。
(二)增强青年的红歌文化自信
青年群体乐于追逐流行文化,对网络文化更迭呈现出“喜新厌旧”的心理特征。红歌作为红色主流音乐文化,虽然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但仍然会被一小部分青年嫌弃带有“土味儿”。这种“土味儿”的非议,会进一步阻碍红歌文化在青年群体中发展和传播,在“emo时听红歌”文化圈群中便有成员表达了对于这种非议的忧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emo时听红歌”现象在网络上的出现使得红歌在青年群体中“出圈翻红”,成为疗愈“emo”情绪的新网红,恰恰证明了对于“土味儿”的忧虑的非必要性,更证明了红歌在当下的重要现实价值和文化魅力。因此,要积极利用网络提升“emo时听红歌”的影响力,倡议主流媒体尤其是以青年为主要受众的媒体加大肯定和宣传力度,为“emo时听红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不断增强当代青年对红色主流音乐文化的信心。
(三)推进红歌文化的守正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3]。“emo时听红歌”现象的出现,正是以青年群体对于红色主流音乐文化的精神需求为现实基础的。但如何以“emo时听红歌”为契机弘扬红歌文化,实现其在青年群体中从“翻红”到“长红”的飞跃,则是其所面临的新的发展问题。2022年1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回信勉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时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崇德尚艺,守正创新,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14];2023年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贺信中指出,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15]。因此,以“emo时听红歌”为契机实现红歌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由“翻红”到“长红”的飞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立足青年需求,不断创新其创作和传播工作,以红色主流音乐文化的魅力充盈新时代青年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