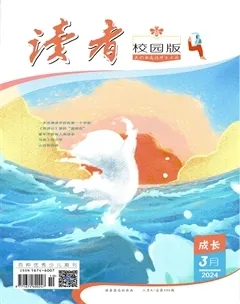我不是你最出色的学生

教师节那天,手机弹出来一条信息:“虽然我不是你最出色的学生,但你是我最好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呀!”
送祝福的,是我之前带过的小学毕业班的一个女生。如果不是知道她在小升初语文考试中发挥失常,我会认为这只是她的客套话。
简短的文字仿佛一块尖锐的石头,穿越厚重的尘埃,击破紧闭的时空之门。我看到门内有一个人向我走来,那轮廓越来越大,面貌也越来越清晰——是学生时代的我。
曾经的我也会因为不是老师最出色的学生而难过、不安。那时候,观念里的出色是用成绩衡量的,分数高,便自认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而一旦成绩跌落,无论跌落多少,都会生出一种愧疚,认为对不起老师。所以自小学起,我就懂得用努力、拿名次来维持自己在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形象。我既怕自己做得不够好,不能让老师骄傲,又怕自己做得太好,却不能一直维持这种状态而让老师失望,所以我患得患失,时喜时悲。
然而,就像所有的食品都有它的保质期一样,光环这种东西也有它的保质期。中学时代的我,已无法单纯靠勤写勤记来消化复杂的知识。当大脑太久跟不上知识的步伐,我自然泯然众人。意识到这一点,我焦虑、挣扎过,但时间久了,便习惯隐匿在人群之中。唯一不变的是,我还是会在老师偶然的关注下,因觉得自己不够出色而抱有歉意。
是的,因为不够出色,所以我不能在老师抛出问题而全班鸦雀无声时,给他一个完美的答案;因为不够出色,所以我没有机会在众多佼佼者中为班级争夺一份荣誉;因为不够出色,所以我无法在老师需要时,成为他管理班级的左膀右臂……青春期的我,为自己的普通而内疚。
初入大学,我仍然是班里的“小透明”。大二竞选上班级的学习委员后,我才有了走出人群,独挑大梁的勇气。彼时的我也在为自己是否担得起大任、做得好表率而担忧。因为害怕辜负老师和同学的信任,所以我要想常人不能想,将事情做细、做精。虽然其间我因对工作负责而获得不少任科老师的认可,但我始终无法重新定义老师眼中的出色。
直到有一次,心理老师让大家上台分享关于“惩罚式教育”的看法,我提前三天思考、打底稿、背熟稿子。上台后我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直接念从网上抄来的稿件,而是结合自身经历全程脱稿。我记得下讲台时,在第一排做记录的老师不加掩饰地表扬了我,后来又在微信聊天中再次夸我的发言精彩,说我的发言让他印象深刻,他很欣赏我。
那一刻,我意识到,做好一件事何尝不是出色的另一种诠释?也许只做一件事和出色依然有差距,不妨保持认真的态度去做好每一件事。
仔细想来,我的中学时代没有值得炫耀的成绩和才艺,但不止一位班主任曾在我的家庭报告书上写下“该生努力、踏实,能做好本职工作,深受大家喜爱”之类的评语。我初二时的英语老师,曾在我的英语日记本的最后一页,用红笔工整地写下:“You really did" great and I’m proud of you.(你做得很棒,我为你感到自豪。)”显然,我是班上一篇不落写完整个学期日记的少数学生之一。
我又想起大学时教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老师。她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学时我很怕她,在她的课堂上并不活跃。虽然在大一那年,在4个班的100多个人当中,我拿了她所教科目的最高分。毕业后每年的教师节和春节,我都通过微信给她送上祝福。有一次她说,我是她“2019级教过的学生中最深情的一个”。她没有忘记我,正如我没有忘记她一样。而我由衷地相信,她对我有印象,来源于我的用心。我每年给她发的祝福语,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了表达对她的感激,我曾写过小诗送给她。还有大一时,我精心打磨了她每周交代的日记,她也不止一次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展示给其他同学,用有声和无声的方式表达对我的肯定。
我曾以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成绩要绝对优异,可是在我遇到的老师的眼中,做事有始有终,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做好每件事的我,同样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没有老师用“出色”来评价我,即便在我成绩名列前茅的小学时代。我的老师夸我,无外乎我的字写得好,学习态度端正,做事踏实等,他们评判学生的依据是那么多样而具体。
冷冰冰的成绩无法完整诠释“出色”二字,这一点,我在大学才有所领悟,毕业后当了老师更是深有体会。我固然记得那些成绩好的学生,但我更记得那些成绩一般却一直在努力的学生,就像故事开头那个给我发信息的女生,她曾在短短一个月里,把语文成绩从60多分冲到90多分。我当然为她骄傲。但在得知她在关键时刻马失前蹄时,除了惋惜,我并未觉得她辜负了谁的期盼,也没有因此认为她不好。因为我知道,这个结果不是她后期怠惰造成的。相反,她已经尽力了。
思及此,我回复了她的信息,首先谢过她的祝福,然后告诉她:“在成绩方面,没有谁是最出色的,但在坚持与努力方面,你比任何人做得都好,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潜力的学生。”
我的意思是,不必因你不出挑的成绩而觉得愧对老师,比起用成绩单方面定义的出色,老师更希望你在青春这场航行里,踏实掌舵,扬帆远行,那样的你,更值得被称赞。
(本刊原创稿件,大冰咂图)